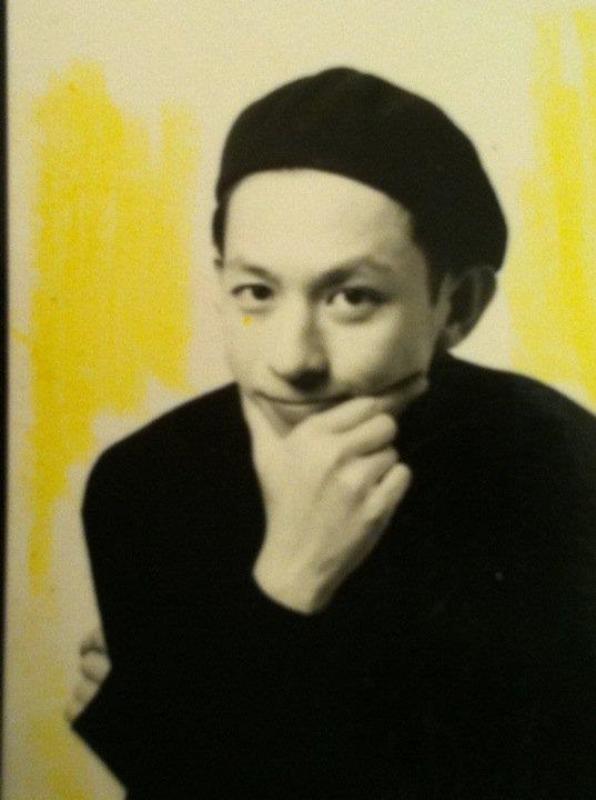創作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來訪的遠方
總統大選前,有兩位特別的朋友來訪問我,特別來觀選,為了保護她們,個資會模糊處理。 她們是來自對岸的朋友,《人選之人》的觀眾,其中一位喜歡閱讀,很早就讀過我的戲劇劇本。另一位,對政治跟社會改革非常有興趣。 她們在歐美留學,兩人背景不同,一個家中靠近公務體系,一個靠近市場,但都不約而同地,或因為霸凌、或因為性向,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幻滅,不管是身為女性、身為性少數,或面對審查,而再怎麼家底高於他人的人,都特別在疫情期間感到幻滅,「我20歲的時候感受到了一個存在主義的危機。」來訪的友人說。直接把你鎖在家中數個月,甚至用鐵鍊把你鎖在家中,像動物一樣地搶著物資,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求助無門。 我想起我在北京做小劇場跟寫小說的好友,前幾年跟他通信時,他說,審查愈來愈嚴格了,一開始是交劇本,後來是交排練錄影,再來是現場,要一字不差。 這樣要怎麼創作?有好多戲就不能演了,那得怎麼辦?不曉得,不知道,這樣還能創作的,我都深深敬佩。 還有曾經在深圳駐校教戲劇,遇到一位學生,我會一直記得,他來找我的那個下午,支吾再三,說有一件事想跟我說,但又起身,逡巡一週,到處檢查頭上有沒有監視器,確定整個教室都沒有,才開口跟我出櫃,如今,他也在國外,正在學習表演,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 以上幾位友人,都想盡辦法要留在國外,只有北京的朋友,說,雖然想走,但也不知道要去哪,創作與表達,如果跟所在之地斷了連結,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台北的書店是天堂。」來訪的友人說,她們買了好多好多書。 「我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但我們參加支持巴解的活動,都要戴帽子口罩,因為大使館會派人來看,會參加這類活動的通常都會特別被注意。」互相提醒、參加這類活動要蒙面、隱蔽身分已是常態。 「家裡以為我學的是一個有用的科目,但我其實唸的是政治。你知道嗎,辛亥革命前有個女性政治家,很早就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理想的世界,跟一百多年前她提出來的居然差不多,很可惜的是並沒有發生。」 那為什麼特別來找我呢?她們說,這是政治代餐,常常透過韓國或台灣的作品來「代餐」,但聽到中文講出來,衝擊力又更強,她們感受到政治是一種日常,感受到戲劇可以跟自己有關。 「你們那邊還是有很
-
兩廳院櫥窗 Hot at NTCH NTCH Salon 劇院沙龍:劇場.議場—「思辨機構」系列講座摘要
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二)
「思辨機構」系列講座的第二場仍以「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邀請四位劇場中生代導演黎煥雄、周慧玲、王榮裕與郭文泰與會座談。他們都從小劇場開始自身的創作生涯,一路親身經歷台灣表演藝術環境的發展變遷,也與國家場館進行過不少合作;趁此機會,4位導演分享了他們對國家場館發展迄今的觀察,也提出他們對場館與藝術家合作過程的期待。
-
挑戰邊界
乾杯
對於藝術家來說,所謂挑戰,在於如何創作出概念和思想碰撞衝突,卻又兼容並蓄的作品,進而將我們從每天的日常中,提升到不同的層次。作為劇場吧檯的調酒師,我們如何使觀眾能夠同時品嚐到威士忌、麝香葡萄、香蕉、白可可、牛奶?而同樣重要的是,是如何建立足夠的自信,以及對觀眾的信任,提供充足的空間,讓他們在獨特而複雜的劇作脈絡中理出頭緒?
-
兩廳院櫥窗 Hot at NTCH NTCH Salon 劇院沙龍:劇場.議場—「思辨機構」系列講座摘要
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一)
除了作為表演空間,國家兩廳院也自許成為為產業創造對話的場域,從3月下旬開始的「NTCH Salon劇院沙龍:劇場.議場」,第一個系列以「思辨機構」為題,邀請產業裡的各種角色開啟對話,用各自的立場闡述,檢視、思考藝術機構在文化生態裡的公共任務,在時代快速的演進中,各機構又該如何轉型。 此系列首場的題目為「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邀請蘇品文、洪千涵、許哲彬與鄭伊里4位藝術家,分享自己在與場館或機構合作創作的經驗中,對自己與機構角色的看法與思考。
-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工作中的反思
表演藝術在疫情期間被迫停下,難免會陷入「社會真的需要我們嗎?」的自我質疑,表演藝術產值很小,12億,電影200多億,出版100多億,但小眾有小眾的自由,如果最終會面臨上大劇院的挑戰,有做大的準備嗎?
-
挑戰邊界
無念
這段歷史回顧提醒我們關於藝術的傳承,提醒我們自己並不孤單。作為藝術家,我們經常面對空白的畫布、空無一物的空間和傳統的重擔。太多時候,一板一眼的體裁格式限制了我們回應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被要求寫一首詩,與其拿起紙筆,或許我們更該熬煮一碗滾燙的石頭湯,或是靜靜地躺在鬧區的大馬路上,抑或裸身躍入太陽
-
A Bigger Picture
創作,是追求安全感,還是走出舒適圈?
《亂世佳人》的主角被詬病的原因,一是以愛之名,不理他人觀感。二是以「明天又是另外一天」為座右銘,什麼事都好,先做了再說,天掉下來當它是被子拿來蓋。 自我中心一向被認為是一個人自私的禍源。不管今天追求明天更是好高鶩遠的惡習。但放在創作過程來看,擁有自我但又無畏別人的評斷,那樣的分享可以很無私。敢去提出未知而不是緊緊握著已知,也可以讓人看到明天。
-
 專欄 Columns
專欄 Columns浪頭浪尾
一位創作者的光采歲月可以有多長?就像一個人的生命可以有多長一樣,表演藝術因為人在特定時空的接觸而成立,沒有了人表演也就不存在。人的有機而多變,是他最迷人也最難掌握的宿命。因為歲月的增長,技藝的淬煉,藝術家成熟了、又漸漸老去了;而長江的後浪永遠不會停歇地湧來,所以我們不怕藝術的炊煙會斷。但這世代交替的窘境,也是真切到令人著急又無法輕易逃脫的現實。
-
 專欄 Columns
專欄 Columns藏不住的秘密
任何從一個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東西,都有同樣洩密的效果。無論一個人的外表、他的氣味、說的語言、做的創作、行為態度等都是一樣。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就算偽裝也只能掩蓋一時,時間久了真相還是會大白的。
-
特別企畫 Feature 焦點七
國人作品/致力「台灣音樂」 樂音傳唱寶島之美
透過創作才能創造自己的文化,透過樂團的展演,創作才能有展現的舞台。各樂團樂季中展演國人作品,不管是舊作或委創,都可以看到推動「台灣音樂」的方向,透過樂音,展示台灣作曲家的創意與台灣之美。
-
台前幕後
揮灑編舞創意的舞台
「雲門舞集2」的藝術總監羅曼菲表示,舞團方向以創作爲重心,目的在鼓勵年輕人發揮潛力,爲台灣的舞蹈創作注入新血。舞團願意免費提供舞者、道具、場地,給年輕編舞者一個無憂的創作環境。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劇場.創作.行銷
世紀末的台灣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行銷的時代,行銷的概念不只限於商品,就連政治、文化也無可避免。從近兩年台灣劇場的運作上,我們可以看出各中大型劇團對行銷的日益重視;然而,在表達自我意念的「創作」與市場導向的「行銷」之間,是矛盾對立,還是相輔相成?而劇場的行銷又有什麼特殊的思考與做法?透過對劇場創作者與行銷人員的訪談,我們來探究這其中的微妙關係。
-
回想與回響 Echo
亞維儂退燒後
亞維儂藝術節的特色及魅力何在?其代表意義爲何?參演團隊是否從中得到激發與啓示?就藝術節本身,我方政府的交流政策、表演團隊的藝術風格等方面來看,整個活動突顯「藝術節行政組織」、「國際交流意義」、「表演團隊創作」等省思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