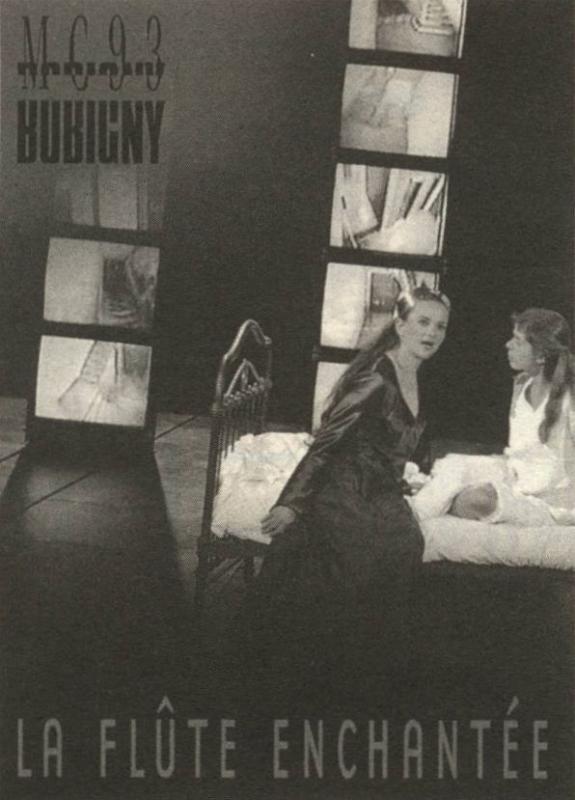被英国重量级剧作家品特称为「诗人」的作家莎拉.肯(Sarah Kane),其作品大胆冲撞欧洲政治、社会、家庭与性的禁忌,并描写舞台上难以表现的酷刑、屠杀、食人、强奸与乱伦,借以嘶喊出对世界的恐惧与狂怒。《四点四十八分,精神异常》速写具有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的耗竭状况,充满了激情与谵妄,表现了作者的全部力量。
若要重新寻觅其必要性,在爱、犯罪、战争或疯狂里的一切,戏剧都应该给予。
──亚陶(Antonin Artaud)
《四点四十八分,精神异常》4.48 Psychose的演出是去年巴黎秋季的戏剧盛事。在崇尚朴实无华风格、艺术要求严格的法国导演克劳德.黑纪(Claude Régy)执导下,伊莎贝拉.雨蓓(Isabelle Huppert)第一次担纲主演、诠释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伦敦自缢身亡,享年二十八岁的英国剧作家莎拉.肯的遗作。
被禁锢的绝望与疏离
雨蓓在暗阒中自观众席间走道以轻悄的小跑步,踏上巴黎「北方滑稽歌剧演员剧场」边界不明的舞台空间,在一小时四十五分的表演时间里,直立定点、寸步不移。她扎了个自然的少女马尾,身著蓝色短袖圆领衫及象征叛逆的直筒皮裤,足登篮球鞋,使她略带稚气的娇小身材,产生雌雄同体的幻觉。在开场时漫长的沉默中,她仿佛被莎拉.肯遗嘱般的诗文穿透,情不自禁地泪珠盈眶,但毫不眨眼。演出中,她双臂贴身下垂,偶尔紧张地举起,双拳紧握,偶尔痉挛似地展开。幽灵般的脸色,空洞的眼神,雨蓓以奉献、被禁锢的绝望英雌姿态,成功地扮演了这个濒临自杀边缘的疏离者角色,赢得观众与剧评的一致喝采。
黑纪在雨蓓背后架设了一片特殊材质的帘幕,虽呈金属光泽,实际上产生了像金属墙的功效,不但可供投射,也同时能让字与数字投射到剧场的背景墙上。这些投射因此被切割成两部分,有的超越帘幕,直到投影在剧场两侧的楼厅和墙上,使得观众感受到建筑物的布局被打碎、弄乱和扩大,而被转换成一个心理空间。雨蓓和剧中另一演员瓦特金斯(Gérard Watkins)隔著帘幕对话,两人从未面对面,象征著无法沟通的困境。
流星般的烈焰生命
被英国重量级剧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称为「诗人」,也被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剧作家博德(Edward Bond)誉为「新英国戏剧」(New British Theater)中最重要的作家莎拉.肯,其作品吸引了英国当今二十到三十岁一代的年轻戏迷。一九九五年,她的第一篇剧作《摧残》Blasted在伦敦皇家宫廷剧场(Royal Court Theater)首演时,引起媒体的骚动,迅速成名。在如流星般倏忽即逝的烈焰生命里,她总共写了五篇影响英国当代剧坛深远的剧作,现在在欧洲各地不断地被搬上舞台。
莎拉.肯大胆冲撞欧洲政治、社会、家庭与性的禁忌。在她最暴烈的作品中,喜欢描写舞台上难以表现的酷刑、屠杀、食人、强奸与乱伦,借以嘶喊出对世界的恐惧与狂怒。因此她的剧作充满了挑衅、猥亵与颠覆性,令人想到亚陶的「残酷剧场」;作者本人也曾承认亚陶与她剧本的相关性,但她直到写作《四》剧时,才读到亚陶惊人的论述。
《四》剧宛如一首长诗,没有角色,也没有舞台指示,在表面的松散结构下并列内心独白、对白的断片、交谈的片段、一连串的药物名称、病状、字与数目字等等。作者主张的「形式即意义」,不仅体现在文体的音乐性上,同时也体现于文本在页面的排版上:重复地另起一行、右侧的评注、自由的字距与行距等等。此外,剧名中的「四点四十八分」无疑指出黎明前精神清醒的极限时刻,也是剧中陈述者自缢的时间(「四点四十八分/当自暴自弃造访时/将自缢而死/听著我底恋人呼吸的声音。」)
速写自杀前的耗竭
《四》剧速写具有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的耗竭状况,充满了激情与谵妄,表现了作者的全部力量。开场时,在意识清醒的短暂片刻,陈述者以一连串重叠排比的问句自我质疑:「可是妳有朋友。/妳有很多朋友。/妳给予妳的朋友们什么?使他们如此支持妳?/妳给予妳的朋友们什么?使他们如此支持妳?/妳给予什么?」她不自觉地、深刻地拒绝一切并厌恶自己的身体:「我好胖!」、「我的臀部太大」、「我讨厌我的生殖器官」;同时表明在接受医学治疗时,体重暴跌暴增,和描述与不知所措的精神病医生破洞百出的谈话,更自称为「破碎的阴阳人」。
莎拉.肯自杀前不久公开谈到《四》剧时说﹕「在人的头脑里,现实与各式各样的想像之间的屏障完全消失,以致你分不出清醒生活和幻想生活的区别……你不再知道该在哪儿,也不知世界从哪儿开始……所有都属于连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界限开始崩溃。」再者,文末一连串的祈使句,透露出她对爱的需要与幻灭:「确认我/见证我/看我/爱我」、「看著我消失/看着我/消失/看着我/看着我/看着。」在吐出最后一句话「请把帘幕打开」之后,她便告别她的精神炼狱,她的痛苦、黑暗和疲乏,永远地沉寂了。
导演引导生命物质的交织
导演黑纪已届八十高龄,今年是他第五十年的剧场生涯。这位对现今法国四十岁一代导演有深刻影响的大师,不依靠剧院机构或常设剧团,特别致力于当代戏剧作品的首演,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以外的作品。他经常与在世的剧作家合作,最近几年则发掘了三位欧洲新生代剧作家──挪威的佛思(Jon Fosse)、苏格兰的哈洛尔(David Harrower)和莎拉.肯。黑纪于一九九一年获得法国「国家戏剧大奖」(Grand Prix National du Théâtre)的肯定,三年后再度荣誉加身,获颁「巴黎市舞台艺术大奖」(Grand Prix des Arts de la Scène de la Ville de Paris)。
对黑纪来说,他导演的主要工作在重新处于文本写作之前的状态,试图感觉话语和动作的起源。对于表演手法,黑纪选择极简的原则,他说:「我不相信声音的练习,也不相信肉体的表达。」他反对所有欧洲传统剧场的写实主义,关注「如何引导每个人,以自主的方式,革新自己对世界的感觉。」他以缓慢的节奏、灯光投射布景的优势,以及疏离的美感,来达成这个目标。
黑纪细致缜密地执导了这部莎拉.肯的天鹅之歌,虽然整体演出过于均匀地抑郁,忽略了文本中某些剧烈的挣扎,仍然让我们无声地听见,在套上命运的绳结前,这个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阴阳人,是如何勇敢地说出「我」这个字。
文字|苏真颖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法国文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倾听充分流泻的文体
专访克洛德.黑纪谈《四点四十八分,精神异常》
地点:巴黎的「北方滑稽歌剧演员剧场」
时间:二○○二年十月五日
访问整理:苏真颖(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法国文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前言)戏剧学校学的、电视上演的及百分之九十五舞台上的呈现等等一些惯用的表演方式,正是谋杀作品文体的表演手法;我们听不见文体,文体不活跃。我的尝试是继续致力于文体的倾听,让文体被听见和充分地流泻;倘使文体能被确切听见,那么就能建立倾听者想像中的表演。
苏真颖(以下简称「苏」) ﹕您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戏剧导演之一,现在「北方滑稽歌剧演员剧场」正在上演您最新导演的《四点四十八分,精神异常》;您为什么对莎拉.肯的《四点四十八分,精神异常》感兴趣?
黑纪(以下简称「黑」)﹕我不止感兴趣而已。对我来说我最关注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仿效许多前人,比如贝克特(Beckett)、品特(Pinter)、毕希纳(Büchner)以及其他人,甚至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新文体;然而莎拉.肯发明了一种随着每部剧作转变的写作方式。
她总共写了五个剧本。在前三个剧本里,都有极端暴力的行为如鸡奸、口交、阉割与拔卸肢体及眼睛等的描绘;在这三部剧作之后,她认为其实这些暴力行为的呈现对她来说都是隐喻,也许她希望停止在舞台上表现这些暴力,而决定往后将写作当成语言的锤炼。
仅仅页上一字,即成戏剧
她最引起我共鸣的是在《四》剧中所说:「仅仅页上一字,即有戏剧。」( Just a word on a page and there is the drama)。 实际上我所尝试的就是放弃所谓的奇观式演出,如布景、动作、机器装备、灯光、映画和复杂的音效等等,而以语言的处理为优先,并且训练演员让他们的语言被听见,来证明语言能传递感觉、运载感觉。同时,如果以某种方式述说语言,将会让语言的形貌被看见。因此,我选择避免创造过多的形像,甚至丝毫都不要,也没有什么布景,反而使用流动而无限制的元素如灯光,让文本来创造并影响观众的想像。观众看见文本希望让人看见的,从他们听到及看到的线索开始想像。
莎拉.肯的文笔十分艰涩、十分赤裸,事实上,她以一种绝对直接的方式直指「存在」。同时,她面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非常极端,也就是说她不想死,但是她也不想活。无疑地她因为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无法和她不能接受的世界联系,终于导致她走上自杀一途。
苏:两年前《四》剧在伦敦首演时有三名演员,为什么您只以伊莎贝拉.雨蓓(电影《钢琴教师》的女主角)与杰哈.瓦特金斯的两人对话来演出?
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方式。莎拉.肯说她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角色;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剧本,不如说是一首诗,而她想证明一首诗也可以是戏剧。不管是像伦敦的三人演出还是几人,都是情有可原;不止是莎拉.肯,从许多忧郁症、自杀的病例来分析动机,我们知道精神分裂症会增殖人格,因此我认为由同一个人诠释多重人格比较有趣,感觉也比较强烈。
多重人格的演出诠释
伊莎贝拉.雨蓓特别具有这种诠释多重人格的天赋,连续诠释几个非常不同的人,甚至在肢体有所区隔。只是在这出戏里有许多的拼贴,和写作风格的变化,实际上还有好几个文体。除了设法让观众聆听和想像这些文字被书写的原貌,我还保留了短篇幅的对话语气,并且避免让观众以为这只是一段主角与医生面对面隔著一张桌子、在精神病院里的对话。
透过演出,这些对话变得抽象,同时这或许发生在她的回忆里,并任由她重新组织。她对杀她的医生感到莫名其妙,却又带著激情的爱。她严厉批评精神科的治疗方式,更严厉批判她所谓的化学性脑叶切开术,亦即大量使用抗忧郁剂来试图救人。我们虽然可能把某些人从某些事情里拯救出来,但同时我们也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身体变坏,改变他们的思维,也剥夺了他们真正的人格,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即使是对所谓进步的精神病医学,我们也要对其提出质疑;同样地,更要探究它的极限。事实上,萦绕在莎拉.肯脑际的念头之一就是消除界限 ,跨越极限;而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就是打碎所谓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当我们正视社会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发现它病入膏肓,各国元首似乎也是病入膏肓,很奇怪的是这些「病人」以什么名义决定其他特别有天赋、特别聪明而超越普通思想的人是病人,而他们不是?继俄共与德国希特勒之后,是制度决定了作品思想有碍当权者的人,必须被送进精神病院和劳动营等等而无法继续写作。我认为,莎拉.肯的剧作说的就是这件事,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见证人,一个以自杀作证的见证人。
沉默与倾听的关键
苏﹕和您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在《四》剧中听见大量的沉默。您对剧场中「沉默」的处理有何看法?
黑﹕我们应该将沉默视为一种语言,而不是什么语言的停顿。演员总是发出声音,又很快地激动起来,说得太快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从那里说出来,为什么说,或随便说而不留意台词的文体,只造成动作与声音的混乱,什么都无法辨认,这是一种绝对的蒙昧主义,也是大多数剧场演出的情况。无论如何,在我们欧洲地区是这样,我希望在你们国家不一样。
苏﹕您努力让您的演员避免角色分析与自然主义的扮演原则。那么要如何指导演员饰演如此极端的自杀者?
黑﹕只要其他事情不假装,专注于作品就好了。在作品里潜在著真正的内容,还没有完全具体化,也还没实现,然而却能激发比现实表象更强烈的想像。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作品世界的潜能状态,并悬浮在想像事物的世界当中。要达到这个境地,只需要聆听作品就够了,一切都在作品当中。当它是一部真正的作品时,演员的表演方式就在作品里,导演也在作品里。因此,除了倾听文本之外,没有别的,我希望演员们专心倾听文本,而我们倾听专心倾听文本的演员。
当然!我们也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研讨文本,我们经常重新翻译作品,朝各方面探索,尝试联系作品里作者无意识的部分,而那部分确实非常广大,这是工作的本质,作者的作品正好揭露了持续存在而无意识的事物。如果我们好好倾听,可以感觉到文体的根源,感受到从作者身体发出的声音,如何释放写作中沉淀的东西。重要的是,不要装内行,自以为是天才或戏剧家。归根结柢,戏剧学校学的、电视上演的及百分之九十五舞台上的呈现等等一些惯用的表演方式,正是谋杀作品文体的表演手法;我们听不见文体,文体不活跃。我的尝试是继续致力于文体的倾听,让文体被听见和充分地流泻;倘使文体能被确切听见,那么就能建立倾听者想像中的表演。道理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