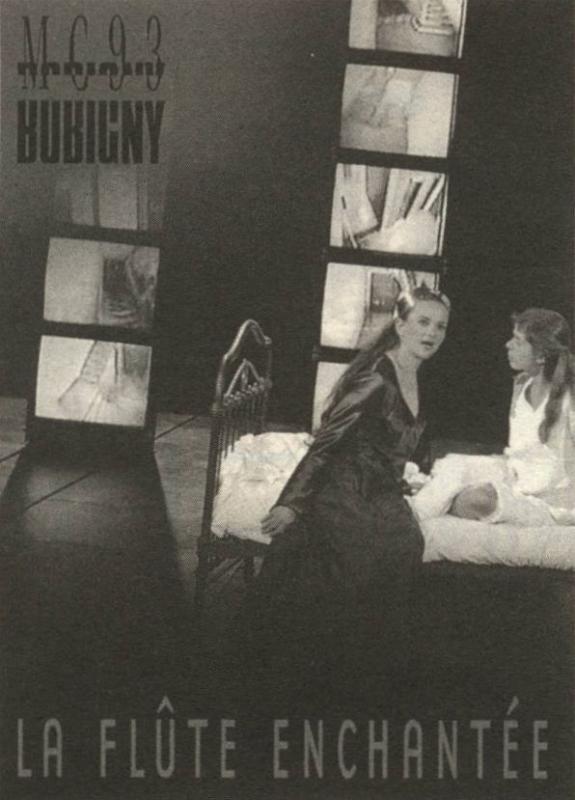观赏胡塞尔的舞台作品,不免使人联想亚陶毕生所追求的一种独立于言语之外的具体、物质化舞台表演语汇,一种先行诉诸观众五官的舞台语言,熔音乐、舞蹈、戏剧与多媒体为一炉,表演意象强而有力,演员精力迸射,全场演出爆发惊人的能量。
「对我而言,文学的文本出奇地重要。文本由现实的凝聚与浓缩架构而成,为一种可触摸的现实。这是一种应该爆发的能量,而非剧场的根基。文本既非一种刺激,亦非一种灵感,这是一个搭档……对于文本,我比任何人都还要忠实,因为我视文本为涵意的总和,可是表达的状况是我创造的,根据我个人艺术意识进展的阶段。」
──T. Kantor(注1)
千禧年四月,当巴黎剧场受春假悠闲气氛之感染而显得有点动力不足时,来自比利时名不见经传的「乌托邦」剧团(Compagnie Utopia),在北郊的「热纳维利尔剧院」(Théâtre de Gennevilliers)带来创团的三出力作──《安葬死者/拯救生者》(改编自契诃夫之名剧《普拉托诺夫》)、《侯贝多.如戈》(戈尔德思著)以及《欧洲人》(豪尔德.贝克著),这三出戏不仅演得热烈异常且意蕴丰富,更重要的是活力四射,让观众看得血脉贲张,内心澎湃激动,终场仿佛经历一场净化的仪式,身心舒畅无比。这类型高热量的文学剧场近来在法国甚少得见,这也就难怪巴黎的剧评家会大加推荐,而现场观众不管同不同意导演的诠释观点,剧终也不得不为演员热情奔放的一流演技忘情地鼓掌。
导演阿梅尔.胡塞尔(Armel Roussel)可以想像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由于不满法国剧埸侧重文学诠释的传统而跑到比利时求发展,今年才三十出头。可是就舞台表演语汇之掌握以及剧本分析的能力而言,胡塞尔的表现完全不输成名的大导演;那种完全驾驭舞台演出因而显得胸有成竹的气势,是刚出道的导演所少有的。这点想必是巴黎剧评家对他另眼相看的主因。
胡塞尔导起戏来绝不墨守成规以外,更是个能用大脑思考的导演。他所挑的三出剧本无一不是现代经典之作,而且契诃夫是廿世纪下半叶欧陆剧场的最爱,戈尔德思为近十年来最热门的法国剧作家。面对这两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后起的导演首先必须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突破前人之作。而贝克的名声在欧陆或许不如前二者响亮,不过他的剧作侧重历史深度之际并同时观照当代世局,绝非容易处理的剧本。
创团之始即敢挑战受欢迎、高难度的现代经典,并勇于提出新诠,更能以戏剧表演特有的媒介先行诉诸观众的感官,借以与一般阅读剧本之知性活动作区别,胡塞尔不仅能读更能导。为了淋漓尽致地表达个人读剧的观感,他不惜改编、浓缩剧本,并擅用多媒体,极力刺激演员用身体直接表达他们对剧中人的各种幻想,他的舞台演出因此总是濒临疯狂的边缘,爆破力惊人。
以契诃夫之作为例,众人皆知,契诃夫的剧作向来被视为日常人生的写照,乍看之下无聊、消极,角色缺乏生命的动力。《普拉托诺夫》为作者十九岁时的处女作,从胡塞尔的视角观之,本剧透露的是少年契诃夫满腔改革热情受阻,以至于对人生幻灭的剧烈过程。主角普拉托诺夫虽有奋斗的想望,一股压不下去的欲望却在他体内蠢蠢欲动使他日夜难安,可是周围的环境却处处掣肘,让他经常感到无奈与无力。
这两股相互对抗的势力造成剧情猛烈动荡的活力与张力,胡塞尔由此点切入剧情,浓缩、改编、甚至于改写台词,大量借助马戏、音乐与舞蹈,将主角本能的冲动、欲望以及狂放的性幻想一一呈现于观众眼前,其他角色亦皆为求生的欲望所逼,个个显得激昂与疯狂,全场演出迸射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生猛精力,与一般契剧缺乏活力的演出情境大异其趣。
胡塞尔更在舞台上公然为契诃夫的演出传统致哀:导演在舞台右前方供著一张作者遗照,前面点了一根白蜡烛。看似破坏偶像的(iconoclastic)顚覆性演出,其表演逻辑实际上是出奇地紧密,环环相扣,高潮迭起,让人看了还想再看。
然而胡塞尔绝非便宜行事的导演,更非一位随意窜改作者的心血结晶以满足自己创作欲的导演。他所导的《侯贝多.如戈》,仅在表演的场次顺序上小作更动,其余不仅完全按照原文一字不易地演出,且在表演的过程中处处突出剧文的绝对重要性,结果依然震撼人心。
凸出剧文的绝对重要性
侯贝多.如戈为一无动机杀人狂,戈尔德思采戏剧表现主义编排场景的手段,以十五个主角歇脚的人生旅站,铺排主角越狱、弑母、逃亡、「强暴」少女(一名「小女生」)、暗杀警探、劫持人质(公园中的一名「太太」)、滥杀无辜、被捕、以及最后从监狱屋顶坠楼丧生的人生行程,剧情支线交待两个家庭──「小女生」以及「太太」两家人──解体的过程。本剧虽以真人真事为本,剧情初看在于暴露现代都会的暴力问题,实则借由种种象征譬喻,探究当代人生的困境。戈尔德思并于剧中大量旁征博引,特别是古波斯太阳神密特拉(Mithra)的崇拜仪式,全剧因而远远超出社会写实剧的规制。
于深刻的主题之外,戈尔德思剧作之所以能在作者谢世后的数年间迅速成为欧陆剧场的常演剧目,乃在于他独出机抒的文风,这是一种宛如街头巷语但其实典雅有致的古典语言,个人色彩浓烈。
胡塞尔即以戈尔德思的剧文作为全场演出的重头戏,因此他几乎从头到尾皆让演员面对观众直抒胸臆。如此一来,剧中人的言谈困境首先得以暴露无遗;他们表面上看来有问必答,交往密切,实则各说各话,一种基于无法沟通而衍生的孤寂感弥漫全场演出。孤单、寂寞、沟通困难是戈尔德思戏剧的基调。
更重要的是,由于正面表演,戈尔德思文字稠密的对白得以充分展现其绝对重要性。诚如法国当代另一重量级的剧作家维纳韦尔(M.Vinaver)所言:于戈尔德思的字句之间,形式与内容合而为一,各式情感、念头、转瞬即逝的冲动、以及大可扩及宇宙的主题采独特的方式发展,故事、人物、时空全由对白的字里行间透露(注2)。
以戈尔德思的剧文为主,胡塞尔扣紧剧文的神话、幻想与寓言层面发展表演的意象,透过主角人物的活力与能量,探讨现代社会的问题与人生困境。
一个处处有墙的世界
出乎所有观众的意料之外,全戏以第六景〈地下铁车站〉开场。事实上,观众仍在陆续进场之际,一名挺个大圆肚子、装扮成一位老先生的演员(V. Minne饰)已在台上走来走去,并好奇地张望现场的观众。
由巴索尔斯(M. V. Bassols)设计的舞台,其前景正中为一道巨大的铁格栅栏所挡。视演出需要,这道栅栏可分左右两边拉开以空出舞台中央的区位,但此时栅栏仍位于舞台左右两侧的前方位置,并未全然消失不见。因此于演出过程里,观众等于是透过铁格栅栏看戏。这道铁栅栏具体点出禁锢世界的主要表演论述:正如男主角坠楼前所言,我们居住的世界是一个墙外有墙、处处碰到阻碍的世界(注3)。
栅栏之后的舞台全空,只有四部闭路电视分置台上地面四个角落,另有两部电视悬吊于舞台视框之外左、右两侧高处。此外,舞台的最后方为一片落地的投影大银幕所围。闭路电视与投影萤幕的设置皆在于建构一个媒体社会的表演意象。
正戏开演,观众才知台上的「老先生」是第六景中那位半夜在仿佛迷宫般的地下铁车站迷路的老头,他脚步慢半拍,一不留神被栅栏挡住出口:「哗啦一声,我这会儿就在世界以外,在这个不是时候的时候,在这种奇怪的光线下面」(189)。此时从暗地里冒出来的杀人通缉要犯如戈(E. Castex饰)身材壮硕,面无表情,却讽刺地被心慌的老头视为救星。两人接著在看似于夜半的地下车站交心,实则各自面对观众自我表述:老先生自此领悟到:「年青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出轨」,「随时随地」(189),而杀父弑母的如戈则希望自己「变得和玻璃一样透明」,「别人的眼光穿透你的身体看到你身后站的人,好像你人不在那里似的」(188)。他渴望变成「一节安安静静穿过田野的火车,什么都没办法让车子出轨」(189)。
立于高大的铁栅栏之后等著第一班地铁进站,老先生与如戈实为人生道上的迷途者,而白天的正常世界已明白将二人隔除在外。以这场迷途/出轨之戏开场,导演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剧的主题所在。
媒体、影像与社会
〈地下铁车站〉一景过后接著上演的才是原剧的开场戏〈越狱〉,其处理手法亦颇出人意料。因为本场戏里于深夜时分巡逻的两名狱警从头到尾都未在阴暗的舞台上露面,观众是从舞台两侧高悬的闭路电视看到这两名狱警的嘴脸。且由于影音视讯经过电脑处理,角色的面貌已不复辨认,而只见影像的五官动作被夸张处理,演员的声音同时变得失真、滑稽,配上粉蓝的色调,造成一种有如卡通的喜剧效果,这与此时由于阴暗而显得危机重重的舞台气氛成一强烈的对比。
这两名狱警于夜半巡逻无聊至极的时分,因为忘情地辩论人到底是用耳朵或者是用念头听到外面的动静,而眼睁睁地看著由于谋杀生父罪嫌遭到囚禁的如戈从容地逃离监狱。这场开场戏原就是于紧张时刻流露荒谬的况味,尤其是当狱警乙说起:「人家跟我说杀人的本能是安顿在屌上头」,而他已趁监视犯人洗澡之便,仔细观察过六百个以上的屌,结论是这六百个「有大的、小的、有细的、有非常小的、有圆的、有尖的、有超大的,可是从这中间得不出半点结论」(169)。
胡塞尔以只具轮廓、快节奏、机械的闭路影像处理本场戏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且契合戏剧状况。崭新的表演手段从戏一开演即能吸引所有观众的注意力,进而激发观众于未及逆料的表演状况里更专注于欣赏演出的过程。在此同时,闭路电视的影像虽节奏明快,毕竟变化有限,观众不一会儿即转而注意聆听比机械化影像更有意思的对白,因此等于是同时强调剧文的重要性,而未产生喧宾夺主的缺点,十分难得。
在后续的戏里,胡塞尔更三度于背景大萤幕上播放黑白录影影像。首先是第四景〈便衣警探的忧郁〉,一名警探向妓院的老鸨抱怨自己连日来莫名的苦闷。他出门后,如戈尾随其后。紧接著,背景萤幕播放一名吓坏的妓女正面向著观众(老鸨)描述如戈刺杀警探的过程:「他(如戈)跟在探长的后面走,探长好像陷入深思里;他跟在探长后面走活像探长的影子一样;然后影子又像中午的太阳越缩越小,他就越走越靠近探长弯曲的背后,接下来很快地,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插进那个可怜的探长背上。探长停下来。他没有回身。他轻轻地摇头晃脑,好像他的沈思刚刚才找到解答似的。然后他全身摇晃,倒在地上」(184)。
稍后第九景〈大利拉〉更全景透过录影演出:如戈的小情人「小女生」,如同旧约圣经中出卖大力士参孙的大利拉,在警局作证指认如戈,后者的身分因而曝光,立时成为全国追缉的要犯。胡塞尔以小女生脸部被警察威胁修理的特写镜头直指暴力之存在,而且小女生的脸部成为影像焦点所在,更能将观众的注意力聚焦于戈尔德思亦庄亦谐的剧文上(注4)。
第十二景〈火车站〉以火车奔驶于铁轨上的影像意示这场戏的背景,遭到通缉的如戈在这场戏里濒临崩溃的边缘,来来往往的乘客在他眼里全是杀手的化身。「看这些疯子。瞧他们不怀好意的样子。这些人都是杀手……他们的脑袋只要收到一个最小的信号就会大开杀戒」(226)。这是全戏唯一以实景录影交待剧情发生所在的场景,作用在于凸显开场戏里提及之人生轨道的表演论述,而且放大的火车奔驰影像生动地塑造本场戏里心灵幻象的空间。
以上利用录影影像烘衬精练的剧文,或强调重要的表演意象,同时也点出了媒体、影像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其他执导本剧的导演不免大加发挥之处(注5),胡塞尔则未直接触及,而是旁敲侧击。例如四部置于舞台地面上的闭路电视,于全场演出中固定播出彩色切分成廿四小格之分割画面,色彩亮丽,但画面转换甚缓,画面的内容(大自然与昆虫的生态)与演出无直接关系,却无时无刻不在,胡塞尔似以此暗示存在于现代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媒体与影像。
另一方面,胡塞尔引用不少媒体或刻板人物形象:第十景中儿子遭如戈劫持的「太太」(F. Marcq饰)仿玛丽莲梦露的造型亮相;「小女生」(S. Delcart饰)胖嘟嘟的脸庞与圆圆的身材宛如一个长大的洋娃娃;头戴一顶呢帽、身著一袭黑色风衣,本戏中的警探吻合电影私家侦探的刻板形象;将自己妹妹「小女生」卖到妓院的「哥哥」(K. Barras饰)打扮如色情杂志里的人妖;「姊姊」(A. Delatour饰)一袭黑色皮衣下穿的是妓女的行头;上文已述在地下铁车站迷路的「老先生」与小丑相距不远,等等。舞台上这些眼熟的身影,明白地点出现代生活环境中各式媒体影像充塞的景况。事实上,真实社会里的主角──义大利的Roberto Succo──正是我们媒体化社会的犠牲品(注6)。
发扬肉身剧场的震撼力
在迈向导演的路上,胡塞尔深受原籍伊朗的美国导演雷查.阿布多(Reza Abdoh)影响。简言之,阿布多的剧场深入挖掘肉身躯体的表演潜力与张力,他的演员常在台上公然穿脱,演员热切的身体,比起台词,更能表达角色内在的驱力与骚动。阿布多喜挑战常人对躯体、性别、扮装与欲望的既定概念,因此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在他的作品中司空见惯。胡塞尔深受启发,也大力刺激自己年轻的演员与台词建立一种肉身的关系,尽情开发自己对台词的各式幻想。而年轻的演员为狂热的情绪与欲望所激发往往不惜自我暴露,大胆赤身露体表达最深层的内在骚动(注7)。
于《侯贝多.如戈》一戏中,两场裸戏均处理得剧力万钧。其一是居全剧正中的枢纽场景〈就在临死之前〉:苦闷的如戈在一家酒吧借酒装疯,他和酒吧里的保镖大打出手,最后累极,于黎明曙光里沈入梦鄕,人虽未死,但已距死期不远。
这场关键戏最难处理的部分,莫过于开场如戈引雨果长诗《世纪传奇》第十二章第六节爱琴海上罗德岛上巨大太阳神石像的呐喊。在笔者看过的其他演出中,这段引言往往是喃喃道出,宛如梦呓,雨果原诗的气势与力道完全丧失殆尽。
在胡塞尔的演出中,如戈全裸先行出场独自立于台上,伟岸、孤立,背景银幕整面刷蓝,一股烟雾缓缓地从舞台两翼渗出,逐渐弥漫全景,他正面对著观众怒喊:「就是因此我被塑造成运动员。/今日你的震怒成全了我。/喔大海,我站在神圣的底座上无比巨大/你汹涌的波涛无法侵蚀我的双脚。/赤裸、坚强,前额沈入浓雾深渊」(195)。
如此具震撼力的处理手法不仅充分展现巨大石像张口呐喊的惊人力量,且强劲地点出全剧太阳神的重要指涉。接著,保镖与妓女方才陆续登场,他们在绝望的心态下大跳劲舞。全裸的如戈与周遭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的确像是旁人称他之「疯子」,他甚至对著不通的电话说话:「我要走了。我得马上上路……我得走了因为我快死了。反正,谁也不关心谁。没有的事!男人需要女人而且女人也需要男人。不过说到爱情,男女之间没有爱情……我相信没什么好说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一年、百年,都是一样的;迟早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198—99)。此景中裸裎现身的如戈,更能突出主角于生命危机时分自我剖白的情境。
结局〈侯贝多逐日〉,全体演员全裸演出。这场高潮戏原应只见如戈一人于日正当中逃到监狱的屋顶上,其他人犯只闻其声,未见人影,突然之间刮起一阵暴风,如戈最后于正午「仿佛原子弹爆炸一样耀眼的末世景象中」坠楼(240),全剧终。
胡塞尔则反其道而行。他让代表囚犯的四名演员裸身分别爬上四部闭路电视的轨道杆上,直视前方,分别道出剧中囚犯眼看主角爬上监狱屋顶的惊险过程,演员全身的肌肉由于用力因而全面绷紧,危急万分的情势眼看一触即发。此时的如戈则相反地,赤身留在地面上,直至尾声方才在现场观众伸出手扶住身的状态下,跨上中央观众席的椅背上,踏著逐渐往上升高的椅背出场。这也就是说,如戈并未在舞台上摔下,而是相反地,逐渐爬高,最后消失于最高之暗处,「升天」的象征意味显而易见(注8)。全体演员赤裸裸的演出强化了结局撼人的力量。
无法逃离的梦魇世界
采表现主义编剧的《侯贝多.如戈》于写实的大背景中,不时浮现视角扭曲的梦魇情景。胡塞尔则透过选角表达另一种心灵梦魇的观感。他用六名演员扮演剧中廿多名角色,其中除了如戈一角由固定的演员担纲外,其他演员必须一人饰演数角,因此如戈看来仿佛随时随地都碰到同样的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母亲与他稍后在公园中遇见的一位太太即由同一名女演员出任,饰演小女生的演员稍后又化身为一名妓女。而他在地下铁车站碰到的老头,拿掉圆滚滚的肚子,便成了他在公园里劫持的小孩(注9)。这种情形,从小女生的观点视之,更是令人心惊:她的哥哥维持人妖的装扮,同时扮演妓院的保镖;她的姊姊采一贯的歇斯底里表演路线,同时出任老鸨,最后是她花钱买小女生下海。小女生因此看来永远逃不出这个肉欲横流的世界。
观赏胡塞尔高能量的舞台作品,不免使人联想亚陶(A. Artaud)毕生所追求的一种独立于言语之外的具体、物质化舞台表演语汇,这是一种先行诉诸观众五官的舞台语言,熔音乐、舞蹈、戏剧与多媒体为一炉,表演意象强而有力,演员精力迸射,全场演出爆发惊人的能量,而且意蕴丰富,丝毫不让人觉得导演哗众取宠。在此同时,胡塞尔又能兼顾剧文的重要性,甚至于《侯贝多.如戈》一戏中,特别凸出剧文举足轻重的地位,殊为不易。
注:
l.Le théâtre de la mort, T. Kantor, éd. D. Bablet, Lausanne, L'Age d'Homme, 1977, p.20.
2.M. Vinaver, "Sur Koltès", Alternatives theatrals, no. 35-36, février, 1994, p.10。另请参阅拙作〈不同凡响的戏剧世界〉,《戈尔德思剧作选》,桂冠出版社,1997,页262-66。
3.引文见拙译著《戈尔德思剧作选》,桂冠出版社,1997,页237。以下出自本剧的引文皆直接于文中注明页数。
4.例如:
探长:「你知道他叫什么?你一定知道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小女生:「我知道」。
探长:「说」。
小女生:「我知道,而且很清楚」。
探长:「小女孩,你在开我们的玩笑。你想挨耳光吗?」
小女生:「我不想挨耳光子。我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一下子说不出来」。
探长:「就像这样子说,你说不出来?」。
小女生:「名字就出来了,已经到舌尖上了」。
探长:「舌尖,到舌尖上。你找耳光打。」(204)
5.详见拙作〈暴力、媒体与戏剧〉,《表演艺术》,第六十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页18-25。
6.Roberto Succo于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义大利北边的Trevise城落网,翌日所有的媒体与记者皆闻风赶至,正巧目睹Succo利用犯人外出散步的时机,趁狱警不注意的当下,爬到牢狱的屋顶上对著媒体记者大声喊话,并拾起屋瓦砸坏地上的汽车,且开始宽衣解带。底下站的「观众」群起哗然,Succo受到鼓舞,将身体吊挂在电缆上来回摆荡,最后手一松,人从八公尺高的屋顶摔下,不过只受了一点轻伤。三个月后,他在狱中用塑胶袋闷住头部自杀死亡,详见拙作〈疯狂杀手或神话英雄?(上)〉,《当代》,一九九八年六月,页76-78。
7.胡塞尔引叔本华之言自我表白:「性关系在人的世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性关系是所有行动隐而未现的中心,却到处遭到遮掩。性本能是所有战争的原因以及和平的目标;它是一切严肃行动的基础,一切玩笑的目标,一切风趣话永不枯竭的泉源,所有影射的关键,所有无声符号、所有未表白的提议以及所有偷偷摸摸的视线的解释,是年轻人每天的希冀而且通常也是老人的渴望,下流者成日为此顽念所缠,而端正之心灵亦无时不思及此」,引文见Dossier de Presse, Compagnie Utopia,2000.
8.按密特拉崇拜仪式之观点视之,主角肉体虽亡,但灵魂将得到永生。有关戈尔德思是否将一杀人要犯神话为英雄的争执,详见拙作〈疯狂杀手或神话英雄?(上)〉,页84—88。
9.这个「老孩子」符合剧文所提及之小孩比实际年龄大许多的情形(209)。
文字|杨莉莉 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