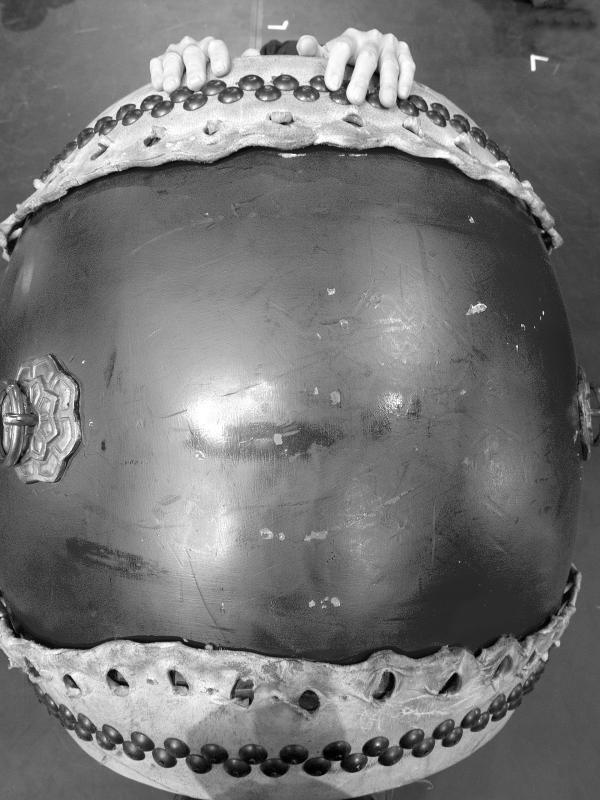很少音乐家像朱宗庆,在访谈中一直把自称是「乡下孩子」挂在嘴上。
朱宗庆是来自台中的乡下孩子,
是从台语歌星文夏的歌,及学校的升降旗典礼开始他的人生音乐课,
参加学校的管乐队时,他所能见到「职业音乐家」是庙会里和丧葬上的康乐队。
乡下孩子朱宗庆进了国立艺专,才发现自己努力吹小号的嘴形是错的,
那改学萨克斯风好了,结果麻烦更大,
因为学院派里没有人主修这种只在歌厅出现的乐器,
音乐系里流行一句话:「不会吹,不会拉的就到后面去打鼓吧。」
没想到,这个没有人要坐的打击乐位置,
赶上台湾七○年代大量现代作曲家创作的年代,
打击乐喧宾夺主地成了朱宗庆的最爱,
同时也让他站上台湾打击乐界教父的地位。
两根棒子,玩真的,
一九八六年,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
这位来自乡下的音乐家把现代打击乐再带回民间庙口、广场,也带至了国际上;
而打击乐这个二十年前最冷门的器乐,
在台湾,现在成为仅次于钢琴的最热门选择。
卢—最近几年击乐音乐节请来的节目有各种跨领域的变化,例如与影像或剧场的结合。我好奇,如果有这些表演趋势上的变化,团员的每日训练是否也有不同?
朱—朱团对团员有一定基本功的要求,例如一定要会弹钢琴,会弹木琴、会打小鼓、低音、传统打击乐,这些基本功不会因为趋势的变化而改变,环境在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有新的尝试与因应,但只要最专业的领域能把握,各种环境变化都可以。
我前天才带北艺大学生去韩国交流演出回来,在那边造成疯狂。韩国第一位打击乐教授朴光绪,也是我在维也纳时的同学。我们都希望在教育体制里改变学生对表演的看法,学打击乐并不是一定要进交响乐团,我们的表演风格也影响了他们,培养出内在对音乐有所感受,上台应是一种享受,而不只是刻板的正襟危坐。
马友友在报上说,小时候他一直不喜欢练琴,一直到有一天他长大到自己感受到音乐的力量,音乐开始与他产生不同的关系。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感受到艺术的美,那他只是一个「匠」。
卢—谈谈你当时是如何开始走上打击乐这条路?击乐演奏有没有明显的师承体系?
朱—有一次在立法院,有人问我,为什么所有的评审都是你的学生?这没有办法,因为我是第一代,要等到打击乐界不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大概就要等到第三代了。我觉得有没有师承这是时代的问题。现在的击乐学生问起师承就会很明显了。
但我那一代不一样。我本来是学管乐的,初中起就是学校管乐队的队长兼指挥,从参加学校升降旗典礼开始吹起的。因为哥哥后来也在学校里担任管理乐队的行政人员,我有机会去玩各种乐器、小喇叭、萨克斯风、爵士鼓等,后来到了艺专,学校乐团里需要鼓手,就指定我去,对于打击乐的演奏,一开始只是根据指挥的指示去做,有时候甚至是模仿唱片,然后经验累积,很多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后来两位老师影响了我,一位是日本作曲家北野彻,当时省交请他来台湾一个月讲座,我、连雅文、陈扬都跑去当他的学生。另一位是麦兰德,是文化大学请来的美籍打击乐家,我已在艺专音乐系四年级,在系主任史惟亮的介绍之下,我也到文化大学去上他的课,我、连雅文、陈扬、徐伯年都成为第一代的打击乐家。这两位老师应是启蒙台湾打击乐视野很重要的两位人物。
卢—你认为在他们身上分别学到的是什么?
朱—北野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规」,而不是谱拿来就开始打。按步就班的学院式学习。有一个环境上的背景,事实上推著我走上这条打击乐之路。七○年代,正是马水龙、李泰祥、许博允、赖德和、温隆信这些现代作曲家开始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们有许多与声音有关的实验与尝试,就常常找我去打,试试这个声音,那个声音;艺专四年级时,樊曼侬的环境音乐节也引进了很多运用打击乐器的现代作曲家,我几乎也和他们一起工作过,对年轻的我而言,反正也没有什打对或打错的负担,也不怕错。
回想起来,我一直感谢史惟亮老师,是他建议我这一条当时还没有人要走的路,同时还介绍我好老师。另外,当时教我管乐的薛耀武老师不但没有怪我「一心二用」,还借给我他收藏的打击乐唱片,打开我在听觉上的视野。
卢—当年打击乐应是很冷门乐器,你不会想放弃?
朱—这回二十周年,美术设计家刘开设计的海报帮我表达了心声。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他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敢拿打击乐来做职业的,是跟天借胆。」现在想想确是如此。当时我还未满二十岁,根本没想到前途,只是一直觉得打击乐好玩,而且当时社会一直给我很多很多机会,推著我去做,让我没有空闲下来去想我可以去做别的有出息的事情。当兵时是国防部示范乐队的打击乐手,退役后二十三岁,到省交担任打击乐首席,这已经是一般人认为学打击乐的最高位置,我后来要出国的时候,有人说你不用出国,就算出国回来也只不会再比这个位置更好。
我出国之前只是喜欢打击乐,没想过未来是不是当什么演奏家。所幸父母从未反对,他们心目中曾有过的期待可能是回来之后当个公务员就好了。而等我二十五岁取得打击乐演奏文凭要回国时,素不相识的马水龙老师写了一封信给还在维也纳的我,希望我为即将成立的艺术学院音乐系规划五年学制的打击乐专修课程,这也是台湾破天荒第一个打击乐主修。这又让我继续投入打击乐在台湾专业化发展的开始。
卢—到那个时候,为什么马水龙会觉得有需要在音乐教育里出现打击乐专修,是觉得现代音乐的作曲趋势里已有需求出现?
朱—作曲家都比演奏家思考得早,第一马老师看出打击乐应该和管乐分开发展,第二他认为台湾的打击乐应该更大幅提升。我在回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开始疯狂在维也纳、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各国找打击乐教学体系的资料和谱子。演奏、推广、教学、研究是我一开始就设定的四大目标。但在参考了各国的教学体系之后,觉得最重要的是也要有自己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作曲家合作。朱团从创团至今委托作曲有九十多首,编曲则更超过三百多首,当时一般都认为「国人作品」是票房毒药,我不相信,觉得这是建立自我特色最好的方式。
卢—第一届招生时有多少人来考?
朱—第一年来考时只有三个,但我没有录取任何一位。没有学生,也就没有了这一年在艺术学院专任的教职。我不能为了找一份大学教授职业就录取了不适合的学生。但第二年就有好人才出现了,现在每年招考大概有七十多个学生报考。
刚成立的时候,学生会要求说他只要学木琴,其他的不学,我说不行,你必须全部都学,当时学生反弹得厉害,但我很坚持,现在看起来这个决策是对的。因为你必须知道各种乐器可能的音响与各种声部的关系。
卢—朱宗庆打击乐团一九八六年成立,我记得有几场户外演出是十分轰动的。
朱—我回来时认为推广打击乐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怎么推广?就是让好东西走向人群。并且打破一般人认为音乐是昂贵严肃的观念。所以一回来没多少就和福茂唱片公司签约,做很多当时很多文化人觉得没有办法在影视综艺频道做的宣传,上张小燕的综艺节目,并且到庙口广场做户外演出。我自己从小在乡下长大,很能体会人群聚集在一起感动,但到庙口演出,应该要有适合庙口观赏的曲目,我们改编了很多民谣、节庆小调,结果,活泼热闹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人。后来第二年再受电视台之邀又到祖师庙再去录制成节目。
卢—朱宗庆打击乐团有很多在各地精采的演出,我在观众席常看到观众的投入与听完后的开心,但对你来讲,二十年来这么多场演出,有没有那些演出是有深刻意义的?
朱—这么多年来有三场是特别让我无法忘记的。一九九四年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幕时,《中时晚报》邀请我们到高雄演出,那一晚来了一万多个观众,美术馆广场上坐得满满,演至一半,却下起倾盆大雨,团员们还措手不急的时候,忽然间许多观众冲上台,我们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不知他们要做什么,后来发现是要帮忙团员拿塑胶套盖住乐器,心疼乐器淋湿了,台下没有人要走,还好雨一下子停了,观众又帮我们掀开塑胶套,恢复演出,演出之后,美术馆放起烟火,观众和团员们都兴奋得难以言喻。
第二个演出,是为一位得脑瘤的重病儿童在荣总大厅的演出,他最大的心愿是听朱团演出《鳟鱼》五重奏,因为这首曲子是这位病童和爸爸妈妈全家最喜爱的曲子,为此我们还特别改编了这种曲子的打击乐版本;但到了现场,我看到孩子的父母就楞在那里,这才发现他是一位在朱宗庆打击音乐教室的学生,我本来以为他已经痊愈了,但没想到却又在荣总里见他最后一次。孩子已经是在昏迷状态里,在父母陪伴下听完我们的演出。
第三则是去年在俄罗斯的演出。之前,朱团在美国各地包括林肯中心的演出,那种「攻进」美国观众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但俄罗斯不同,我们是第一批到莫斯科演出的当代表演团体,主办单位也大力宣传,观众来不是因为知道我们有多好,而是对台湾的表演团体有好奇,结果从第一首开始,每一首结束后观众就大呼大喊,以他们的环境,他们对打击乐的观念是比较保守的,我们安排的曲子包括改编传统的《小河淌水》,让他们感受中国式内歛婉转的情欲,几乎每一场都让他们为之疯狂。
卢—朱团的表演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你们的表演总是让观众感到开心,快乐的,你认为这是你们广受欢迎的原因?
朱—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热情。朱团不是为了制造快乐而让大家感到快乐。很多东西虽然是有意识地追求,但快乐只是其中之一。团员必须把真正的热情摆在台上,专注、完整才能让观众感受到与音乐的一起投入。事实上我们的团员不只是台上很热情,台下也很热情,我希望我的团员及学生们对社会事务的关心要广泛。
刚刚说到在荣总演出的经验,让我发现音乐可以给人的慰藉,后来我们去了各地的医院、养老院,也去过一次监狱演出,这些都是很少对外说的。有一回去了一个平均年龄八十七岁的养老院,演完之后,老人家动作慢,掌声是慢慢响起,然后看到他们的眼泪,有一位老人握著我们的手说:「我们都要走了,你们为什么还来!」至于监狱,我会非常愿意为狱中受刑人训练一批很棒的打击乐团。对我而言,不管是做这些社会工作或开设音乐教室,我想要做的是让人能感受音乐的力量,是教音乐而不是教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