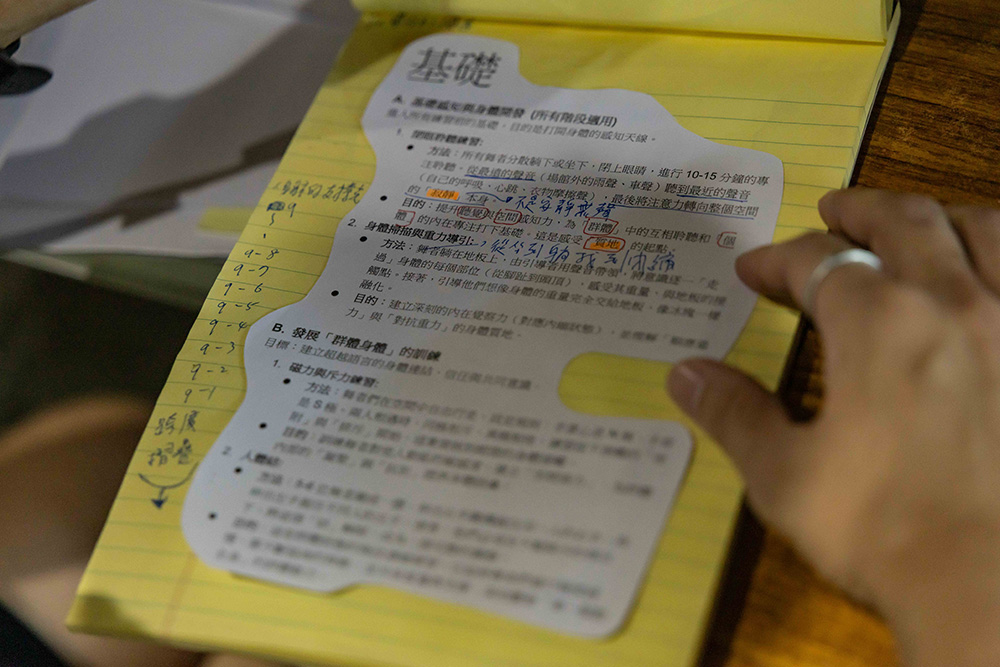虽然在研究所主修剧场导演,却也涉足新媒体与装置艺术创作,对陈侑汝来说,「快乐」与「好奇」是她一路探索艺术的主要动能,一路玩,一路做,无形中积累了美学观察与导演能量,也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汇;若将这些语汇整理为几个关键字,那应该是:土地,环境,与空间。
在陈侑汝的自我介绍里,多会出现一行字:「剧场工作者与艺术家」。
她在北艺大念导演,亦曾于布拉格艺术学院念了一年的新媒体(New Media),所以她的作品确实不限于剧场表演范畴,过去多有装置艺术的展演经验。但何以剧场工作者无法包容进「艺术家」的词汇里面?陈侑汝回答,不是不能,但这么做是为了提醒自己,「无论是剧场导演,或者是纯艺术工作,两种身分都蛮好的,特别提及『剧场工作』,是希望自己能够时时用一种比较旁观的角度去观察整个生态与环境,这样我才能持续吸收与学习。」
导演经验丰富的她,现在仍会想起早期当导演助理时的经验,她说:「成为助理是非常有趣的事,你不用真的下决定,而是去协助人下决定,再把某些事情记录或整理完成,在这样的状态下,有时候更能看清楚那个人的创作可能会是什么,也能更清楚地看见作品的改变。」
分明置身其中,却仿佛旁观一切。陈侑汝的旁观并非漠视,而带著一种冷静的从容感。或许是因为这样,本次台北艺术节的《北车写作计划》系列作品,她一口气揽下了三出导演工作,与三组不同的编剧、演员合作,却能激荡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火花。
单纯觉得快乐
当初独自从高雄来北艺大应考,第一年落榜,第二再战,目标皆是与戏剧有关,然当时却不敢说自己真看过什么大戏。「我大学以前的成长背景多跟艺术相关,国小念舞蹈班,国中念美术系。」她推测应该是受热爱艺文的父母薰陶所影响,但实际上当时做这些事情都没想得太多,也谈不上什么梦想或抱负。
「只是单纯觉得快乐。」陈侑汝说。
大学以前,志愿比较像是删去法,删去不擅长的科系,尝试自己尚有把握的那条路,而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快乐。「当初决定要去布拉格当交换生也是,总觉得在目前的环境里好像无法再有新的刺激,所以想去其他地方看看。」
出发前,她脑袋里想得都是要「好好地玩」,「之前上台北念书的时候,也只是想说要离家远一点。」并且强调「我去布拉格的时候也没想说要把自己的创作推到什么极致喔,完全没有,就只是想到那里看看一些有的没的。」
虽是这样说,但陈侑汝像是一不小心就会把事情做得太认真的那种类型。而她也确实在新媒体尝试到不同的艺术领域,有别于国内戏剧系多演绎经典文本趋势,新媒体的学习则是要她从零到有产出一件作品,她必须在巨大的空白中寻找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且想办法将之聚焦为某种可见可感的作品。
她一路玩,一路做,无形中积累了美学观察与导演能量,渐渐找到了属于她的艺术语汇。若将这些语汇整理为几个关键字,那应该是:土地,环境,与空间。
人与土地的关系,以艺术回应
离开故土,才真正发现每个土地的气味都是不同的。布拉格的远行是一个发现,而2017年陈侑汝出访日本秋吉台国际艺术村驻村则是另一次生命中的转捩点。
「驻村的环境跟都市的状态非常不一样,那里原本是一个观光胜地,后来人口渐少,整个日本又慢慢走向老年化,可以感受到世代明显的断层。」随著自己年纪渐长,陈侑汝开始意识到,人与土地的衰老状态或许是比肩齐行的,「总觉得,说不定在未来我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然艺术终究不是答案的交付者,而是直面这些疑问的角色。
陈侑汝将当时的体悟寄托在土地上,「以异地人的状态在这个环境里,会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事物。」她说,比方说空间、比方说空间之于人的连结性皆然,「土地比较像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所产生出的不同连结,当人移动到某个地方,周遭给予的环境,无论是声音或是空气中的风、甚至是摆设的改变,都会让我们联想到琪他的经验。」
而她观察空间的感受又不仅限于视觉层面,陈侑汝提到自己相当在乎声音的质感,「驻村的时候,和许多艺术家在一起吃饭,其中一位日本人非常喜欢蒜头,吃饭一定要磨蒜头来配,当时他坐我旁边就开始在磨,我忽然觉得那个磨蒜头的声音,跟前些日子我们去看烧山祈福的声音很像。」她说自己当场就把手机拿起来录,后来回放来听,感觉就像抽掉了视觉以后、以听觉的感受让脑海里的记忆与另一个空间相连。
她以此回探土地的意义,又或者说,以此回望人们生活过的痕迹,如何凿刻成环境的样貌。
人物小档案
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与剧场艺术研究所,主修导演。
现为艺术工作者,个人创作常与当地环境、声响结合,透过细微生活、经验观察,提出人与空间、身体、声音之关系,创作领域包括剧场、视觉装置、声响录像等,作品曾多次获台新艺术奖季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