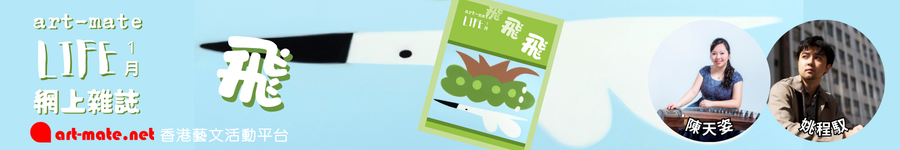网路上随手一点,各式影片扑面而来,和以前资料得来不易的时代真是完全不同了,本文就从一段唱片受难记的回忆写起吧。
长辈得到一张京剧新腔唱片,欣喜若狂,八百里加急召唤我去他家一起听,还愿借我回家听一周。我也毫不藏私,转头就告诉戏迷好友,他兴奋极了,一早开车恭迎唱片,双手捧接,供奉于后座,准备晚上回家享受。
当晚接他电话,颤抖、呜咽、哭泣,我直觉出事了,忙问唱片在哪里?他啜泣半天才说出 : 「唱片在洗澡!」
飞奔而去,果真躺在浴缸!
怎么回事?原来酷暑高温,车里的唱片弯曲翘起,此刻正在冲澡降温。我们战战兢兢捞出擦乾,放上唱机,居然还能听,但唱腔高下闪烁、摇曳生姿,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面对长辈!
这是早年听戏的实况,至今犹记得那一刻的惊心动魄。
泡澡的是谁呢?张君秋,崔莺莺。经此一番洗涤,《西厢记》在我心中地位,更一夕拔高好几层,我也常把这段唱片蒙难记当作张腔动人的例证。
而这只是同温层刻骨铭心的记忆,沉浸在其中的我们,很难想像圈外人的想法。
有一年上海京剧院来台演此剧,散戏听一群观众说 :「好可怕,满台蟑螂!」我一辈子都在戏里,从没想到张郎╱蟑螂的谐音会惊吓观众,当然我知道这类闲言听听笑笑就罢,然而我无法忽略第2次的外行冲击,那是我学生的疑问。
我自教书以来渐能站在圈外人立场看我热爱的艺术,试著搬开障碍物,为新观众打通一条欣赏的道路。《西厢记》最适合当教材,古典文学名著加上张派魔力,应可抓得住同学吧,但一开头就触礁。同学问我,不是爱情戏吗?为什么崔莺莺一开口就说「烽烟满目,扭转乾坤」,还要学木兰从军?
天哪,我竟从没发现!
「满目烽烟迷关塞,扭乾坤要等待天下英才」,「那木兰当户织停梭惆怅,也只为居乱世身是红妆。」这几句谁不会唱?早被张腔迷住了,根本没管词意。经此一问,才仔细思考,虽知是要引出莺莺对与表兄婚约的忧心,但这几句的确沉重。
同学也对长亭送别的悲怆感到讶异,离愁别绪,想像中应是低回幽缓吧,仍当以缠绵为主,何以如此澎湃激动?
何以如此?京剧原本流行的是荀派《红娘》,莺莺例由「二旦」饰演,几句摇板,不能抢主角光彩,这是舞台潜规则,事关主配伦理。观众著迷于荀派的娇媚酥嗲时,田汉却觉得「崔莺莺不见了」。
以「救亡图存」为职志的田汉,1958年新编《西厢记》,以莺莺为主角,写了她争取爱情的连串积极动作,从孙飞虎抢亲开始,莺莺就有主动性,唱出五大理由自愿挺身而出,每一步都有主见,结局更改为张生落第而归,遭老夫人羞辱赶出,莺莺私奔,标准反抗封建的女性形象。
田汉创作态度与齐如山等文人不同,编剧不是为了烘托演员,剧本是个人「言志」的载体,扭转乾坤的理想早已「溢出」莺莺,根本是田汉自己人生理念的投射。他下笔编剧时并未想到由谁主演,剧本完成后,写了一大篇创作理念,最后淡淡加了一笔「有幸得张君秋主演」。对张君秋而言,他为莺莺设计了华丽璀璨又宛转跌宕唱腔,成为「张派」开宗立派的关键。
编剧和主演看似相互成全,但问题来了,张生落第、莺莺私奔,是剧本冲突矛盾最高潮,但各团却常删去不演,只到〈哭宴〉长亭送别为止,理由显而易见,因为〈哭宴〉反二黄是演唱高潮,而后的场子和唱腔都零碎,乾脆删去。剧本创作总要到搬上舞台才告完成,即使「戏曲改革」时期编剧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但表演设计与演员表现仍左右成败。
本专栏上篇写过《杨门女将》遭政治监控,幸有采药老人言派老生开出新局,本文所谈的《西厢记》是戏曲改革负责人主导者田汉的剧本,文辞优美,但反抗封建,沉重严肃,与爱情主题并不相合,戏迷被张腔魔音圈粉忽略词意,一离开同温层便产生疑问。
我在国光规划戏码时便常犹豫,好几次用不同的方法融合《西厢记》和《红娘》,但经典唱腔总想保留,因而形成莺莺红娘各唱了一大段四平调的音乐重复。有一回参考越剧,新增了几段莺莺的犹豫和红娘的劝说,但因不是原来经典,老观众陌生,没办法留下印象。
有时想想,我真多事,想这么多干嘛,为什么不能回到当年纯听唱片的年岁?
但老师和剧场工作者种种身分让我想太多,回不去了。
而我这套想法,会不会就像田汉的救亡图存?不同的是,他为国家,我为京剧。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