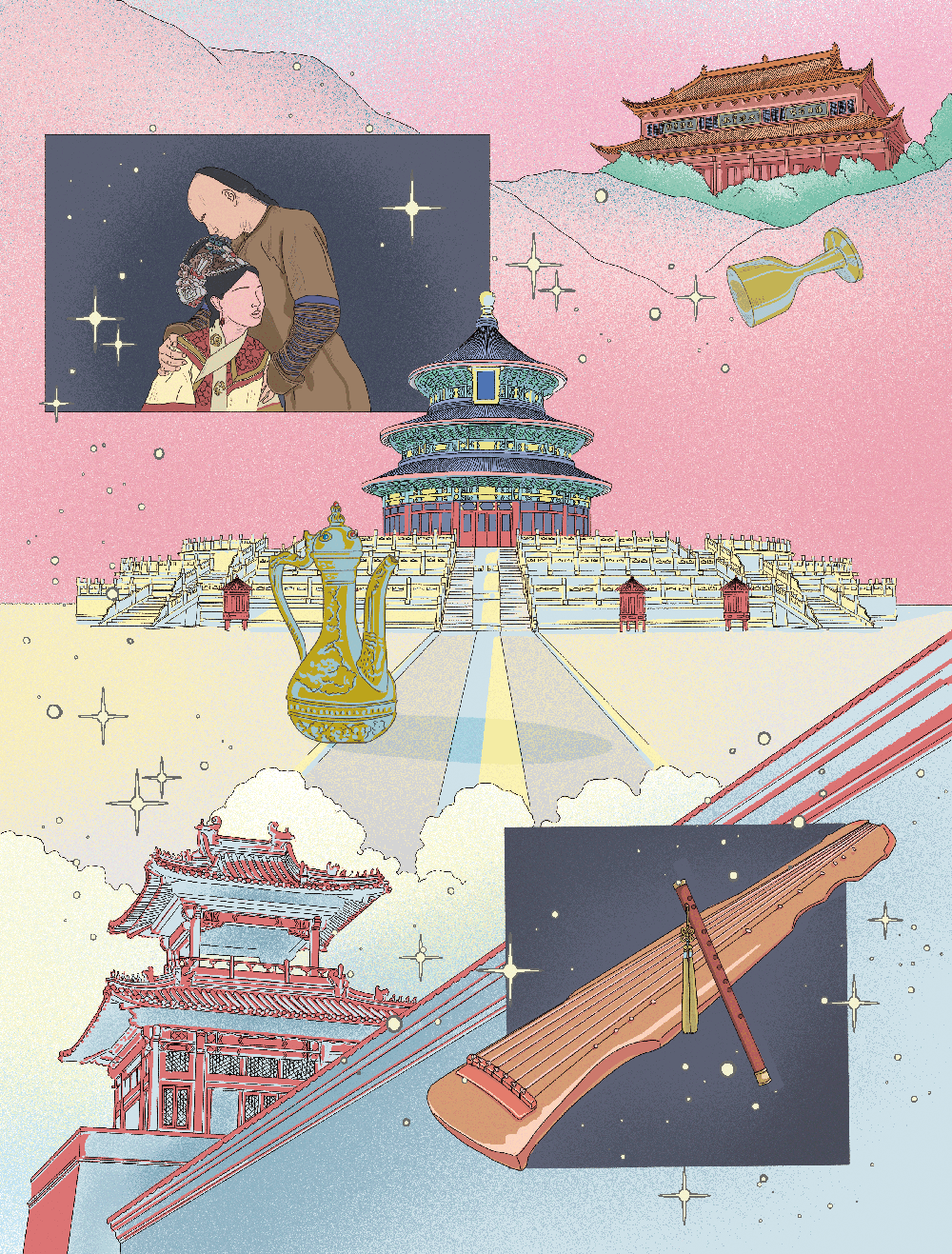在巴爾巴筆下,葛羅托斯基的神話性色彩漸然褪去,年輕劇場人的靑澀、笨拙、孤僻、狂熱、奉獻、達觀使得大師更具人性,而値得一書的是,作者不畏劇場硏究瑣細的罄竹難書,將整個葛氏體系的崛起置放於宏觀的歷史脈絡,同時那些曾經在葛氏探索中投下心力的無名英雄,也得到較爲公平的關注。
巴爾巴與葛氏的早年劇場探索
《灰燼與鑽石之境:我在波蘭的學習生涯》Land of Ashes and Dia-monds: My Apprenticeship in Poland是作者尤金尼歐.巴爾巴的劇場思考與葛羅托斯基早年劇場時期的探索互棲共生,半自傳體的書寫風格,以出席歷史現場之姿,不忌繁瑣地鋪陳六〇年代葛氏陣營篳路藍褸的細節,旁徵博引釋出極其詳盡的第一手資訊。尤其巴氏詩化般的見證與一方大師的洞察力,將葛氏的劇場冥思,放在不同的文本以論述,爲早年葛氏系統的發展重新下註。
本書分爲兩個部分──灰燼與鑽石之境:我在波蘭的學習生涯;與親愛的欽(Kim)(註):二十六封葛羅托斯基給尤金尼歐.巴爾巴的信。在第二部分二十六封來自葛氏有若劇場歷史文件的基礎下,第一部分〈我在波蘭的學習生涯〉中,巴氏時而踏出場景,爲葛氏系統繁鉅的脈絡,提供具個人的剖析與詮釋,另一方面時而悠揚、時而銳利的筆觸,不厭其煩地回溯每一個名字,每一道細節。在巴氏筆下,葛氏的神話性色彩漸然褪去,年輕劇場人的靑澀、笨拙、孤僻、狂熱、奉獻、達觀使得大師更具人性,而値得一書的是,作者不畏劇場硏究瑣細的罄竹難書,將整個葛氏體系的崛起置放於宏觀的歷史脈絡,同時那些曾經在葛氏探索中投下心力的無名英雄,也得到較爲公平的關注。
就劇場史的角度觀之,巴氏認爲,葛氏的硏究集二十世紀前半劇場改革先鋒之大成:就斯拉夫民族的傳承而言,上可推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anislavs-ky)、凡欽丹柯夫(Vachtangov)、梅耶侯德(Meyerhold)、艾森斯坦(Eisen-stein);就表演文本與文學文本互融與對抗的傳統而言,則有梅耶侯德(Meyerhold)與布萊希特(Brceht);而不再將演出看待爲劇場唯一目標的傳統,溯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Sanislavs-ky)、舒勒欽斯基(Sulerzhitski)、柯波(Copeau)、歐斯德瓦(Osterwa)。葛氏延襲前人的探索,在六〇年代的波蘭社會主義背景之前,意義相形深刻。一直以來,葛氏在個人乃至集體層面尋求精神性的徹底解放,與古典文本間崇拜與冒瀆的辯證對話,在巴氏娓娓的陳述中,找到社會性的參考點。
哲學影響深邃
在葛氏儀式化的劇場行動中,挑戰社會迷思與集體原型間,表演者技藝的淬煉,實爲葛氏工作系統的基石,然其工作的旨趣卻不僅止於表演方法論而已。葛氏對人類基本處境與本體問題的觀察、進逼極致的劇場策略與近乎宗敎的精神性色彩中,實蘊藏更爲深邃的哲學思考。巴氏直陳,葛氏除靑年時期即熟諳東方哲學,上自各流派的印度宗敎哲學(Hinduism)、香卡拉(Shankara)的吠陀哲學(Advaita Vedanta)、到潘達惹利(Patanjati)的論述哈達瑜伽(Hatha yoga)、大乘佛敎(Mahayana)及自其衍生的禪宗,乃至那迦鳩那(Nagajuna)的新智慧敎派(Mad-hyamika),及其主要敎義Sanyata──空無哲學等,常成爲二人話題的焦點。
巴氏更進一步指出,印度宗敎哲學的影響,在葛氏始入劇場之初即見端倪。一九六〇年二十七歲的葛氏在接掌十三排劇場(Teatr 13 Rezdoz)一年之後,提出《濕婆之舞》Dance of Shiva來陳述其劇場理念。這樣以印度神祇結晶般多層切面的意象,來呈現主客體意識狀態的矛盾結構與文本間互動對峙的律動關係,在巴氏的詮釋下,濕婆之舞:
是一種關於實體的個人視界,就演員的技術層面而言,可被翻譯成有機性(organicity)──脈搏與律動(pulsa-tion and rhythm);在戲劇策略的層次上,可被視爲同時對立存在的極端──崇拜與冒瀆的相互辯證(dialectic of apotheosis and derision);在美學層面上,則爲拒絕製造幻覺,在幻覺的收縮、擴張與對立間,濕婆始舞。(55)
在葛氏對本體認識的思考及系統方法論的建立中,新定法(via negativay)可被視爲其劇場階段發展的里程碑,據巴氏的分析,乃得自Sanyata「空無」敎義的啓發:
「空」是主觀與客觀沒有分別的非二元對立狀態……「空」處於是與否、存在與非存在之間的連接點,是一種時刻,於其中認同與拒絕,堅信與拒斥互生。在佛敎傳统中,「空」是對此一世界的絕對拒斥,非藉由理性思考,但透過經驗所發展的技巧。那是一種存在於確認與否定,行動及節制的訓練。每當一個人欲求開悟之時,悟便不可得,因爲那仍屬於一種欲求。其間存在二元對立:一個以被欲求爲目標的自我(self),與一個以非自我(non-self)爲目標的完我(one)。眞正的成就在一個人不再欲求成就之間而達成。在《邁向貧窮劇場》一書中葛羅托斯基以此一境界,應用於演員身上,「心理必須處在一種被動的穩定狀態,去了解一個積極的角色,不欲求作什麼,卻無法不做它。」(49)
在巴氏所揭露與葛氏天文地理無所不及的私密對話中,東方宗敎哲學思想彷彿主導著作者對葛氏體系的解讀,巴氏的洞察雖晰利透徹,讀者或可不必依以爲窺探葛氏劇場探索的唯一透鏡,終究一個思潮的崛起,難以在一人的筆下獲得全面性的觀照。而縱貫全書回憶錄般的書寫,或許正是對讀者的提醒:《灰燼與鑽石之境》一書實爲作者場面調度下,葛氏與(波蘭)劇場實驗室的發展斷代史。
註:
欽(Kim)原爲Kipling小說Kim的主角。陪伴及保護年長的西藏喇嘛印度朝聖,尋找救贖之水。在二人信函往來之時,巴氏與葛氏經常以喇嘛與欽暱稱彼此。
參考文章:
陳惠文(1999)《留白之後:葛羅托斯基在卡地夫》,表演藝術雜誌第七十七期。
文字|陳惠文 威爾斯大學劇場碩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