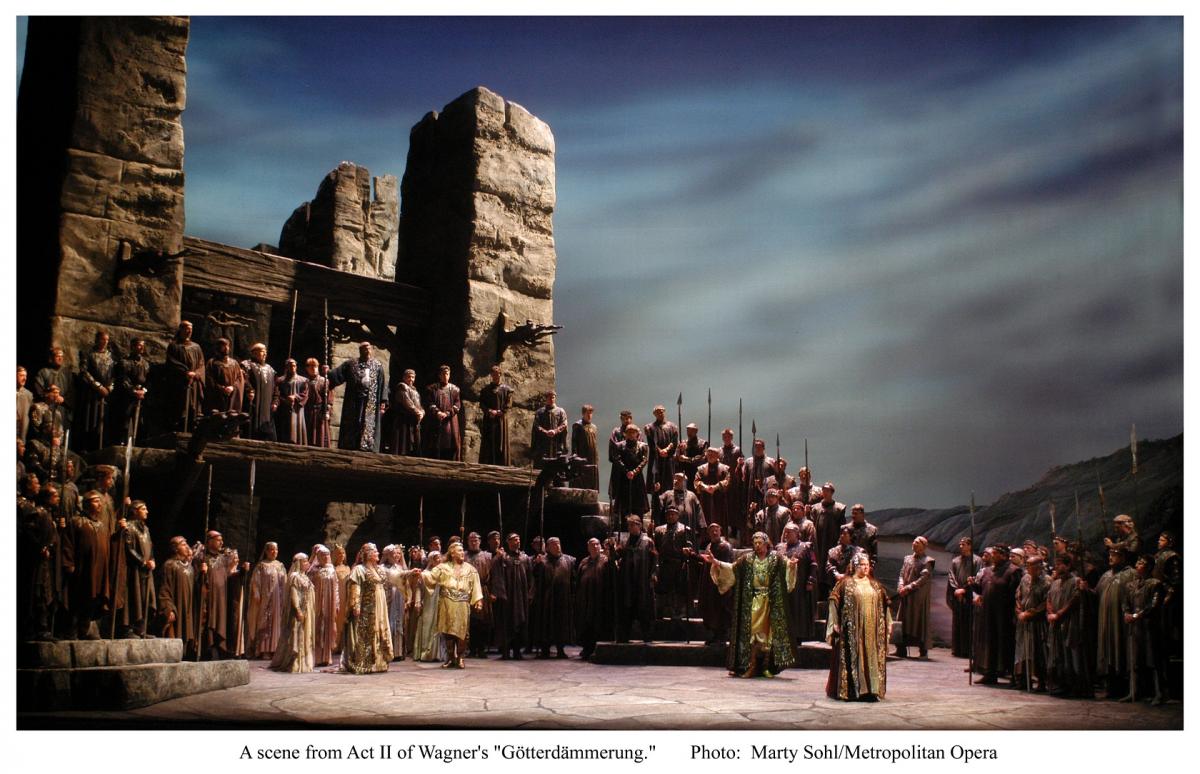來自中世紀的一則神話傳說,如何在歷經文學家的敷陳說演下,到華格納手中揮發出強大的魔力,進而讓世人沉迷百餘年?華格納到底想透過《尼貝龍指環》說些什麼?是權力的虛無,還是真愛的永恆?
神話,總是特別令人心醉神迷,那千變萬化的人物、曲折迂迴的故事百態,它訴說的再也不僅是一個神話故事那般單純,是人性縮影的映照。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說:「我不是要指出人如何在神話之中思考,而是要指出神話如何在人們心靈運作。」的確,每則神話總會留下些許悵然、情思、渴望或驚喜,那是在人們心中一個始終解不開的謎題,演繹著始終未完結的故事,《尼貝龍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便是如此。
尼貝龍的神話與十九世紀的德國文學
日耳曼的神話文學中,尼貝龍傳說一直是饒富色彩的一段傳奇故事;它隨著世紀的更迭,綿延傳承了下來。中世紀之時的英雄史詩《尼貝龍之歌》Nibelungenlied應是最早遺留下的手稿,一四七二年則又出現冠上《身負鳞角的齊格飛之歌》Das Lied von hürnen Seyfrid標題的手抄,當中講述的多是關於日耳曼神話英雄齊格飛(Siegfried)的蜚語。尼貝龍的魅力歷久不衰,一七七二年它更以散文般的記敘式變體呈現,擺脫了史詩的框架,融入了德意志浪漫散文的元素,帶領著神話傳說邁向新穎的文藝風格。
神話的洗滌確實賦予藝術界無盡的靈感,尤其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更掀起一股應和神話的文學旋風。德國小說家與劇作家傅凱(Friedrich Heinrich Karl Fouqué, Baron de la Motte)在一八○三年首度完成了《打鐵舖中的鳞角齊格飛》Der gehörnte Siegfried in der Schmied的草稿;若干年後,他將此改寫為《北方英雄》Der Held des Nordens的戲劇三部曲,分別為《弒龍者之齊古爾德》Sigurd der Schlagentöter、《齊古爾德的復仇》Sigurds Rache與著重描寫齊格飛與布倫希德(Brünnhilde)之女的第三部《阿絲勞格》Aslauga。一八二八年,劇作家勞帕赫(Ernst Raupach)也推出了五幕名為《尼貝龍的寶藏》Der Nibelungenhort的唸白劇。此外,德國詩人及劇作家赫伯爾(Friedrich Hebbel)也以《尼貝龍之歌》為形,在一八六二年完成了《尼貝龍三部曲》Die Nibelungen Trilogie,包含《長角的齊格飛》Der Gehornte Siegfried、《齊格飛之死》Siegfrieds Tod及《克里姆希德的復仇》Kriemhilds Rache;其將歷史概念與神話傳說並置在同一軸線上來勾勒這三部文學作品,轉化描繪了異教與基督教的紛擾和衝突。
革命性的《指環》
時代的潮流與華格納的創作相互驅動著,在接觸了戈德林(Carl Wilhelm Göttling)的《尼貝龍與吉勃林》Nibelungen und Gibelinen(1816)及默內(Franz Joseph Mone)的《德國英雄傳說的歷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Heldensage(1836)之後;一八四八年的春夏之際,華格納也發表了《浮貝龍:傳說之世界歷史》Die Wibelungen:Weltgeschichte der Sage文集來探討德國諸民族之形成與關係。隨即在同年秋天又撰寫了《尼貝龍神話,作為一齣戲劇的草擬》Der Nibelungen Mythus, als Entwurf zu einem Drama,這雖僅是樂劇的草本,卻已經清楚地揭露了角色輪廓;而華格納耗時二十六年的《指環》創作狂熱,此際更是如火如荼地在他心中炙烈燃燒起來。
一八四九年起,華格納積極展開歌劇改革的運動,發表《藝術與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1849)、《未來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1849)及《歌劇與戲劇》Oper und Drama(1851)等書,闡述其欲擺脫貧瘠的傳統歌劇思維,建造生氣蓬勃的樂劇氣象;也期許著社會於革命時期的動盪不安中也能有突破性的變革。因此,《尼貝龍指環》不僅成為華格納實踐樂劇願景的初試作品,也表現當時破壞性、革新性的反叛情緒,被視為融合浪漫主義、民族主義與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風格的爭議之作,也是醒世之作。
華格納在《指環》中想表達什麼?
從華格納的《指環》不難看出他對日耳曼神話及文學的深遠涉獵,他由多方架構的尼貝龍神話與冰島英雄文學作品中去插補新的素材,修砌屬於他自己的神話;而當中對於熱烈的、溫厚的、晦澀的、戲謔的情感表現,華格納施展著更為豐沛的戲劇張力。《指環》四部曲的程序安排雖導出齊格飛慘烈的一生,但更可窺見神話中諸神由神殿完竣到面對毀滅的過程,意圖指出權力由生至滅所難以擺脫的循環,以及指環魔力雖可載舟、亦能覆舟的覺醒。
此外,後世研究指出,華格納在《指環》中塑造了三位要角,即佛旦、齊格飛與佛旦之女布倫希德。關於佛旦,華格納曾描述他就像人類汲汲營營要達到的目標一樣,代表著高峰;齊格飛則是一個擁有未來性的角色,他並不屬於我們,而是必須透過現世的毀滅而得到重生。對於布倫希德,華格納認為她有著與眾不同的氣質,代表著苦痛,是一位自我犧牲的救贖者,也是一位永恆的女性。
死亡、意志、破除封建的構件
華格納曾表示試圖藉由《指環》來傳遞關於毀滅、學習死亡、意志與變更成規的革新性思維;這是受到一八五四年拜讀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之著作《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的影響,啟發他對於人生哲學的另向思考。華格納寫道:「我們都必須學習死亡,亦即在充斥純粹感官的俗世中死去,恐懼面對終止是寡愛之源,那私愛已枯萎……怎麼為終止而背離恐懼?我的詩會指出方向。」
對於意志,他則表示以諸神領袖佛旦(Wotan)面對極致的悲劇性下場,看清自我毀滅而徹悟的無畏精神來作為代表。而《指環》對於變更成規的投射,則聚焦在佛旦與佛麗卡(Fricka)這對夫妻身上。華格納認為人性缺少易變性,佛旦與佛麗卡的結合造成兩者密不可分的聯繫,而兩人虛無的愛情成為對於不朽與永恆的誤解;劇中佛旦風流成性的行為對其妻造成傷害,華格納描寫出這對怨偶因為道德的桎梏而相互緊鎖,怨懟只是徒增苦悶,恰好也表達出他本身對愛情解放的自由觀。
跨越 vs.制約
《指環》在創作當時最受到爭議與關切的部分是道德的問題。雖強調道德的節制、高尚的情操,但《指環》中強烈濃稠的情感、忌妒復仇的心智和奪取掌控的渴想,皆在在衝擊著世俗的普世價值。
表現最為鮮明的應屬佛旦了吧!在劇中他被華格納設定為悲劇性的角色:《女武神》的第二幕描述佛旦以他的長矛毀壞其子齊格蒙(Siegmund)的劍,使得齊格蒙遭到渾丁(Hunding)的殺害,等於宣判佛旦間接殘殺他的親生骨肉,無不引起一陣撻伐之聲;佛旦所擁有的崇高地位與其所作所為形成了矛盾的對峙,這等於種下諸神走向滅亡的第一顆種子。此外,佛旦與崴崧族人(Wälsung)所生的齊格蒙與齊格琳德(Sieglinde)這對孿生兄妹的遭遇雖令人同情,但兩人的結合悖離倫理,同樣不見容於世;也因為佛旦的不忠,這一波波被詛咒的命運轉嫁到他的子女身上,甚至是他的孫子齊格飛也因而受禍。這一串連鎖效應導致諸神之首的佛旦也無力抵抗,象徵著神並非全能的窘境。
華格納指稱布倫希德在《指環》中扮演一位救贖者的形容相當貼切!布倫希德雖為堅悍的女武神,但自始至終她皆保有感性的心靈,和佛旦的威權與齊格飛的勇武有著強烈的對比,也為全然的陽剛氣息注入一瓢暖流。她在劇中一開始的角色是護衛神殿的女武神;擔任聽從其父掌控的一枚棋子;卻為了保護齊格蒙而背叛父親的指令,下貶為凡人,也因此得以與齊格飛共同體驗愛情。《諸神黃昏》最終景,她壯烈地帶著指環邁向火堆,與已死的齊格飛共赴黃泉,也使得各方爭奪的指環重回萊茵少女之手。在此,燃燒他倆的熊熊火焰好似宣揚真愛的永存,也表示權力拉扯的終結;布倫希德所扮演的幾乎超越了救贖者的性質,相對的,是抵抗佛旦跨越道德藩籬所給予的約制。
誰給的迷咒?
歷時二十六年的構思,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三日在拜魯特音樂節(Bayreuth Festival)上演的《尼貝龍指環》帶給藝術界與社會新的衝擊和啟發;當然,啟發的不僅只有藝文上的靈感震盪,還包括世人都掙脫不了的心靈迷咒——愛與權力!看來,《指環》就像是個世紀大預言一般,一百三十年來,眾人皆在裡面浮游;何時能上岸?又不知是多少個一百三十年的歲月吧!而這到底是不是華格納所設下的陷阱?恐怕是始終解不開的謎題、終未完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