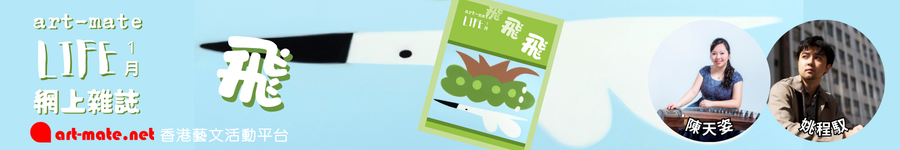真正跳舞的人是要讓靈魂落下到身體,外在的世界造就了我們的人性和編織在我們身上的東西。這種對世界的認識更加謙遜,也更加穩定。自然是創造者,而不是被創造者。人類不是環境的中心。
關於一座山如何才能進入人類的眼睛,人們討論了很久。這種視角上的困難將自然環境縮小了,而人類卻放大了。即使是現在,大自然也常常是由脫離土地及其居民的人來定義的。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生活通常只包括已開發國家的大多數人。我們很少明白,靈魂存在於人類意識與自然萬物的所有交會點上。對於我們的身體和自我而言,皮膚很難成為一個承接器。我們的邊界並不牢固,我們是可以滲透的。
真正跳舞的人是那些從未出賣自己靈魂的激烈自由,從未割斷對自然、神靈、人的連結,也從未抑制對聲音和味道產生身體反應。此外,當這樣的存在跳舞時,所有的時間都消融了;風的輕觸,過去、現在和未來交錯成一個無法形容的永恆光亮。
土地,我們已經習慣中途離席,
只剩殘響,如祖先最後的呼吸。
那山腳的鹽,仍然在,
山胡椒卻已?
不再有回聲。
我們的腳步曾踏實,
但現在,只能匆匆滑落,如碎石般散落山間。
我們不再是大地的延續,
斷裂了,
在穿越城鎮、舞步之間,
這片土地已不再承載我們的重量。
我們曾經咀嚼這片土地,
現在卻無力感知它的味道。
峽谷的岩壁,
巨人輕輕一擊,就裂開了,
不再是完整的,
留下沉默的空隙。
對不起,
我們匆匆離去。
在那遙遠的另一邊,山羌焦急地等待著,渴望與我們分享著跳舞,渴望聆聽我們的故事。但我們早已吞噬了我們,推動著我們不斷前行,渴望抵達那不可知的中心。
即使我們知道,走向水源的地方需要付出相對的身體勞力,但我們仍然無法抗拒,徘徊於恍惚與現實之間,彷彿時間的洪流早已將身體捲入未知的深淵。
在那逐漸成為柏油路的邊緣上,我們成為了一個模糊的「我們」,時間已經不再重要,只剩下這場現代節奏。獸骨相撞的聲音在耳邊迴盪,竹片彎曲插入,被風掃過的空隙中。我們的腳掌輕輕擦過,如泥土般滑膩,腳掌與柏油相觸,這一瞬間感覺結塊的存在,只是我們與土地斷裂了。
你看見了,那曾經屬於土地的我,
皮膚中,風掠過我們,
純淨如暴雨中相擁的石塊,
在這漩渦般的混沌中,
我,化為渺小的顆粒,滑落於大地的裂隙,
握緊的泥土從手中流失,
眼睛低垂,注視著肚臍,
沙粒無聲堆積,
未曾察覺自己已然遠離,
直到那一刻,
一切光滑無痕,過去未曾存在,
在你將我放在那現代交通工具前,我與大地早已斷裂。
grig跳舞主要是身體與靈魂的連結上,它傾向於超越在日常使用中所經歷的身體限制。在競較模仿中,身體的邊界慢慢被推進。深植於人與自然、靈的連繫,維持著超越可能性的緊張感。是一種靈魂的,它使身體變成液態、固態且流動。它讓身體像口簧琴的舌頭一樣震動。(編按1)
跳,雙腳離地,短暫漂浮,再回歸原點,像一切未曾發生。
山羌的天空如此空洞,
指甲在月亮升起前已經脫落。
自信已經消散,彷彿只剩下光禿的邊緣。
他解開我的扣子,再扣上一個扣子。
全身的肌肉在抽搐,我唱起著如此單薄的旋律,
而他依然在吟唱,
不要拿起麥克風,我不願他像我一樣跌倒。
我伸出手,請他帶我走下峽谷,
即使他說自己已準備好迎接那傾盆落雨,
我仍捨不得這些qabang的溫暖。(編按2)
他將自己包裹起來,讓我為他解開,
可正如我所說,我們不該吟唱那些不屬於我們的聲音。
我用土壤般的舌頭說話,
在那洶湧的水流聲中,從口腔到根部的震撼,
我無法在其中歌唱,
而他像個怪物般在下一個峽谷裡低吟。
我依戀這搖搖欲墜的舒痛感,
無法脫離這首曲子的旋律,
詞彙尚未成熟,
我們等待著洪水,卻始終未曾到來。
我的腰上上掛著遮陰布,帶子緊繫天空,
膝蓋泛白,沒有一聲呻吟。
編按:
- grig為太魯閣族語「舞蹈」之意。
- qabang為太魯閣族語「被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