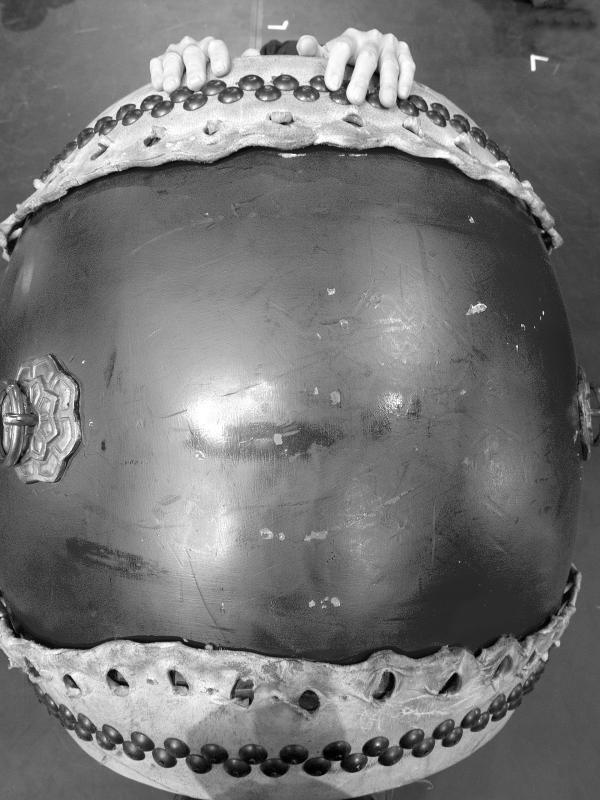盧健英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回望
《歌劇魅影》真是夠擾嚷。有一日,清晨的兩廳院廣場進來了數輛巨型卡車,工人們小心翼翼地卸下金色的水晶吊燈,以及巨大工程裡每一件不能稱小的小零 件,水晶燈杵在艷陽下,讓電視媒體的攝影鏡頭在廣場上像蜜蜂般鑽進鑽出。那一個星期裡,劇院地面層的廊道間彷彿進來了一位霸道的客人,行李多如牛毛,巨如 高山,一天天在國家劇院內拼裝雕琢出另一個劇院。然後,有一天,廊道裡不再擁擠,我們聽到了悠揚的魅影。 《歌劇魅影》的製作,是一 個整體輸出,以及高度精確的整合,其實,就算把環繞音響加進去,根本沒有什麼高科技,幕後是所有流程細節整合的成果。整個製作的流程,把人為因素降到最 低,才能確保每一日都是同一個水平的演出品質。但表演這一行,活脫脫是人為因素的組成,用情感搏情感,偏偏裡面還要有高度的技術控制,做到能符合最大多數 人口味的穠纖合度。《歌劇魅影》對台灣表演藝術最大的衝擊便是複製化,在故事、音樂、演員、造型、節奏以及快速順暢的舞台變化之外,他們複製在掌握之下的 緊張情緒、扣人心弦、哀歎與讚美。 台灣表演藝術複製化的能力夠不夠?問這個問題的同時,在我心裡響起另一個問號:藝術如果複製化之後,那個 搏感情的純度還夠不夠?台灣表演藝術的複製化能力與環境也許還不夠純熟,但搏感情的純度不容置疑。一月六日我們聽到了伍國柱過世的消息,那位用作品搏生命 的青年編舞家,終於無法來得及回到殷殷等待他的舞台。我們在二月號裡重新回顧了這一年的表演藝術舞台,選出我們印象深刻的作品片段,它們說再見了,它們或 許無法複製,但因為獨一無二的純度,讓我們再回頭看一次。
-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 Feature預知2006表演紀事—Top 10 & 10 Topic 十大表演紀事背後的現象與議題
前年《PAR表演藝術》雜誌曾做過一次「預知二○○四表演紀事」,預告全年的表演大事,當時編輯們做得辛苦,但讀者們反映熱烈,把一年的表演大事做了一遍掃瞄,在國內表演團體往往演出的不確定因素還很高的情況下,編輯檯的「預知」風險壓力很大。 二○○六年,編輯檯重提此事。但這一回,我們放聰明些。一方面也因為現在可以照表操課的節目比過去穩定的多,另一方面,每一年其實都有一些大事,背後有著若隱若現的代表意義與趨勢。於是PAR編輯檯蒐列了未來一年即將發生的表演藝術大事,涵蓋人物、場地、節目、事件共二十項,由音樂時代出版社總編輯楊忠衡、劇場及電影導演鴻鴻,資深劇場工作者耿一偉及PAR雜誌總編輯盧健英,為讀者選出二○○六最值得期待的十件人與事,而「Top 10」的背後有十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與議題(10 Topic)。 表演人物亮眼出線 超凡的舞藝及亮眼的舞台魅力,許芳宜一開始便在無異議的情況下被評為今年「最閃亮的明星舞者」,台灣大部份的觀眾對這位來自蘭陽平原的舞者或許都還不熟悉,除了三月與葛蘭姆舞團領銜演出,今年四月她還將在雲門舞集2主跳羅曼菲為其量身訂做的獨舞。在舞蹈這一行裡,「舞星」的出線十分不易,先天條件、後天努力之外,還要加上許多環境裡的拱月因素,使得她能以身體與作品交盪出極大的影響力,並成為家喻戶曉的舞蹈藝術家。做為一位在國際上被看見的亮麗舞者,我們期待她有更多讓台灣觀眾看到的機會。 在伍國柱因病猝逝後,目前擔任雲門舞集2駐團編舞家的布拉瑞揚更受矚目,被選為「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編舞家」。長年關注布拉瑞揚的劇場導演鴻鴻認為他的作品「格局恢弘,結構奇特,多焦點調度大膽,畫面變化豐富,節奏張馳激烈」,而最難得的,莫過於「情感表達的深沈」。今年四月,雲門年度公演的組合便是林懷民+布拉瑞揚的師生檔。布拉首次從雲門2「晉級」為雲門舞集編舞,「接班人」的態勢呼之欲出。 兩廳院世界之窗系列請來的歐陸當紅導演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無疑是今年「最具份量的國際導演」,十月將帶來易卜生的《海達‧蓋布樂》和東德劇作家克洛茲的《點歌時間》。曾多次到德國看歐斯特麥耶作品的鴻鴻說:「他的作品直接面對社會問題,政治氣息濃厚,肢體衝突強烈」,每有新作都會成為歐陸劇壇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你的莫札特經驗是什麼?
人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詮釋莫札特。 編輯廖俊逞提議說要做莫札特紀念專輯的時候,初時我皺了皺眉,這是最難做的題目,最容易被 看懂,最不容易被滿足,對老饕級的莫迷而言,認識莫札特,文字永遠比不上音樂本身;對入門的人而言,莫札特一生創作六百二十六首,我們算了算,一個常人就 算用每天抄八小時,也要花三十年才能把他所寫的譜抄完,我們要從哪一個角度來認識莫札特?難。 於是我們想:建立自己的莫札特經驗。二百五十 年以來,莫札特對人類的影響無遠弗屆:全世界暢銷排行榜的國際通童謠裡,「一閃一閃亮晶晶」應該是第一名如果沒有莫札特的話,它可能無法離開法國鄉間 的民謠身分;我知道有朋友在生產前,一再叮嚀醫生,如果可以的話,分娩時為她播《魔笛》裡的夜后之歌〈我心燃繞著怒火〉;當然,就更不用說,醫學上如何努 力證明,莫札特音樂不只使孩子不會變壞,更證明足以使孩子變聰明。 但是你認識莫札特嗎?我們反過來問,這位兩百五十年來像鄰居般存 在在世界各角落裡的長不大的音樂家,他真的靠天才過一生嗎?我們翻讀了許多關於莫札 特的書籍、書信之後,覺得他一生不快樂的時間應多過於快樂,他喝酒、說髒話,還愛對女生毛手毛腳;在金錢方面,如果活在現代,他肯定是各家銀行現金卡最搶 手的廣告代言人,然而天才與貧窮似乎是宿命裡的同卵雙胞胎,他給世人留下豐富的音樂遺產,自己卻窮得連棺材本都沒有。 關於莫札特的書多如牛 毛,除了《安魂曲》之外,這位作曲家裡的阿波羅永遠給人向上的、華麗的、優美的、光明的想像與慰撫。這本紀念專號的策畫,一方面為讀者先預告了一整年關於 莫札特的全球活動,另一方面,就像我們對潘金蓮仍有無限的想像與同情,全世界的歌劇導演都在嘗試重新詮釋莫札特歌劇裡的女人,今年國家交響樂團選擇了以兩 齣歌劇《女人皆如此》與《費加洛的婚禮》,導演賴聲川把兩齣歌劇搬到民國三○年代繁華時髦的上海,在這一期裡由賴導演詳盡說明了整個導演的想法。
-
特別企畫 Feature
擊樂二十年,台灣的音樂奇蹟
十年前,打擊樂本來是最沒有人要學的樂器,可是,如今擊樂幾乎以「國民音樂」之姿,在音樂、戲劇與舞蹈的各種領域裡,都撩起觀眾的安靜、興奮與熱情。除了它的群體性、平民化、多樣性外,打擊樂最接近心跳的節奏熱情,讓觀眾感受由衷的快樂,正是造就台灣「擊樂」奇蹟的關鍵原因。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台灣音樂奇蹟
對很多人而言,朱宗慶是「可敬的對手」,去北投結束朱宗慶的訪問,離開時辦公室早已燈火通明,但電腦鍵盤的工作聲依然此起彼落。朱宗慶打擊樂團彷彿一座精力充沛的發電廠。 二 十年前,他把一個在管絃樂編制裡坐在最後面的樂器打成了主流;朱團的成功讓更多人有熱情與信心學打擊樂,現在音樂系裡打擊樂主修學生人數遠高於其他樂器; 他攻佔了原本以日系鋼琴教室及高大宜系統為主的才藝班市場,朱宗慶打擊樂教學體系成了新的品牌,而且今年更在澳洲設立第一個海外據點。 在累積數千場的演出紀錄裡,朱團的演奏曾讓上萬人的群眾廣場為之瘋狂,也讓臨終病童嘴角泛出微笑曲線;有超過八萬多的台灣民眾,人生的第一堂音樂課是從朱宗慶打擊樂開始;朱宗慶,以兩根棒子創造出台灣的音樂奇蹟。 我 記憶中的第一場朱團經驗,是創團首年夏天在三峽祖師廟前的演出,鑼鼓鐃鈸聚集了趿著拖鞋的父老們,來看這群不像一般賣藝團草莽奔騰,但卻有著另一種活潑親 切的年輕人表演,他們用來自中南美洲的馬林巴琴,演奏都快聽出油來的台灣民謠,竟令拘謹的歐吉桑們不禁跟著節奏點頭,搖擺起身體。這樣的演奏,一九九五 年,到了陝西西安的小村落裡,一樣引起民間父老內心裡的澎湃熱情,用幾千人的縣戶鼓樂隊來歡迎朱團。 說起來打擊樂應該是過去二十年裡,台灣 發展得最快的器樂。不管是主修人口、欣賞人口,以至於創作作品的數量,在國際上的活躍程度,都是驚人的成績,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將開始的台北國際打擊樂節, 以「新潮流」為主題,繼續朱宗慶打擊樂團引領擊樂國際發展的企圖。這一期我們除了有詳盡的節目介紹外,本期的主題企畫編輯鄭淑瑩同時也將打擊樂在台灣的重 要紀事與發展做了一個詳實的年表,在這個年表中,我們發現擊樂「平民化」的崛起過程,是讓台灣中產階級家庭「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所負擔得起的選擇;此 外,朱團演出所提供的「熱情」、「快樂」的價值,也很容易讓憂鬱指數越來越高的台灣社會引起共鳴,也是擊樂普及化很重要的社會動能。 鋼琴家波哥雷里奇上個月來台演出,和十年前第一次來台,他的人生與性情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鋼琴家波哥雷里奇與陳毓襄、焦元溥的台北七天音樂課〉一文,透過波哥雷里奇的台灣好友焦元溥與弟子陳毓襄的親身經歷,以採訪的方式獨家披露來台七天幕後點滴。 <stro
-
特別企畫 Feature
兩根棒子,玩真的
很少音樂家像朱宗慶,在訪談中一直把自稱是「鄉下孩子」掛在嘴上。 朱宗慶是來自台中的鄉下孩子, 是從台語歌星文夏的歌,及學校的升降旗典禮開始他的人生音樂課, 參加學校的管樂隊時,他所能見到「職業音樂家」是廟會裡和喪葬上的康樂隊。 鄉下孩子朱宗慶進了國立藝專,才發現自己努力吹小號的嘴形是錯的, 那改學薩克斯風好了,結果麻煩更大, 因為學院派裡沒有人主修這種只在歌廳出現的樂器, 音樂系裡流行一句話:「不會吹,不會拉的就到後面去打鼓吧。」 沒想到,這個沒有人要坐的打擊樂位置, 趕上台灣七○年代大量現代作曲家創作的年代, 打擊樂喧賓奪主地成了朱宗慶的最愛, 同時也讓他站上台灣打擊樂界教父的地位。 兩根棒子,玩真的, 一九八六年,朱宗慶打擊樂團成立, 這位來自鄉下的音樂家把現代打擊樂再帶回民間廟口、廣場,也帶至了國際上; 而打擊樂這個二十年前最冷門的器樂, 在台灣,現在成為僅次於鋼琴的最熱門選擇。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柔性政變
十月看完當代傳奇劇場的《等待果陀》,吳興國的表現遠比《暴風雨》裡好的太多。但青年演員盛鑑及演「垃圾」的丑角林朝緒和演暴發戶的馬寶山則令人刮 目相看。盛鑑剛「黯然」離開台灣最活躍的國光劇團一個從小坐科、在鼻青臉腫中長大的京劇演員離開京劇團,不是黯然是什麼?十五年前的吳興國不也是噙著 淚水離開。在傳統師輩眼裡,他們是叛徒。 離開之後,卻見戲曲演員海闊天空的新舞台。中國京劇名伶梅蘭芳說:「演員需要靈活運用程 式,不能被程式所困。」戲曲程式不是限制,但那個鼻青臉腫造就的紮實根基,只要靈活運用,卻讓傳統可開可闔,穿古通今,東西遊走。傳統的創新哪裡需要大破 大立,原來從梅蘭芳開始,傳統戲曲的柔性政變就不斷在每個時代裡發生推翻與被推翻。 因為即將登場的雲門舞集《狂草》、及王心心的「王心心作 場」,這一期我們製作了「傳統的現代啟示錄」,台灣這幾年在傳統的創新上走出了許多成功的案例,不管是傳統戲曲的現代化,或者結合傳統元素的現代創新,從 明華園到當代傳奇劇場,從雲門舞集到國光劇團,從漢唐樂府到霹靂布袋戲,塑造了台灣當代藝術既傳統又時尚的經典面貌。 我們用「柔性政變」來 形容這樣的轉變與創新,因為並沒有破四舊,只是不斷融入新的時代情感、時代節奏,傳統的在朝與在野可能都有喧囂或喝采,但我們看到每一個時代裡出現它的最 新,也有它被尊崇的古老。傳統不能逆時代而存,而時代面對傳統亦應謙卑。老祖宗的東西如果要「靈活運用」,就正如《等待果陀》節目單裡,年輕的盛鑑在這一 齣作品裡的體會:「唯有紮實的傳統基礎才是創新的後盾。」 西方的傳統藝術裡,最被我們熟悉的該是芭蕾吧,有趣的是,在柏林,古典芭蕾霸佔數 百年的歌劇院,今年也在歐陸頗具指標性的「八月舞蹈節」裡,出現後現代舞蹈企圖「攻城略地」的一場「柔性政變」。事實上,九月下旬法國當代舞團瑪姬.瑪漢 來台演出的《環鏡》也在柏林觀眾裡引起各式各樣擁抱與反對的意見:走路算不算舞蹈? 一再重覆算不算?《環鏡》究竟是不是一支舞蹈?新世紀以來的現代舞發展是不是遇到了瓶頸?在這些似舞非舞的作品裡究竟還有沒有新鮮事兒?我們在歐洲的作者 林冠吾,給這次藝術節的幾支重要作品如何顛覆傳統,作了詳細的描述與觀察。
-
特別企畫 Feature 面向新觀眾 傳統變時尚
發動老祖宗的柔性政變
傳統不能不老,但傳統可以不死,把傳統文化當成一座取之不竭的活博物館,傳統便能歷久而彌新。當傳統舞台風光不再,傳統藝術仿如發動柔性政變,一走傳統戲曲的現代化,一是結合傳統元素的現代創新,兵分兩路,從明華園到當代傳奇劇場,從雲門舞集到國光劇團,從漢唐樂府到霹靂布袋戲,塑造了台灣當代藝術既傳統又時尚的經典面貌。
-
特別企畫 Feature 台北製作,大陸發光
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可以開出奇花異草
盧健英(以下簡稱盧)當初《牡丹亭》的首演為什麼選擇從台北開始?而一年後又再度回到台北,這在華人文化圈的推動裡,是事先設定好的策略嗎? 白先勇(以下簡稱白)設定好的,早就計劃好巡演一輪後再回到台北。有幾個理由:第一,我常說「大陸有一流的演員,台灣有一流的觀眾」,台灣觀眾看過那麼多崑曲,多少年下來培養出這麼高的程度,如果這批觀眾點頭了,那這部戲大概就通過考驗了。 第二,我一定要在台北的國家戲劇院演出。這麼多地方巡演下來,還是我們國家戲劇院裡裡外外的味道對。兩廳院剛剛興建的時候,紅柱綠瓦,我覺得好老式,像是從圓山飯店搬過來的味道,現在想想,這樣的建築還真有一番道理,不但有宮殿式的派頭,又保留了中國的傳統。像上海大劇院就很洋派,完全是西式建築;台北國家劇院的建築讓人有一種精神上的歸依,而且它的精神和青春版《牡丹亭》很像,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再發展出來的新文化。 第三,這次的演出可能是兩岸文化合作,工程最浩大的一次。台灣戲劇、文化界菁英盡出,如王童、董陽孜、奚淞、樊曼儂、吳素君、林克華等,這批文化菁英的投入是這次演出成功的重要因素。 台灣文化界二、三十年來,吸收了東、西兩方的美學,在觀念上很自由開放,所以夠融合傳統與現代,經驗豐富。台灣的這批人在傳統美學的掌握、及劇場整體整合上具有很大的長處,加上精選大陸優秀的演員,所以這次的演出是兩岸各取所長,在文化契合上相當成功。 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中國文化在台灣再造」。大陸過去幾十年經過文革及種種政治運動下來,傳統文化的根其實是受到傷害並且停滯了。而在台灣反而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加上台灣本身的島國特性,吸收了各種外來文化,因此極具創意及創造力,如果把中國文化的根,在台灣培養起來,可能會生出一朵「奇花異草」,《牡丹亭》在台灣演出也是這個意義。 盧《牡丹亭》在上海、北京、台北三地的演出成功,對你而言,代表了什麼不同的指標意義? 白在台北演出成功,那是很要緊的,因為台北的崑曲觀眾裡有行家,台北演出不成功,別的地方都免談。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伏特加,呼乾啦!
「蘇聯」本來占了全地球面積的百分之十,曾是地球上最大,或更正確地說,最強大的國家。但一九九一年解體之後,一個國家裂成十五個,就像一個人突然改了名字,瘦了身,昨是今非,大江東去,連怎麼稱呼都令人結結巴巴,小心翼翼,因為我們不認識它──或說「它們」。 儘管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不再那麼遙遠,但卻依然陌生。這次專題在製作的一開始,編輯檯上決定:要有一張大地圖。兩廳院「世界之窗」系列行之有年,我們想真正打開地圖上的窗,了解這個從十三世紀就存在的國家,一千年前它如何擺脫蒙古,以宗教力量創建帝國;一百年前它如何在貧富不均引起激化的十月革命裡,開創人類歷史的新格局;十多年前,它又如何在社會主義終於不敵資本主義的情形下,一夕間紛紛解體。而十月隨著「世界之窗─冰磚四國」來台北演出的節目系列,將更讓大家體驗這些交融著宗教、文化、藝術之美的演出,如何詮釋這個苦難與華麗俱存的國度 。 這個專題製作得既辛苦又充實,從暑假開始,編輯辦公室裡蒐羅了十多本從書店、圖書館、私人收藏挖來的俄羅斯相關書籍,從地理、歷史、政治,到文學、美術、電影,他們抱著書猛K,K完之後互相獻寶,包括實習記者在內,過了一個話題很俄羅斯的暑假。暑假過後,他們用非常七年級的方法:整理出一○一條俄羅斯關鍵名詞,在這裡面,我最喜歡「伏特加」那一條:如果沒有伏特加,俄羅斯的歷史將大為不同。 這次特別企畫的主要負責人是編輯廖俊逞,截稿之後,我問他,做完了這一期後對俄羅斯有什麼感想?剛過二十七歲生日的他說:「這個國家好像只有過去,沒有現在。他們的過去如此豐碩厚重,但現在藝術上的表現還是『過去』。」酷嗜電影的編輯田國平說,解體之後的電影都很悶,不像德國電影在兩德合併之後還有著生猛活力,最新一部在台灣可以看到的片子,甚至還很好萊塢味。 生存壓力永遠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最大的課題,我的腦海裡還是電影《齊瓦哥醫生》裡蒼白與腥紅的對比,毀滅與理想的對陣,俄羅斯的表演藝術進行式是什麼樣子,或許兩廳院的世界之窗可以一探究竟。終於截稿了,就算是伏特加,誰說不能呼乾啦! Ps.感謝馬曉瑛、顏華容、伊格爾、邱光、熊宗慧在製作期間提供知識及經驗寶庫的協助。
-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不要自抬身價,也不要妄自菲薄!
成立已十九年的國家交響樂團,自八月一日起正式成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一員,也擁有了法定的地位。面對樂團的新紀元,本刊總編輯盧健英與資深樂評人楊忠衡,在新樂季的一開始,深入專訪這位國家交響樂團成立以來最年輕的音樂總監簡文彬,談樂團的未來與規畫。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九月的存在主義
這年頭誰還記得存在主義?上個世紀的藝文青年最崇拜的時尚名詞。 其實當初也沒有弄懂過,只是整個時代都在談著:「人為什麼活著?」、「人為什麼荒謬地活著?」,而那個時代正在遠去,哇哩咧,管他為什麼活著,現在的網路、MSN、部落格,讓你一次可以用十種身分去打發你的無聊,解決你的苦悶。 但瑪姬‧瑪漢這個月把存在主義風再帶來台北。在家先看了新作品《環鏡》的DVD,動作無聊到不行:吃東西、撿東西、調情、換衣、上班、洗頭、抱娃娃,舞者各走各的,在一片片的鏡面裝置裡虛虛實實、進進出出,配上一路隆隆作響的電子音樂,舞台上看似一再重覆以致催眠的效果,同時也正在堆累出對於「存在」意義反覆辯論的問句。越看心裡越沈,它在談生活裡的虛擲、毫無結構、莫名其妙,在鏡子裡,華麗的,低頭的、求生存的、機械般重覆的,都是充滿荒謬本質的「我」。瑪姬‧瑪漢的作品往往是一幅幅如雕塑般的眾生相,這些眾生,沒有出路。 在劇場裡,相隨的往往是瘋狂的本質,存在主義常在瘋狂與正常中辯論,但在戲劇的發展過程中,每個劇作家都曾著迷於「瘋子」。配合兩廳院實驗劇場九月份的「瘋狂菁英藝術劫」系列節目,我們深入探討了劇場裡「瘋狂」基因,正如執筆的戲劇學者林于竝所說:「因為『瘋子』除了擁有一般人所無法享有的「特權狀態」,同時舞台上的瘋狂也有可能是一種美麗。」 瑪姬‧瑪漢的精神導師是荒謬劇場大師貝克特(一九六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貝克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等待果陀》,十月份將由當代傳奇劇場的吳興國導演,第一次以中國傳統戲曲樣貌出現。貝克特傳記作者克洛寧(Anthony Cronin)這麼形容貝克特:「他有本事把最糟糕的事情變成好笑的事。」,《等待果陀》劇中兩位主人翁一直在等果陀,在等待過程中一直是又無聊、又煩悶,第一句台詞從「什麽事都做不成!」開始,整齣劇看似是喜劇,但最後卻是一場等不到果陀又走不掉的荒謬劇,最後的台詞是:「我們走吧!」但是他們不動。 將京劇帶往現代化的路上,吳興國從來不是「等待」果陀的那個人,我知道吳興國想做這齣戲已經很久了,拿著《等待果陀》這個劇本去和戲劇界的許多人討論過,擅長喜劇的李國修也是其中的一位,這個月的「異次元曼波」專欄,邀請了吳興國與李國修從喜劇開始展開「兩『國』論」。」</
-
藝次元曼波 HEART to HEART
喜劇.兩「國」論
當代傳奇劇場的小客廳,一雙吳興國練功的厚底靴站在樓梯間下。 青少年時的吳興國,穿過一雙雙李國修父親手工縫製、並謹慎地在鞋底內親手蓋上店章的戲靴;青少年時的李國修一次次隨父親走進荷花池畔的國立藝術館,看吳興國的師兄、姐們演《打漁殺家》、《釣金龜》,有時睡著了,有時把戲學著回家逗鄰居玩。 這雙靴子好像聯繫了兩個人命運中似有若無的緣分。 說也奇怪,這兩「國」,在台灣這許多年,就沒這樣開天闢地地談過。這一天,搬到金門街的當代傳奇劇場,吳興國泡好老人茶等這個二十年來第一次的兩「國」論。 吳興國與李國修,七○年代的一開始,一個從嚴格坐科的京劇團裡被拉去跳現代舞;一個打小在京劇裡吸收語言趣味,而在蘭陵劇坊的《荷珠新配》成為一炮而紅的喜劇演員;吳興國以當代傳劇場打開台灣京劇與西方經典接軌的里程碑,屏風表演班則以充滿城市寫實風格的作品首創台北商業劇場品牌,但在台北,兩人從沒有這樣談過喜劇、戲劇、京劇。 兩人都在彼此的劇場裡當過觀眾,擅喜劇的李國修在《慾望城國》的觀眾席裡,「戲沒開演就掉淚」,擅演英雄將相的吳興國則在屏風的《半里長城》裡捧腹大笑。過去三個月裡,戒煙戒酒的李國修一下子胖了十二公斤,於是兩個人一見面從養生、防老開始談起,「如果三十歲我們兩人就見面,當時就會談:『嘿!那邊那個女生長得真漂亮!』」 十月份,兩人的新戲將同一天開演,當代傳奇劇場挑戰《等待果陀》,屏風表演班則演繹兩代間的變調婚姻《昨夜星辰》。戲劇的道路上,一個人都演西方經典,一個人堅持原創,但卻在相反的路上,都與傳統相遇。 從京劇到戲劇的成長之路 李國修(以下簡稱李)你有沒有穿過我爸做的鞋子? 吳興國(以下簡稱吳)有!我經常去你家訂鞋子,不過從來沒有看過你。在復興劇校時我是練武生的,光是一齣《戰馬超》,練三個月靴子就磨得差不多了。但穿了那麼多靴子,後來證實你父親做的鞋子比大陸的師傅都好。後來畢了業,和周正榮老師磕頭學老生,只穿厚底靴,不穿薄底,成立當代傳奇之後,就更把厚底靴的功放進去。一九九八年《慾望城國》要去法國亞維儂之前,又跑去跟你哥訂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看,跳舞的人
那一夜,我在兩廳院廣場,滑輪板高高飛過藍色琉璃瓦。一場極限競賽的盛會吸引了數萬人在酷夏的夜晚裡,隨樂音搖擺吶喊。廣場一角,忽然響起和舞台反方向的集體掌聲與喝采,兩廳院階梯旁,眾人圍著一位獨自跳舞的人,那是一位穿著夏威夷衫的老先生,一位六○年代的嬉皮,正跳著九○年代的嘻哈舞步。 我很喜歡那個晚上沸騰的搖滾樂聲裡,那個不斷旋轉的銀白頭髮,他不斷變換舞步,彷彿身體裡有一雙翅膀。這個一個人的舞會裡,最後只吸引來兩個伙伴,一個咯咯直笑的四歲小女孩和一名敞開手臂的流浪漢。 其他人都不跳舞了,都只是看跳舞的人。 我回到辦公室裡,案上正在處理訪問《幸運兒》導演黎煥雄的稿子, 訪問中黎煥雄說:「你的自由,由你的恐懼來決定,那對翅膀就是內在恐懼的具現。」如果是這樣,剛剛那個廣場上,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翅膀,他們選擇了不害怕,沒有從群眾裡出走,沒有離開身體去冒險。於是,都只是看跳舞的人。 這個晚上,我又再翻了一次幾米的《幸運兒》繪本,書裡的最後一頁圖,是柏油路與斑馬線黑白分明的畫面,那個充滿暗示性的白色方向箭頭攫住我的視線。是的,幸運兒講的不是幸運,而是方向,你決定往那裡走,就決定了路上不一樣的風景。 我們在這一期的《幸運兒》的專題企畫裡,試著走出一貫製作的模式,《幸運兒》的故事,在現實裡可以有怎樣的延伸: 告別十年空少生涯,毛遂自薦進入電影圈的趙文瑄; 拋開法學世家傳承,勇敢追求指揮家夢想的焦元溥; 放下西北大學碩士,打造國片賣座新紀錄的李耀華。 他們不當人人稱羨的「幸運兒」, 在人生道路上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勇敢尋找自己身上的新翅膀, 也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新天空
-
特別企畫 Feature
音樂劇《幸運兒》
我們從來沒有問過你是不是真的想飛 我們從來沒有問過你是不是幸運得很累 就像《地下鐵》裡,黎煥雄放進了不相干的「愛麗絲夢遊仙境」童話及黑色的「卡夫卡」,舞台版的《幸運兒》也遠非幾米所預期。 如果說,原著裡幾米談的是飛翔,那麼這個故事到了黎煥雄手上,則是在談飛翔的失敗。「如果翅膀其實是一種恐懼呢?有人說是恐懼奪走了自由,那麼,如果恐懼以一種自由的象徵出現,那麼,事實會是什麼?那就會是象徵佔據了實體的另一個故事了,當人類飛起來,世界,卻開始往下沉。」自由與恐懼於是成為舞台版最重要的探討主題。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這個暑假,讓我們很「經典」
想一想,你有多久沒有看經典文學了?暑假的一開始,我們想回頭看看被遺忘的經典。 兩件事請讓我們想做這件事:去年一家知名廣告集團發表一份「當迷世代─台灣酷文化研究報告」,舉出台灣大學生最普遍的六大「當迷(Dumbing)」現象,「殺時間」是其中最大的訴求,因之發展出零食、簡訊、網路交友、外帶、八卦媒體等集體行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去查查誠品書店銷售排行:銷售第一名的書種是「減肥」書,第二名暢銷書種是「美食」書。 第二件事則是我們自己對表演藝術的反省。上一期的「藝次元曼波」單元,旅美導演李安與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的對談裡,李安談起台灣的表演藝術創意及精采度均足,但「少了具有思想深度的大劇作家」。經典是可以一再重複閱讀,一直到今天,李安還帶著孩子進劇場去看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 於是我們想在暑假裡,用經典來「殺時間」。有趣的是,這一期的「藝次元曼波」,吳念真在與李立群的對談中,便回憶有一年初中的暑假作業,作文題目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讀後感」,六百多頁的大部頭書,「書中的人名又有簡稱、又有暱稱,看到第五頁就忘掉前面的人叫什麼。」吳念真寫讀書報告的時候,很認真地寫:「很難,我看不懂」結果班上其他人因為抄書,全部不及格,只有他得了九十分。老師說:「我是要告訴你們,你們此刻看不懂的書為什麼是世界名著?要記住一點─因為老了可以再看。」 老了還可以再看。但是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裡,經典帶來不同的滋味,這一期的特別企畫「異世代看經典」,國小六年級的張杰今年給自己的暑假作業是看完《三國演義》文言文版,從小學一年級起,已經看遍了《水滸傳》、《包公案》、《封神榜》、《聊齋》等故事,其中他最喜歡的就是「劇情高潮刺激,人物變化多端」的《三國演義》。而新舞臺館長辜懷群,則透過京劇看三國,透過三國理解中國人的世情。誰說三國人物,灰飛煙滅? 今年是德國劇作家、詩人席勒逝世兩百週年,德國議會把二○○五年定為「席勒年」,在德國各地展開為期一年的馬拉松式的紀念活動。愛樂電台知名音樂主持人,同時也是小提琴家的彭廣林說,談席勒,就不能不談到貝多芬,貝多芬傳頌後世的第九號交響曲中的《快樂頌》,歌詞正來自席勒所寫的詩。而對從小學小提琴的建中應屆畢業生鄭淳仁來說,
-
特別企畫 Feature 老戲迷如是說
辜懷群:真正認識三國人物,從戲台上開始
愛文學更愛戲曲的辜公亮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辜懷群,從小在豐厚的人文與表演藝術環境長大,「三國」故事對她而言,除了是閱讀的經典,更是戲台上活生生的人物,所以她閱讀三國或看三國戲時都很忙,忙著檢驗:舞台上的人和書中寫的人物像不像?書裡的人物和自己以為的人物之間有沒有差距?
-
藝次元曼波 HEART to HEART
歐吉桑,安啦!
從歐式風格的咖啡雅座裡拔起來,兩個歐吉桑一溜煙地跑出去,就蹲在落地玻璃窗外,窄窄的景觀廊裡,兩個人聯手掩著風,點著了煙。 在國片最低潮的時候 ,兩人就認識了。一是台灣最真情的電影廣告導演,一個是台灣說話速度最快的演員,兩個人都從村子裡出身,一個是九份山上的礦村,一個是台北都會裡的眷村。 礦村與眷村,都是台灣社會發展史上漸漸消失的兩種聚落,但霧裡山城的貧困歲月,竹籬笆裡的南腔北調,讓這兩個人在上一代的困頓裡立志要讓村子更好,在下一代的幸福裡自勉盡己力讓安身立命繼續延續。 兩個人都是說故事的好手,當然,來自不同村子的兩個人,帶來了不同的故事。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歡慶150
五月中旬,我們開始整理一百五十期雜誌。 始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百五十期《表演藝術》雜誌(嚴格說來是一五一本,還有一本創刊號),在十二年又六個月的時間裡,累積了一百五十本由美術編輯呈現出來的封面主題,一萬六千五百頁,九百七十多萬字,七千多張台灣表演藝術發展過程裡,曾經銘記的畫面與劇照。 作為一個接棒人,我好像不能只用看表演的心情來看這一百五十本。創刊號的《表演藝術》以「摸索與希望」探討當年的台北表演藝術生態:美籍指揮家,後半生視台灣為故鄉的亨利‧梅哲在受訪中說:「什麼是台北的表演環境?在這兒,我拿出最好的節目時不賣座,不夠好的卻可能滿座。」梅哲談的是音樂推廣與音樂落實教育的重要性。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當年說:「台灣是個獨特的地方,千瘡百孔,卻又潛力十足。我們希望這塊土地變成什麼模樣?如何整理過去的足跡,看清目前的處境,聚集眾力來發展經營?」他在說,把劇場當成生活一部分的人,在我們社會仍屬少數。 一九九二年,台灣GNP(國民生產毛額)達到二一○八億美元,平均每人所得首次超過一萬美元,超過大陸十五倍以上。在兩廳院硬體建設的烘托下,來來去去許多國際名牌音樂家與表演團體。這一年,也是台灣表演藝術在九○年的高峰期,兩岸的交流文化密切進行著,我們在大陸劇團裡進一步體驗崑、京之美。根據陸委會的統計,一九九二年大陸來台的戲曲交流人士在這一年激增至二千多人,這個攀升的走勢直到一九九五年之後便走入下坡。 經過十二年六個月,台灣表演藝術裡有多少是還在上坡,有多少已經下坡很久了?歡慶150,其實正希望「整理過去的足跡,看清目前的處境」,在文建會剛剛三天之內花掉六千多萬元,歡慶舉辦完台灣第一次的「表演藝術博覽會」之際,我似乎沒有更多可說的。謹用梅哲老前輩的自我期許來期許台灣的下一個十二年:「在音樂面前,我只能說『好』與『壞』。我所在乎的,是我指揮的樂團是否已達到能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的水準,而不是所謂『台灣的標準』。根本沒有台灣的標準。」
-
特別企畫 Feature
從紐約到回家之路
這天一大早,一身棉衣的,打鼓的劉若瑀就來到雜誌社辦公室裡 「啊!好久沒見到李安了。」 李安當年認識的是演戲的劉靜敏。八○年代初,劉靜敏還在演藝界,是蘭陵劇坊一炮而紅的「荷珠」,主持兒童節目、演文藝電影片,為了讓蘭陵劇坊更好,她塞了三雙高跟鞋在行李裡,紅塵滾滾飛去紐約,認認真真地想做個偉大的女演員。李安改變了她的戲路。 李安算是劉靜敏在紐約大學的學長,李安學電影,劉靜敏學表演,在李安「不計成本」的畢業製作裡,當時台灣金鐘獎得主的劉靜敏免費當他的女主角。這位學長介紹劉靜敏去上感官記憶的劇場訓練課程,學習新的表演方法;英文還很破的劉靜敏,不到一年便一舉考上向來注重英文咬字行腔的紐大表演系。 在表演系,劉靜敏接觸了果托夫斯基的貧窮劇場;從貧窮劇場,她的表演路回到了劇場與原始人文關係的思考。 劉靜敏丟掉了高跟鞋,真真實實地踏在土地、自然裡去尋找身體內在的動能。一九八七年,她在木柵老泉山上成立了優劇場,她和團員們跑山、練氣、打太極,後來走全省、走印度、走到西藏;她的劇場之路從西藏回來之後,走的路越來越遠,卻離自己的文化越來越近。一九八八年,劉靜敏創立優劇場,從此展開一條漫長的東方身體文化的修練與實踐之路。 她褪去了劉靜敏,變成了打鼓的劉若瑀。和李安在越洋電話裡的長談,讓打鼓的劉若瑀想起在紐約的「劉靜敏」,劉若瑀眼眶泛紅,自責怎麼忘記了如此重要的生活過程,關鍵地影響了後來的生命發展;「紐約經驗幫我們開了一扇門,打開門之後深入進來,原來自己的東西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