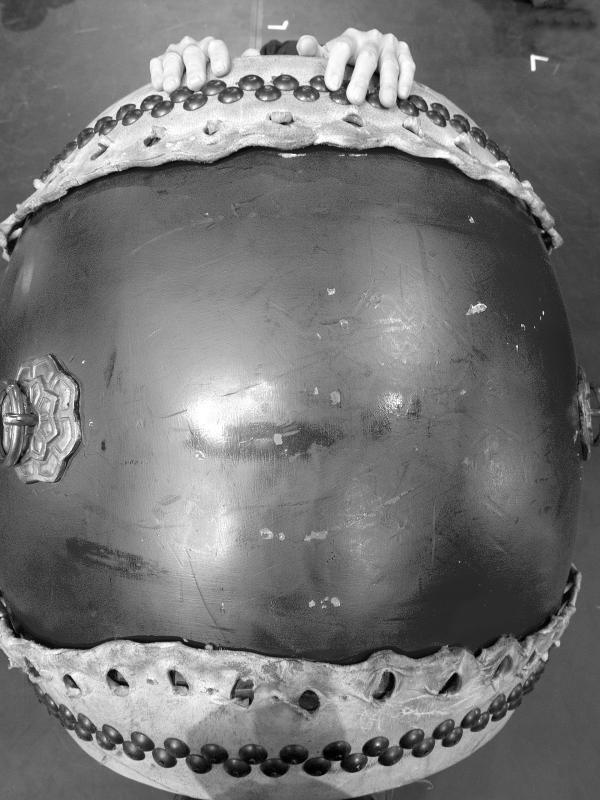很少音樂家像朱宗慶,在訪談中一直把自稱是「鄉下孩子」掛在嘴上。
朱宗慶是來自台中的鄉下孩子,
是從台語歌星文夏的歌,及學校的升降旗典禮開始他的人生音樂課,
參加學校的管樂隊時,他所能見到「職業音樂家」是廟會裡和喪葬上的康樂隊。
鄉下孩子朱宗慶進了國立藝專,才發現自己努力吹小號的嘴形是錯的,
那改學薩克斯風好了,結果麻煩更大,
因為學院派裡沒有人主修這種只在歌廳出現的樂器,
音樂系裡流行一句話:「不會吹,不會拉的就到後面去打鼓吧。」
沒想到,這個沒有人要坐的打擊樂位置,
趕上台灣七○年代大量現代作曲家創作的年代,
打擊樂喧賓奪主地成了朱宗慶的最愛,
同時也讓他站上台灣打擊樂界教父的地位。
兩根棒子,玩真的,
一九八六年,朱宗慶打擊樂團成立,
這位來自鄉下的音樂家把現代打擊樂再帶回民間廟口、廣場,也帶至了國際上;
而打擊樂這個二十年前最冷門的器樂,
在台灣,現在成為僅次於鋼琴的最熱門選擇。
盧—最近幾年擊樂音樂節請來的節目有各種跨領域的變化,例如與影像或劇場的結合。我好奇,如果有這些表演趨勢上的變化,團員的每日訓練是否也有不同?
朱—朱團對團員有一定基本功的要求,例如一定要會彈鋼琴,會彈木琴、會打小鼓、低音、傳統打擊樂,這些基本功不會因為趨勢的變化而改變,環境在改變的時候,我們還有新的嘗試與因應,但只要最專業的領域能把握,各種環境變化都可以。
我前天才帶北藝大學生去韓國交流演出回來,在那邊造成瘋狂。韓國第一位打擊樂教授朴光緒,也是我在維也納時的同學。我們都希望在教育體制裡改變學生對表演的看法,學打擊樂並不是一定要進交響樂團,我們的表演風格也影響了他們,培養出內在對音樂有所感受,上台應是一種享受,而不只是刻板的正襟危坐。
馬友友在報上說,小時候他一直不喜歡練琴,一直到有一天他長大到自己感受到音樂的力量,音樂開始與他產生不同的關係。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自己感受到藝術的美,那他只是一個「匠」。
盧—談談你當時是如何開始走上打擊樂這條路?擊樂演奏有沒有明顯的師承體系?
朱—有一次在立法院,有人問我,為什麼所有的評審都是你的學生?這沒有辦法,因為我是第一代,要等到打擊樂界不是我教出來的學生,大概就要等到第三代了。我覺得有沒有師承這是時代的問題。現在的擊樂學生問起師承就會很明顯了。
但我那一代不一樣。我本來是學管樂的,初中起就是學校管樂隊的隊長兼指揮,從參加學校升降旗典禮開始吹起的。因為哥哥後來也在學校裡擔任管理樂隊的行政人員,我有機會去玩各種樂器、小喇叭、薩克斯風、爵士鼓等,後來到了藝專,學校樂團裡需要鼓手,就指定我去,對於打擊樂的演奏,一開始只是根據指揮的指示去做,有時候甚至是模仿唱片,然後經驗累積,很多概念還不是很清楚。
後來兩位老師影響了我,一位是日本作曲家北野徹,當時省交請他來台灣一個月講座,我、連雅文、陳揚都跑去當他的學生。另一位是麥蘭德,是文化大學請來的美籍打擊樂家,我已在藝專音樂系四年級,在系主任史惟亮的介紹之下,我也到文化大學去上他的課,我、連雅文、陳揚、徐伯年都成為第一代的打擊樂家。這兩位老師應是啟蒙台灣打擊樂視野很重要的兩位人物。
盧—你認為在他們身上分別學到的是什麼?
朱—北野徹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正規」,而不是譜拿來就開始打。按步就班的學院式學習。有一個環境上的背景,事實上推著我走上這條打擊樂之路。七○年代,正是馬水龍、李泰祥、許博允、賴德和、溫隆信這些現代作曲家開始創作的黃金時期,他們有許多與聲音有關的實驗與嘗試,就常常找我去打,試試這個聲音,那個聲音;藝專四年級時,樊曼儂的環境音樂節也引進了很多運用打擊樂器的現代作曲家,我幾乎也和他們一起工作過,對年輕的我而言,反正也沒有什打對或打錯的負擔,也不怕錯。
回想起來,我一直感謝史惟亮老師,是他建議我這一條當時還沒有人要走的路,同時還介紹我好老師。另外,當時教我管樂的薛耀武老師不但沒有怪我「一心二用」,還借給我他收藏的打擊樂唱片,打開我在聽覺上的視野。
盧—當年打擊樂應是很冷門樂器,你不會想放棄?
朱—這回二十週年,美術設計家劉開設計的海報幫我表達了心聲。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他說了一句話:「二十年前敢拿打擊樂來做職業的,是跟天借膽。」現在想想確是如此。當時我還未滿二十歲,根本沒想到前途,只是一直覺得打擊樂好玩,而且當時社會一直給我很多很多機會,推著我去做,讓我沒有空閒下來去想我可以去做別的有出息的事情。當兵時是國防部示範樂隊的打擊樂手,退役後二十三歲,到省交擔任打擊樂首席,這已經是一般人認為學打擊樂的最高位置,我後來要出國的時候,有人說你不用出國,就算出國回來也只不會再比這個位置更好。
我出國之前只是喜歡打擊樂,沒想過未來是不是當什麼演奏家。所幸父母從未反對,他們心目中曾有過的期待可能是回來之後當個公務員就好了。而等我二十五歲取得打擊樂演奏文憑要回國時,素不相識的馬水龍老師寫了一封信給還在維也納的我,希望我為即將成立的藝術學院音樂系規劃五年學制的打擊樂專修課程,這也是台灣破天荒第一個打擊樂主修。這又讓我繼續投入打擊樂在台灣專業化發展的開始。
盧—到那個時候,為什麼馬水龍會覺得有需要在音樂教育裡出現打擊樂專修,是覺得現代音樂的作曲趨勢裡已有需求出現?
朱—作曲家都比演奏家思考得早,第一馬老師看出打擊樂應該和管樂分開發展,第二他認為台灣的打擊樂應該更大幅提昇。我在回國的最後一段時間,就開始瘋狂在維也納、德國、法國、英國及美國各國找打擊樂教學體系的資料和譜子。演奏、推廣、教學、研究是我一開始就設定的四大目標。但在參考了各國的教學體系之後,覺得最重要的是也要有自己的東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作曲家合作。朱團從創團至今委託作曲有九十多首,編曲則更超過三百多首,當時一般都認為「國人作品」是票房毒藥,我不相信,覺得這是建立自我特色最好的方式。
盧—第一屆招生時有多少人來考?
朱—第一年來考時只有三個,但我沒有錄取任何一位。沒有學生,也就沒有了這一年在藝術學院專任的教職。我不能為了找一份大學教授職業就錄取了不適合的學生。但第二年就有好人才出現了,現在每年招考大概有七十多個學生報考。
剛成立的時候,學生會要求說他只要學木琴,其他的不學,我說不行,你必須全部都學,當時學生反彈得厲害,但我很堅持,現在看起來這個決策是對的。因為你必須知道各種樂器可能的音響與各種聲部的關係。
盧—朱宗慶打擊樂團一九八六年成立,我記得有幾場戶外演出是十分轟動的。
朱—我回來時認為推廣打擊樂是一個重要的方向,怎麼推廣?就是讓好東西走向人群。並且打破一般人認為音樂是昂貴嚴肅的觀念。所以一回來沒多少就和福茂唱片公司簽約,做很多當時很多文化人覺得沒有辦法在影視綜藝頻道做的宣傳,上張小燕的綜藝節目,並且到廟口廣場做戶外演出。我自己從小在鄉下長大,很能體會人群聚集在一起感動,但到廟口演出,應該要有適合廟口觀賞的曲目,我們改編了很多民謠、節慶小調,結果,活潑熱鬧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人。後來第二年再受電視台之邀又到祖師廟再去錄製成節目。
盧—朱宗慶打擊樂團有很多在各地精采的演出,我在觀眾席常看到觀眾的投入與聽完後的開心,但對你來講,二十年來這麼多場演出,有沒有那些演出是有深刻意義的?
朱—這麼多年來有三場是特別讓我無法忘記的。一九九四年高雄市立美術館開幕時,《中時晚報》邀請我們到高雄演出,那一晚來了一萬多個觀眾,美術館廣場上坐得滿滿,演至一半,卻下起傾盆大雨,團員們還措手不急的時候,忽然間許多觀眾衝上台,我們一開始還有些緊張不知他們要做什麼,後來發現是要幫忙團員拿塑膠套蓋住樂器,心疼樂器淋溼了,台下沒有人要走,還好雨一下子停了,觀眾又幫我們掀開塑膠套,恢復演出,演出之後,美術館放起煙火,觀眾和團員們都興奮得難以言喻。
第二個演出,是為一位得腦瘤的重病兒童在榮總大廳的演出,他最大的心願是聽朱團演出《鱒魚》五重奏,因為這首曲子是這位病童和爸爸媽媽全家最喜愛的曲子,為此我們還特別改編了這種曲子的打擊樂版本;但到了現場,我看到孩子的父母就楞在那裡,這才發現他是一位在朱宗慶打擊音樂教室的學生,我本來以為他已經痊癒了,但沒想到卻又在榮總裡見他最後一次。孩子已經是在昏迷狀態裡,在父母陪伴下聽完我們的演出。
第三則是去年在俄羅斯的演出。之前,朱團在美國各地包括林肯中心的演出,那種「攻進」美國觀眾的興奮,是可以理解的。但俄羅斯不同,我們是第一批到莫斯科演出的當代表演團體,主辦單位也大力宣傳,觀眾來不是因為知道我們有多好,而是對台灣的表演團體有好奇,結果從第一首開始,每一首結束後觀眾就大呼大喊,以他們的環境,他們對打擊樂的觀念是比較保守的,我們安排的曲子包括改編傳統的《小河淌水》,讓他們感受中國式內歛婉轉的情慾,幾乎每一場都讓他們為之瘋狂。
盧—朱團的表演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特色,你們的表演總是讓觀眾感到開心,快樂的,你認為這是你們廣受歡迎的原因?
朱—與其說快樂,不如說是熱情。朱團不是為了製造快樂而讓大家感到快樂。很多東西雖然是有意識地追求,但快樂只是其中之一。團員必須把真正的熱情擺在台上,專注、完整才能讓觀眾感受到與音樂的一起投入。事實上我們的團員不只是台上很熱情,台下也很熱情,我希望我的團員及學生們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要廣泛。
剛剛說到在榮總演出的經驗,讓我發現音樂可以給人的慰藉,後來我們去了各地的醫院、養老院,也去過一次監獄演出,這些都是很少對外說的。有一回去了一個平均年齡八十七歲的養老院,演完之後,老人家動作慢,掌聲是慢慢響起,然後看到他們的眼淚,有一位老人握著我們的手說:「我們都要走了,你們為什麼還來!」至於監獄,我會非常願意為獄中受刑人訓練一批很棒的打擊樂團。對我而言,不管是做這些社會工作或開設音樂教室,我想要做的是讓人能感受音樂的力量,是教音樂而不是教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