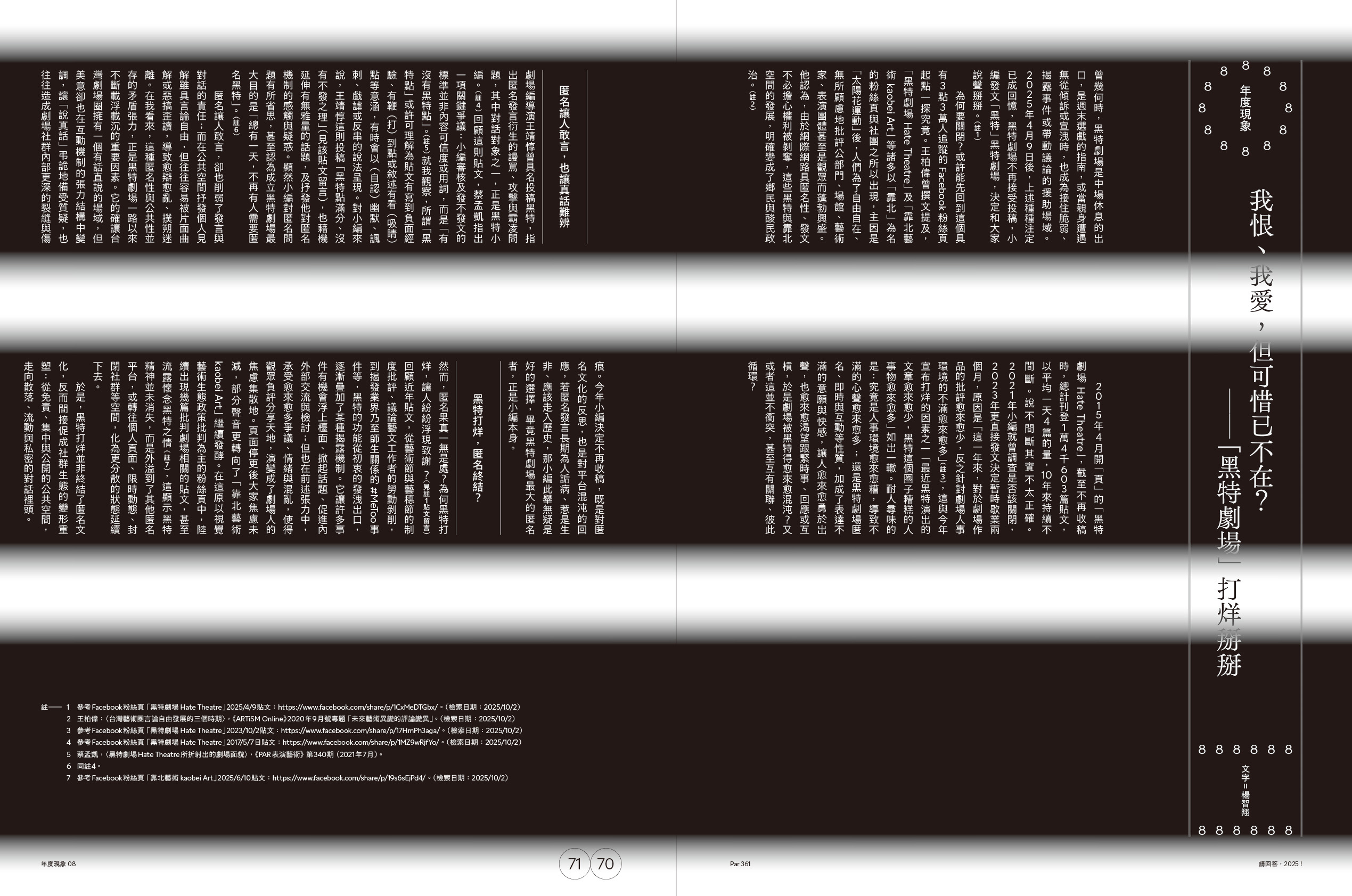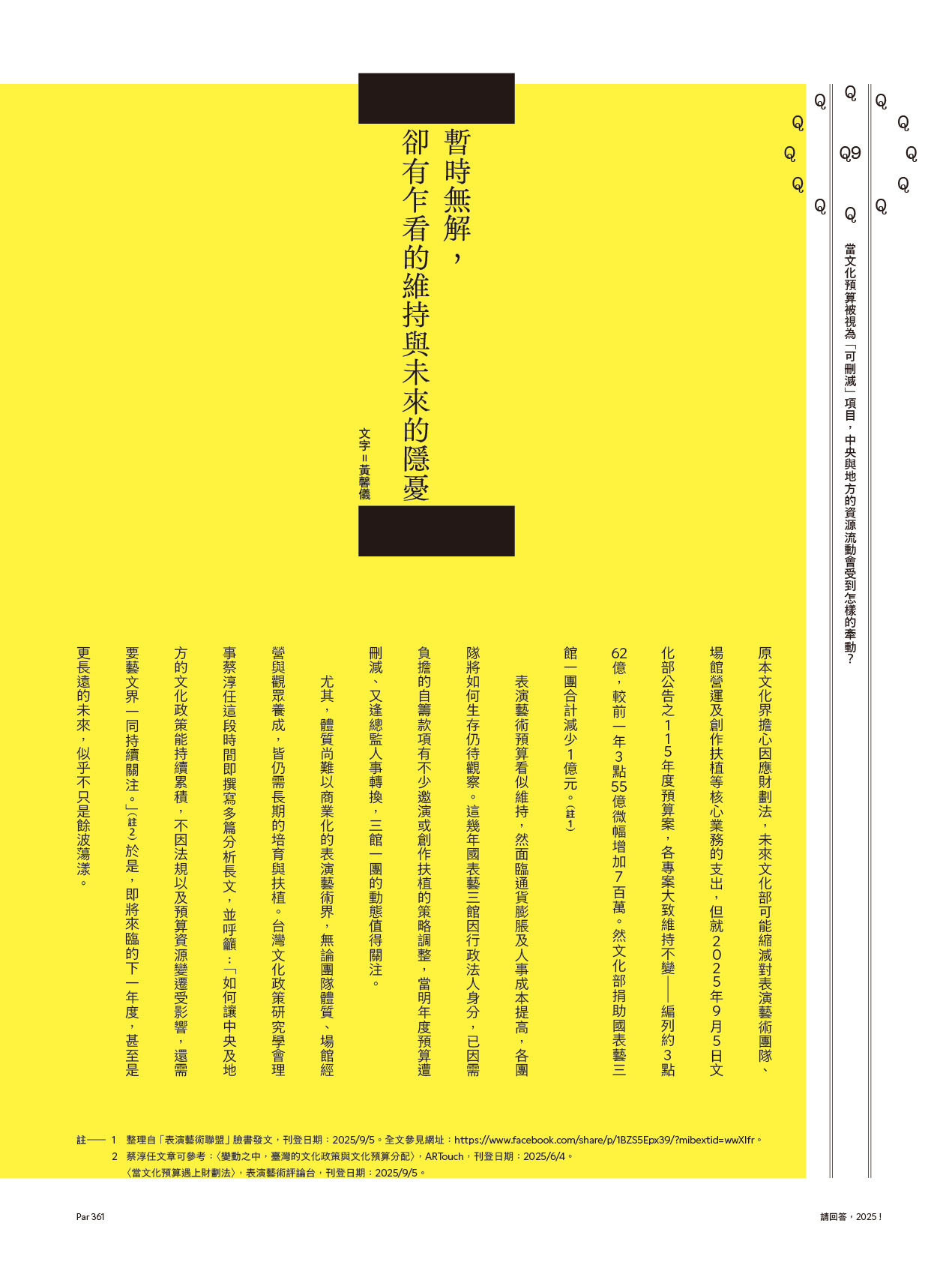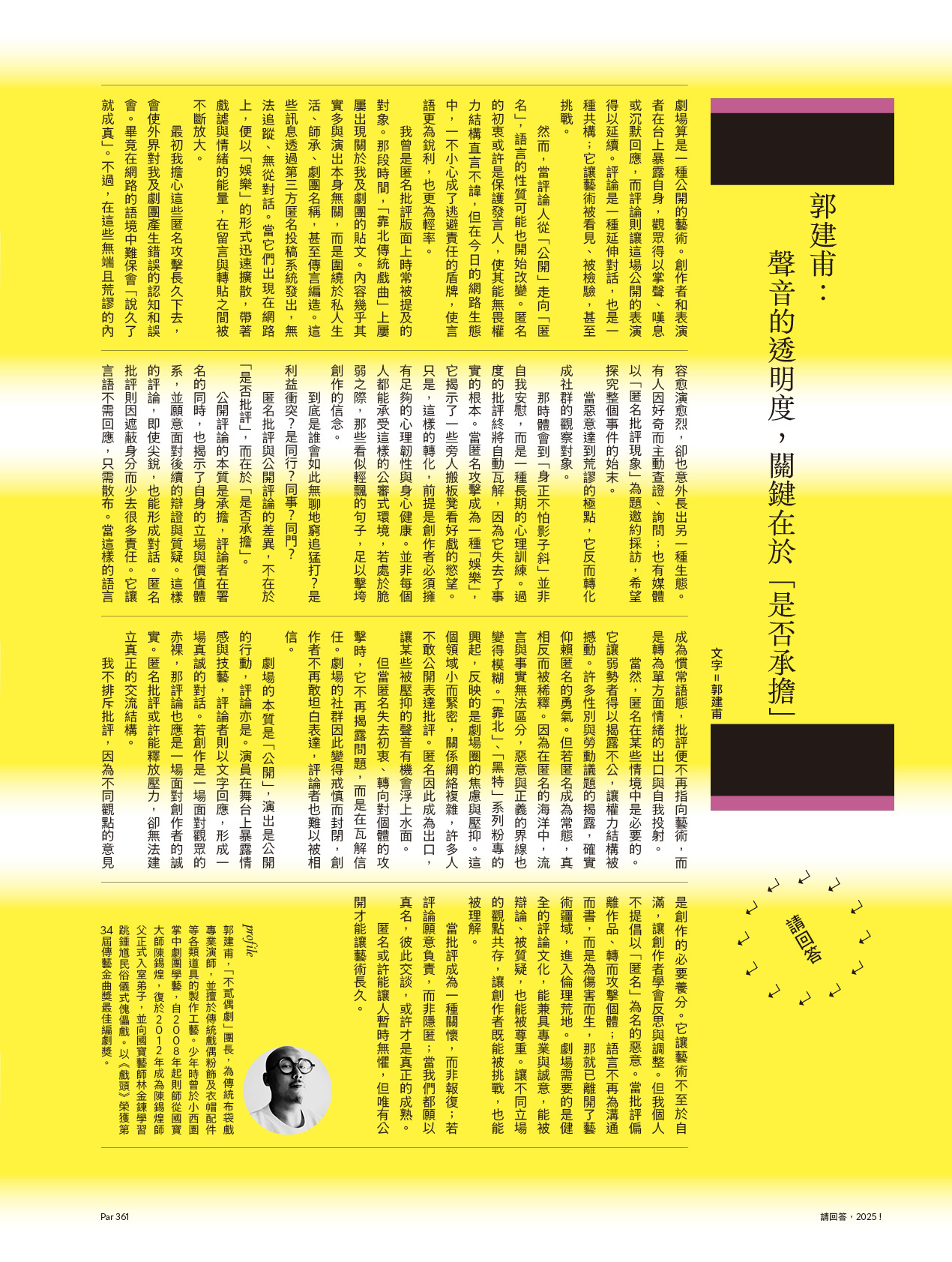郝妮爾
1989年生於台灣宜蘭,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文化藝術工作室負責人。長年從事藝術文學專訪、側記、評論之工作。創作體裁橫跨散文、小說、劇本與童話。2018-2020年台灣表演藝術專案評論人;勵馨基金會《拾蒂》三部曲編劇;著有散文集《我家,或隔壁》、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劉璧慈:生命轉過幾個彎,但沒有一次放下相機
大學一年級時,劉璧慈用存下的零用錢買了一台單眼相機,「是座桃紅色的、那個年代妹仔很愛買的相機唷,一台差不多3萬塊。」說到這裡,她爽朗大笑。當時到底在想什麼呢?是嚮往文青的生活、還是妹仔的青春?大概以上皆是。不過,那台相機當然也意味著她第一次正視自己對攝影的喜愛。 「我很喜歡透過鏡頭看著人細微的表情。」劉璧慈說,過去也曾經聽聞有些攝影師擅長將自己藏在鏡頭之後,不過聊及自己的看法,她倒不覺得自己在躲藏,「特別是拿起相機的時候,我就不害怕跟人靠近了。」 從劇照師到劇場攝影師 高中的時候,劉璧慈曾經模糊地期望自己能夠成為戰地攝影師,那或許是她第一次萌生能以攝影為職業的開端。 「不過當時的情懷多是浪漫的憧憬,我當然知道實際上並不如此。仔細想想,我真正嚮往的應該是極具震撼、故事性的照片吧?」 倒是沒想到,這個嚮往後來先在影視產業得到回應。 劉璧慈的攝影路徑聽來有趣,不從報社、也非自雜誌起家,幾乎可說是初入行就直面繁瑣的影視劇照工作。「其實是因為有親戚也在相關產業工作,這個圈子不大,介紹起來主要還是看人脈。我當時什麼都想嘗試,就直接答應去拍了。」 自電視劇起頭,乃至後來的電影、MV,無論長片短片她都拍過。這條路得強迫自己無師自通,很多眉角都是她後來發現的。「在拍攝現場,攝影師是看哪裡有往好位置,就往那個洞去鑽,可是第一目標還是不可以干擾鏡頭,等於是你要四處卡位,適時詢問:有哪些場合有沒有機會為了拍攝再Run一次?只不過影視圈裡,其實要很小心判斷位階關係,如果拍攝氛圍不對,我們也沒有權力多向導演提議什麼。」 總而言之,拍攝劇照是一場高壓的馬拉松,她得時時刻刻卡在攝影機旁,早晚輪班不定,「可以說是演員拍多久,我們就要跟多久。這樣長時間等待重要畫面出現,時間的控管也不自由,長期下來,我的身體出現了一點狀況。」 於是,她決定讓自己轉一個彎。不是不拍照了,而是轉而拍攝表演藝術領域。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關於攝影,劉璧慈還想說的是……
有一場攝影,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有辦法完成要拍攝的是蔡康永的實境節目,當時他訪談林志玲,中間只有10到15分鐘的空擋可以拍靜態照片,但我要一口氣拍出很多種不一樣的畫面給媒體使用。那天單槍匹馬上陣,製作單位是中國方,來了很多人,藝人本身也有自己的經紀人,加上現場時間緊迫,每次遇到這些稍有氣勢的名人、要他們擺拍我也會小有壓力,無法預知你給出的指令他們是否願意進行?結果卻意外地順利欸,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到外面的花園結束這場拍攝,到現在想起來,我都覺得是上天有在幫助我(笑)。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鄭達敬:懂音樂愛音樂,在怦然心動中按下快門
空間也許真的會形成一個磁場,使走入其中的人延伸出些微妙的改變至少鄭達敬是這麼相信的。 他回憶,2013年,北藝大研究所放榜的那一天,得知自己考上了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那時他才在國家音樂廳拍完一場演奏會,走到戶外的時候日光已漸消退,「站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正中間,我忽然就想說來許個願好了?」鄭達敬當時許下的願望是:「我希望可以在這棟建築物裡上班,我想在NSO(國家交響樂團)工作一陣子。」當時,他還是個四處接案的自由攝影。這個當下聽起來不太實際的願望,沒想到不久後便實現了。 從音樂學習到拍攝音樂人 自年幼起,鄭達敬的生活就離不開音樂。從中規中矩的鋼琴學習,到中學時期加入管樂團開始修習單簧管。音樂之於他是人生重要的夥伴,且當年決心要從馬西亞到台灣留學,本來想的也是就讀音樂系,「不過當時網路查資料的便利性很低,陰錯陽差之下,我沒有緣分到音樂系。所以轉念一想,如果可以學一個能夠助人的專業也不錯?因而進入了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鄭達敬描述,他也是來到台灣以後才開始拍照的,起先純粹為了記錄留學生活,到後來顯然不只如此。作為心理系的學生,鄭達敬卻幾乎一有時間就跑去音樂系的教室溜轉。他說:「我每天都會背著相機去學校,不管是同學、老師上課或者要演出都可以拍個不停。」 當時,鄭達敬感覺古典音樂的拍攝記錄占比少數,獨他樂此不疲,久而久之,他的攝影也開始在音樂系上廣傳,爾後學長姐、乃至同輩的畢業音樂會,也都找他友情拍攝。再過一段時間,這事就從校園傳出,開始有業界的團隊相邀,口耳相傳,他開始從學習音樂的路途,成為拍攝音樂會的不二人選。 且拍且走,待他成為自由攝影師好一段時間,2019年鄭達敬接到一個案子,是NSO有一個音樂會宣告的活動,他在現場看著指揮呂紹嘉與其他媒體的互動,其實心裡有些悸動:「以前都會覺得他是個大師啊,應該非常遙不可及,那天第一次那麼近距離看到,見他忽然轉頭過來朝這裡一笑,我就按下快門了。」 那張不經意捕捉下來的照片,後來有好長一段時間被呂紹嘉當作個人照使用。鄭達敬說的時候,語氣甜滋滋的,說:「同年9月,我第一次受邀進音樂廳拍攝NSO的演奏會。」那一刻,他許下的願望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關於攝影,鄭達敬還想說的是……
我去年(2024)和幾個近期造訪過巴黎的夥伴,安排了一個「 Flaneuring Paris」旅遊攝影展,展覽或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我和攝影之間的關係。雖然拍攝音樂讓我很快樂,不過還是需要一些不同的元素才能夠給我新的刺激,旅遊就是一件很好的經驗。我拍過很多不同的旅遊,比方說2014年到2020年這段期間,曾跟著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造訪瀨戶內國際藝術祭那個村莊很小,每年秋天都有重要祭典,但因為人口嚴重外流的關係,祭典作為凝聚人的功能也逐漸衰退,例如逐漸沒有足夠的人力來扛大轎。我在現場捕捉畫面的時候,也和當地人建立情誼,好像我在城市中養出的疲倦,都能夠在這個村莊中被洗去。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可以把這些感受也帶回台灣。 這次在巴黎的展覽,也有類似的企圖:「 Flaneuring Paris」是我跟兩個朋友共同籌備的,挑選了3間適合的咖啡館,用一種近似巴黎氛圍的城市行旅狀態,讓讀者有感受「邊走邊觀賞」的氛圍。展期到12月1日,也很歡迎大家有機會來看看。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李佳曄:即便重來一次,我也會在漆黑中奔跑
李佳曄是金門人,因此圈內熟識者也喜直接稱其為「金門」。某天早上,他接到一通電話,劈頭就問:「金門,你生肖屬什麼?」彼時他還在床上昏昏沉沉,身子還有一半泡在夢裡,迷迷糊糊地說:「我屬牛。」只聽對方再問:「那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合作?」這個問句聽起來還像是在夢裡一樣,李佳曄瞬間轉醒電話那頭,竟是編舞家鄭宗龍。 彼時鄭宗龍還是雲門2團的編舞家,而李佳曄還在嘗試各種攝影的可能,兩人過去因工作有幾面之緣,但說起李佳曄真正獨當一面拍起雲門舞作,又或者是投入進表演藝術攝影的決定性瞬間,大概就是這通電話了。 一張很棒、卻無法滿足創作者的照片 李佳曄退伍後,輾轉透過朋友的介紹,開始跟著攝影大師劉振祥工作,如人所知,劉振祥是雲門舞集的御用攝影師,李佳曄形容當時跟著學習的感覺,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真的。時至今日,我還是一直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然而,「跟在攝影師」身邊工作,所指為何? 每個人的工作節奏都不同,對李佳曄來說:「劉老師的步調很快,畢竟攝影現場的時間寶貴,你甚至不能等他說了以後才去做。比方說打燈好了,老師有時候不會給什麼指令,直接就自己去調燈光了,剛開始我看了很錯愕,想說這樣我能夠幫什麼?」李佳曄接著說,他只能加快節奏,努力跟上老師的步調,從而發現,仔細留心現場也是工作的一個環節,「總之,不懂就主動問,覺得光不太對就試著調整。」 2010年,李佳曄跟著劉振祥走進實驗劇場,「老師問我要不要拍拍看?那場舞作是何曉玫的《Woo!芭比》。」他點頭應允,照直覺亂拍,最後的結果是:「照片我自己看得很有感覺,但老師跟我說這樣沒辦法接案,他說:『這種照片就是你自己覺得很棒,可是沒有辦法滿足編舞家的需求』。」 那麼,創作者的需求是什麼?在表演攝影的鏡頭之下,那大概不能只有美,而得涵蓋的故事,包容資訊,具體而微地展現這個作品的情感。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關於攝影,李佳曄還想說的是……
其實,除了劇場之外,我每年回金門都會四處走走,記錄故鄉的模樣。冬天的金門通常沒有什麼人,整個地方灰灰的,我很喜歡那種荒涼、平靜的感覺。如果未來舉辦攝影展,我其中一個想拍的畫面,就是金門的「互花米草」。我拍攝的幾張照片,面向海岸,乍看之下像是某種海埔新生地,實則是嚴重氾濫的外來物種,導致海岸線陸化,潮間帶消失,其中許多豐富的物種也連帶不見了。這樣的景象,10幾年前我還看不到,但一年一年回來,發現它是以幾公頃的速度在增長,再這樣下去,以往金門的海景意象或許就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草地可是,第一次看到互花米草的時候,我覺得很美,非常美。之所以會覺得美,卻是因為無知的緣故。若有人第一時間看到這張照片,大概也覺得這很美吧?但如果知道背後隱藏的議題性,這層「美」還存在嗎?若說我能以攝影為家鄉做點什麼,或許這是我能夠做的事。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林韶安:以照片留下真實,彌補失落的曾經
約莫是國小五、六年時,林韶安拿著家裡的傻瓜相機四處拍攝,「當時多是用來記錄我身邊很重要的人。」林韶安說,年幼時的無意之舉,其實已預告了日後她對於人像攝影的流連往返。 大學投入大眾傳播專業,更加留心於每一張照片所傳達的資訊情感,「例如看到世界新聞大獎的得獎照片,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竟然可以把人拍成這成這樣?好像自己會整個被吸進去一樣。」林韶安說。隨著年紀愈長,她對於人像攝影的著迷更加深厚,好像是強烈地意識到,終有一天所見之景將隨時光流逝,唯有當下的攝影能夠稍微彌補一些遺憾,使重要的回憶有個憑據來記得。 一張照片就占滿報紙頭版 千禧年前後,報紙新聞仍是台灣媒體的主力之一,林韶安對於媒體的認識也大概是從那幾年開始累積起來。「以前的報紙圖文非常有力量,一張照片就有可能占據整個頭版版面。那時候看了真的會覺得攝影好厲害,一張照片就可以傳達這麼多資訊。」她說,並從而開始轉入攝影這條路。 不過,捕捉畫面的能力是一回事,要「上哪兒找素材」又是另外一回事。新聞攝影,需要敏銳地去感知到現場的能量流動,並在此盤旋等待。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報社實習工作,恰好是7月左右,就碰到高中生大考,所以我連續3天都去考場那邊繞。」 林韶安回憶,她現在還記得,那時候她捕捉到其中一張照片是這樣的:待所有考試終於落幕的第3天,她人在師大附中,高三生從考場走出,興奮地互相潑水、彼此擁抱,發了瘋似地慶祝考後的激動。「當時拍到那張,我就隱約能夠理解為什麼每次大考中就有攝影在這邊等,因為這一刻高昂的情緒,真的能夠讓攝影師獲取一些什麼。」 林韶安把話說得很含蓄,她口中攝影師所獲取的「什麼」,好像也常常將她拉入每一個鏡頭聚焦的靈魂之中,隨之一同悲喜一同歡騰。當自己也深深投入在現場的情緒以後,「即便是拍攝很簡單的人像,都會感到心動。」她說。 至於後來是如何轉入表演藝術圈拍攝的?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關於攝影,林韶安還想說的是……
我還記得剛接案時,有次要做一場人物專訪的攝影,拍攝對象就是林懷民老師。那大概是2010年前後的事情?我跟著文字記者到場,林老師一坐下來就說:「我們聊聊天就好。」其實林老師自己一個人滔滔不絕就能講一小時,而原先列出來的採訪大綱,好像也已經在網路上有相似的談話,所以他就先將主導權放在自己身上,看能不能再多給記者一點東西。總之,我看到這一幕就被嚇到,他本來就氣場強大,要拍出新意不容易,但現場就是個中規中矩的會議室,我一直害怕沒辦法拍好,當天在那種氣氛下結束了後來,我一直惦記著此事,總覺得沒有真正捕捉到林老師的精神。所幸日後在一場雲門的記者會上,再次有機會與老師相遇,捕捉到一張他說話的照片,事後雲門公關跟我說老師很喜歡那張照片,有抓到他的神韻。從事攝影,我覺得最讓人安心的,大概就是這句話了吧?
-
 焦點專題 Focus 側記秋天藝術節座談「特別企劃╱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上)
焦點專題 Focus 側記秋天藝術節座談「特別企劃╱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上)採集生活的鍾適芳,探訪中間地帶的高俊耀
「本場講座,沒有亮點、沒有攻略,純然聊天。」主持人賴依莉如是開場。 9月初的「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講座,集結2024年秋天藝術節的4位創作者,舞台布置如客廳一樣,卻又聽賴依莉隨後自嘲:「大概會有人詢問,既然是與創作無關,為何仍要選在劇場進行這場座談。但老實說,劇場是我們覺得最親密的地方。」在這樣既是公開又可以私密的場所,眾人彼此相遇,聽一場「與創作無關」的故事,關於這些創作者如何成為他們自己,也關於他們的生命印記如何匯流成河當日,賴依莉沒有說謊,創作者也如實努力地不談創作,然而他們的日常經驗,樸素卻充滿力量地、讓人有一種「藝術,原來如此」的輕盈之感。 4位創作者分別是:《人之島》的編舞家王宇光、《島嶼恍惚》編舞家林宜瑾 、《暗夜・腹語・鬼托邦》編導及演員高俊耀、《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音樂影像現場藝術總監鍾適芳這些創作頭銜,撇開作品名稱不談,也都是他們長年掛在身上的。不過,在這場講座以後,或許我們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他們。 因此,不妨讓我們按照順序,讓這些介紹從頭來過。他們分別是:釣到一隻大魚的王宇光、在三合院闖蕩的林宜瑾、在餐廳裡寫作的高俊耀,以及10歲那年受到毛利族民謠所震動的鍾適芳。 如果你對後者的介紹更感興趣,那不妨跟著文章順勢讀下去。且因4位藝術家分享內容豐富,文章將拆分為上下兩集,本篇聚焦在鍾適芳如何採集生活的塵埃,以及高俊耀如何聊起他童年的餐廳光景。
-
 焦點專題 Focus 側記秋天藝術節座談「特別企劃╱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下)
焦點專題 Focus 側記秋天藝術節座談「特別企劃╱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下)重新與世界連結的林宜瑾,釣起命定大魚的王宇光
「本場講座,沒有亮點、沒有攻略,純然聊天。」主持人賴依莉如是開場。 9月初的「題外話:跟創作無關的事」講座,集結2024年秋天藝術節的4位創作者,舞台佈置如客廳一樣,卻又聽賴依莉隨後自嘲:「大概會有人詢問,既然是與創作無關,為何仍要選在劇場進行這場座談。但老實說,劇場是我們覺得最親密的地方。」在這樣既是公開又可以私密的場所,眾人彼此相遇,聽一場「與創作無關」的故事,關於這些創作者如何成為他們自己,也關於他們的生命印記如何匯流成河當日,賴依莉沒有說謊,創作者也如實努力的不談創作,然而他們的日常經驗,樸素卻充滿力量地、讓人有一種「藝術,原來如此」的輕盈之感。 4位創作者分別是:《人之島》的編舞家王宇光、《島嶼恍惚》編舞家林宜瑾 、《暗夜・腹語・鬼托邦》編導及演員高俊耀、《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音樂影像現場藝術總監鍾適芳這些創作頭銜,撇開作品名稱不談,也都是他們長年掛在身上的。不過,在這場講座以後,或許我們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去認識他們。 因此,不妨讓我們按照順序,讓這些介紹從頭來過。他們分別是:釣到一隻大魚的王宇光、在三合院闖蕩的林宜瑾、在餐廳裡寫作的高俊耀,以及10歲那年受到毛利族民謠所震動的鍾適芳。 如果你對後者的介紹更感興趣,那不妨跟著文章順勢讀下去。延續上篇,本篇聚焦先後造訪過印尼的林宜瑾與王宇光,分享他們的生命因為那趟旅程,曾彷彿與自然連結的那一刻。
-
焦點專題 Focus 國家兩廳院導覽志工
姜佩德:這份工作,是從母親手中接棒的
本身從事國際貿易採購的姜佩德,幾年前因工作型態轉變,開始能夠自由分配自己的時間,而她第一時間做的竟然不是休假放鬆,而是報名了國家兩廳院(下稱兩廳院)的導覽志工徵選。 對此,她的回答是:畢竟是由母親手上傳承下來的傳承的不是營利之事,而是服務的意志。 與兩廳院一起長大 「我的母親過去就在兩廳院擔任前台志工,我算是跟著兩廳院長大的吧?」姜佩德說。 事實上,在母親擔任志工以前,姜佩德就曾經嚷著父母能否帶她來這裡聽音樂會。當時她是個國中生,「有一位好喜歡的鋼琴家來這裡表演,可是票價不便宜,父母當時替我買了一張票,讓我自己走進去,他們就在外散步等我結束。」姜佩德說,也不知道是否正是這個因緣際會,讓母親日後竟也主動申請兩廳院的前台志工,開啟了長達10多年的志工生活。 「當時我覺得媽媽很厲害,早上在桃園上班,下班就衝來做前台。有些節目早一點可能9點半結束,不過有些節目到10點、10點半才結束的都有。」姜佩德回憶,當時她看待母親,有敬佩,也有困惑,無法理解母親為何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這麼疲倦? 然而,輪到自己當志工時,這疑問輪轉到她父親身上,姜佩德笑說:「我住在新竹,每次回台北找爸媽、也都會排班兩廳院的志工,我爸總是問我幹嘛這麼累。」雖說如此,旁人更無法理解的是:志工服務對姜佩德來說,不是工作,竟是一種紓壓。
-
 焦點專題 Focus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導覽志工
焦點專題 Focus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導覽志工李思緯:我所信仰的,是社會的善意
年僅23歲,就擁有海內外多種志工經驗的李思緯,從來不覺得自己因此「放棄」了什麼。 甫自大學畢業,此刻的她,正遊走在與家人約定好的Gap Year之中。 「我的父母親從以前就一直鼓勵我們多方嘗試,不要那麼快就定錨自己的出路。」李思緯說,受到這樣的家庭教育啟發,她自高中開始就積極投入YMCA 的海外志工服務,大學期間因疫情之故,又轉而尋找台灣的志工機會,適才輾轉遇見了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下稱北藝中心)的招募訊息。 帶著工地帽的培訓志工,如今依舊在 李思緯是最初受訓的那一批志工,彼時還得帶著工地帽走進現場認識這個空間,如今晃眼就是兩三年,她已然成為北藝中心的固定導覽志工,無論有多忙,都會努力主動尋找適合自己的班表。「我其實還蠻享受身為導覽志工這件事的。」她說。 李思緯坦言,在接觸北藝中心之前,她與「劇場」二字離得很遠。然而,實際在成為導覽志工以後,親近的卻不只是藝術領域,更是對於人的想像。她解釋:「身為這個地方的導覽志工,接觸的客群真的很不一樣,往往未必是走進來看戲的人,可能就是剛好來附近的兒童新樂園逛逛,順道繞過來這裡聽導覽;又或者是,他們感興趣的不是藝術,而是建築本身。」 在北藝中心志工服務訓練過程中,除了口語訓練之外,也另外增加了肢體表達的工作坊練習。「我其實不是這麼善於表達的人,不過的確因為這些學習而增添很多信心。」如今,說出這些話的李思緯,雙眼明亮而清澈,大方地直視人的模樣,很難想像她過去曾羞澀於表達。
-
 焦點專題 Focus 紙風車劇團志工
焦點專題 Focus 紙風車劇團志工涂宥柔:成為「追風者」,跟著演出就像追隨慶典
紙風車劇團的志工們,有一個很美的名字,稱作「追風家族」,而涂宥柔正是這個家族的元老級人物。 一開始,他們只是一群單純的「追風者」,顧名思義,就是「追著紙風車」巡演的人。「像是我們是住苗栗,但如果知道彰化哪一週有活動,就會帶著孩子南下,玩個兩天一夜。」涂宥柔說,回憶這些年走訪台灣各地的旅遊經驗,幾乎都是以紙風車為座標,南北各處旅行。 因為「順道」,就成了追風家族 倒是,追風者怎麼就成為了志工了呢?起因非常單純,「其實看戲看久了,跟工作人遠都會認識。有一次我到現場,看到工作人員還在排椅子,一群小女生在搬很重的東西,我跟先生就主動過去幫忙。」涂宥柔聊起這些經驗,不像是在談志工的義務,反倒都是非常自然的反應,都是日久生情後的順手,其他像是「順道站個服務台賣東西」、「順道與其他的追風家庭成為好友」 一切都發生得太自然了,「久而久之,我們有一批固定會早早到現場看戲的家庭,不約而同幫忙起來。彼此的孩子就在一旁遊戲,大的照顧小的,好像每個人都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一樣。」 於是乎,這份自然的情誼,先是成立了臉書社團,進而加LINE常保連繫,成為了一個由看戲成員自行發起的活動。乃至後來紙風車劇團正式為其掛名,追風者開心不已,「能穿著紙風車的衣服,我們都感到與有榮焉!」涂宥柔說。
-
焦點專題 Focus 草草戲劇節志工
賴囿任:投入,是不希望那些美好消失
正港嘉義人,賴囿任看待阮劇團的草草戲劇節,就像是一期一會的盛大慶典,充滿年輕、活力的藝術氣味。 平時的賴囿任,任職台塑擔任品管員,假日則是新港舞鳳軒北管戲劇團的樂師,「所以,起初我是以表演嘉賓的身分,接觸草草戲劇節的。」賴囿任說。 從表演嘉賓,走上志工之路 被此熱情所吸引,賴囿任後來幾年便主動申請草草戲劇節的志工服務,頭一次是被放在處理各項雜事的場務工作,第2次參與則投身第一線的服務組,負責買票與路線導覽工作。過去,他也曾經覺得「志工是在消耗時間,不然就是大學生賺學分點數才會去做的事情。」然而實際參與後發現,「大家不為錢、真心以熱忱投入一件事情的感覺,真的很好。」 「很神奇的是,會選擇當志工的人,大概身上都有某些對應的頻率。」賴囿任回憶,自成年以來,最能夠頻繁認識朋友、接觸不同群眾的機會,大概就屬志工服務了。 他舉例:「我們會因為現場的各種狀況,而培養出革命情感。如人所知,草草戲劇節的活動是延伸到戶外的,其中也包含餐食引用的販售。有一年,傍晚時分,打掃阿姨下班了,廚餘桶連帶收走,有些人大概看到沒地方可以丟,竟然就直接把廚餘倒在花圃裡。」聊起這件事情,賴宥任聳聳肩,道:「還是要面對啊,總不能放著。不過當時LINE上講一聲,不同組別的人全都來幫忙,沒人想要推託。」 這樣的情感積累,使藝術節結束以後,大夥兒仍頻繁聯絡。
-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導演 陳品蓉(一)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導演 陳品蓉(一)像株蔓生的植物,做個等待的人
劇場作品有各種形式,屬於陳品蓉的那一種,則像植物一般。 從2019年的《剩人》到2023年的《RJ and others》,陳品蓉擅長如拼貼之鏡頭影像,捕捉抽象的時代氛圍不過,標籤是人在貼的,所謂風格者,她也沒真的放在心上過。「與其說形式多元,倒不如說,我可能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吧?從小如此,一個主題也想著如何能多方發散。」今年11月推出新作《青春》亦然,她集結了20到60歲的人聚於一個舞台上,共同蔓生,如植物循著光走那樣,他們位在各自的座標上,試圖與青春對話。
-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導演 陳品蓉(二)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導演 陳品蓉(二)在摸索中走向藝術,在空白中生發創作
讓我們稍微讓時間倒轉在走進劇場以前,陳品蓉有段時間是在其他藝文場所一面工作、一面探索。 「我一直都對生命有很大的疑問,所以大學期間,什麼能做的事情我都會去做,打工、家教、系學會、到其他系的課程瘋狂旁聽」陳品蓉說,她最後隱隱感受,藝術或許是能安放眾多問題的所在。「但所謂的藝術,到底是什麼?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我經常能感覺一個作品觸動我,會使我哭、使我融化,但我對那圈子一無所知,當時就抱持這個疑問,走進不同的地方試試看。」 其中,她也試過在畫廊的工作。她回憶:「畫廊經驗包含了創作、行銷和買賣,在那之後我內心更確定,在藝術的場域中,我更想靠近創作端。因此,可以說我是近乎瞎打誤撞、或者幸運地找到劇場。」 陳品蓉聊到最初面向劇場的選擇時,聲音會變得很輕很輕。她形容,這世界沒有什麼地方跟劇場一樣單純,又一樣複雜。「它就是一個空間,卻彷彿能夠安放所有,聲音會有共鳴,情感能有共振,文學在其中被擺放,建築在裡頭能夠成立。而這一切的成形,又是那麼地朝生暮死,演完就被拆光了!」陳品蓉相信,最終就是這樣的黑盒子,收束了飄飄蕩蕩的自己。 也因為曾經感受過那樣的飄泊、所產生的困惑與震盪,是能夠激發出何等強壯的創作能量,使陳品蓉日後在排練場上,經常不拘「素人或專業演員」的界線,且期待兩方所激發的花火為何。本次的《青春》也是這麼一回事。
-
 焦點人物 金曲歌王、演員
焦點人物 金曲歌王、演員許富凱 一人飾三角,唱出條通裡的寂寞與絢麗
2023年底,金曲歌王許富凱推出全新專輯《五木大学》。或許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些知門道的觀眾,就在期待此作品登台演出的那日畢竟,攤開專輯製作名單,作詞人有MC JJ、詹傑、呂筱翊等頗具名氣的劇場工作者,製作方面又是聯合瘋戲樂工作室的王希文出擊,企圖心十足。 果不其然,脫胎自專輯概念的戲劇作品《五木大学夜の女王櫻子媽媽》即將於今年(2024)11月登場,許富凱透露:「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劇本,有笑有淚,光讀本就很有感覺,至於我這次要挑戰的角色也比起以往的難度更大。」 從想像的寂寞裡出走 許富凱幾乎是拿著麥克風長大的。 國小擔任婚禮歌手、接著參加電視節目,彼時深刻的台語唱腔,搭配其稚氣的臉龐,那樣的衝突感也讓他得以征戰各個歌唱現場。幾乎可說,他在還不知道歌曲為何的時候,就浸泡在各種悲催的唱詞之中,童年時期也一度質疑:這樣的生活是否真能讓自己快樂? 不過,那些疑問在日後來看,似乎都逐一找到了解答。 「以前有段時間的確會覺得,唱歌是為了達成父母的期待。可是現在回頭來看,我感覺許多事情都是註定好的。」許富凱說,他對於台語歌的愛是後知後覺才浮現出來的,待成年以後才正視自己對此的情感。 「大概是從我發現,原來音樂能夠讓人心境上有些改變開始吧?」許富凱回憶,讓自己從「被動」的表演,轉而成為主動、甚至帶有使命性地唱出社會底層的心聲,關鍵點便是感受到音樂的穿透力。這一路上藉由歌聲所串聯起來的人與事,似乎隱隱為他搭造了一條軌跡,使他在這軌道上開始能夠為自己而唱。 這樣的改變,似乎也讓他詮釋台語歌的聲音更加輕盈,且收放自如。 台語歌曲的氛圍,長年來多藏著寂寞、傷痕的元素,從小唱到大的許富凱,過去以「想像力」詮釋,難免用力過了頭,他說:「過去的我時常有種不甘寂寞的心理狀態,但進入演藝圈後,面對的人變多了,反而發現一個人的獨處非常重要,需要適時放空,需要想事情,現在反而更享受寂寞,這是對自己的是一種沉澱。」
-
 焦點專題 Focus 女高音
焦點專題 Focus 女高音林玲慧 生活中用盡全力,讓台上看來毫不費力
論及台灣的女高音,林玲慧絕對是其中佼佼者。訪問現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暨系主任的她,原以為聲樂這個主題在她口中會充滿各種拗口的學術名詞,沒想到其實她重複最多的詞是「生活」,次之則是「愛」。林玲慧說:「我一天最多只排3個指導學生,3個教完我嗓子就啞了。」實在是沒辦法呀,她也經常提醒自己要冷靜、平靜地指導學生,可是:「我克制不住!曲子呈現出來的張力就是這樣,我怎麼可能平平淡淡地說明,就要學生了解呢?」在義大利生活超過13年,返台後的她身體裡仍飽含當地熱情的靈魂與活力,並將同樣熱切的愛與心意持續灌注在歌唱之上。 你吃過夠多的spaghetti了嗎? 歌劇源於生活,而生活離不開語言。林玲慧當初為了讀懂多數歌劇的語言,因此動身前往義大利唸書。 「剛到義大利的時候,一開始真的覺得蠻累的。」多年前,林玲慧前往向歌劇大國義大利取經,她腦中塞滿各種技巧知識,希望能夠面面俱到地磨練自己的細節,連語言學習都做足準備,卻不知第一時間衝擊她的是當地人生活的熱度。 她舉例:「早上7點,我到咖啡廳點杯飲料,店員就會充滿精神又朝氣地問你『今天想喝點什麼呢?』」林玲慧模擬當地人說話的樣子,身手並進,眼神炯炯發光,對比她平淡的詢問,簡直像是白晝與黑夜的區別。 「可是我後來發現,要唱好歌劇應該是從認識他們的生活開始,否則光是把語言學好,那也只是學到了毛皮。」林玲慧說。 所謂生活者,是真正浸泡在日常之中。因此林玲慧也喜歡提她老師朱苔麗說的話:「她告訴我,你沒有吃夠幾年的spaghetti ,你是唱不出來像樣的義大利歌劇。」小事從食物的選擇,大事則如情感的自由展現,原先只想趕快取得文憑、練好技巧的林玲慧,因此一口氣待了十多年。靈魂有半邊都浸泡在義大利的生活之中,幾乎要就要成為當地人了。 總而言之,讓自己一再「成為」另一種人的方式,而非「扮演」,而是好好生活。這樣的觀念,也是林玲慧日後一再提醒自己的初衷。 歌劇畢竟是生活,看似高大上,實際上「我覺得很像是台灣的八點檔啊,《瑪儂.雷斯考》丟個手帕想要心上人注意到他、《蝴蝶夫人》痛苦於心愛的人離開她,類似的情節我們也在電視上看過吧?」林玲慧一邊說著,笑得大大咧咧,解釋:「我不覺得這樣的形容
-
 焦點人物 歌手、演員
焦點人物 歌手、演員鄭宜農 願你自由迷惘,在我歌聲落下處
由鄭宜農擔任主演的舞台劇《妳歌》,是一部橫跨半世紀的故事,同時,也將帶領觀眾一口氣橫越半世紀的曲風變化。本次她雖然擔任主演,但也拍胸脯保證自己在這個作品的演唱比例之高,甚而得從往昔曲式蜿蜒的台語老歌曲風,一路推進到現代歌曲脈絡,她強調:「我絕對會在這齣戲裡,大量地唱!」 能歌能演的鄭宜農,長年試探過各種可能性,一面衝撞主流、一面守護內在的核心價值,並說道:「我經常思考在不同身分的創作載體上,如何把我,以及我的作品好好地送出去給這個世界。」 我們所在乎的共通點,不外乎是真誠 如果要成為一個持續創作的人,不能夠只是創作而已,「這可能就是一種身為表演者的覺悟吧?但有了覺悟以後,作為表演者的我,也會慢慢侵蝕身為平凡人的我。」她說。 「其實一直到幾年前,我都還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表一些比較私密的、情緒性的一面,但現在幾乎沒有了。」鄭宜農說,覺悟是立即發生,改變卻得循序漸進,此刻的她漸進式地明白話語權的影響力:「現在如果真的發表什麼看起來比較隱私的東西,都是我思考了很久,覺得這樣做有其溝通的意義,才會去執行。」 然而,改變不必然意味著要「背對真實的自己」。 鄭宜農的創作特質,與她面對世界的方式有其共鳴,那是輕輕觸碰,溫柔以待。 她分享:「2019年發表《給天王星》的時候,是我第一次有那樣的覺悟,想要狠狠衝撞主流市場。所以公司請了企劃團隊,發出了超大量的新聞稿,收到各式各樣的採訪邀請。」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她也是在那時候一口氣感受到各種猝不及防的提問,關乎感情、家族、各種八卦等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感受到的還有這是一群很真實的人,他們也跟我一樣努力想把工作處理好。而我們所在乎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與人應對的真誠與否。」她仍舊小心翼翼,卻能更大方面對各種提問,更好地表現了自己的真實。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這種「醜醜的樣子」,也是劇場最好的樣子
一度引起極大討論的電影《怪胎》,於2023年由瘋戲樂工作室改編為音樂劇作品。劇中,王希文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音樂調性,結合大象體操的演奏魔幻呈現,此外,更搭配導演洪千涵獨樹一格的氛圍,使作品更添迷離奇幻。 這也是洪千涵首次執導的音樂劇。過往以沉浸式劇場引發高度討論的創作特性,並不阻止她往各種面向的演出走去,例如在疫情期間的線上演出作品《嗚嗚嗚OHOHOH》(後改名為《北棲》),或是今時今刻的音樂劇《怪胎》。 洪千涵相信,重點不是形式,而是此刻存在的必要性。她在乎:「為何我們要在這個時代去面對這個議題?為什麼這個作品需要在此時發生?無論面對什麼作品,這都是我最在乎的一件事。」 因此,洪千涵與《怪胎》碰撞的契機,當然亦是某種天時地利人和所致。她在2019年曾參加北藝中心辦的音樂劇人才培育工作坊,從中發掘了導演的更多可能性,甚至也撿拾起諸多童年的回憶,包括:「我想起自己小時候非常非常喜歡《真善美》這部電影,大概看了20、30次有吧?算是我的音樂劇啟蒙。」 所以,瘋戲樂《怪胎》的執導邀請,洪千涵當仁不讓。只是當時自己還沒有直接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她的第一齣音樂劇,更是她第一次面對「改編」電影與劇場的距離在哪裡?改編後的主題應該更加聚焦於最初、或勇敢發散出去各種問題都在正式工作後一次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