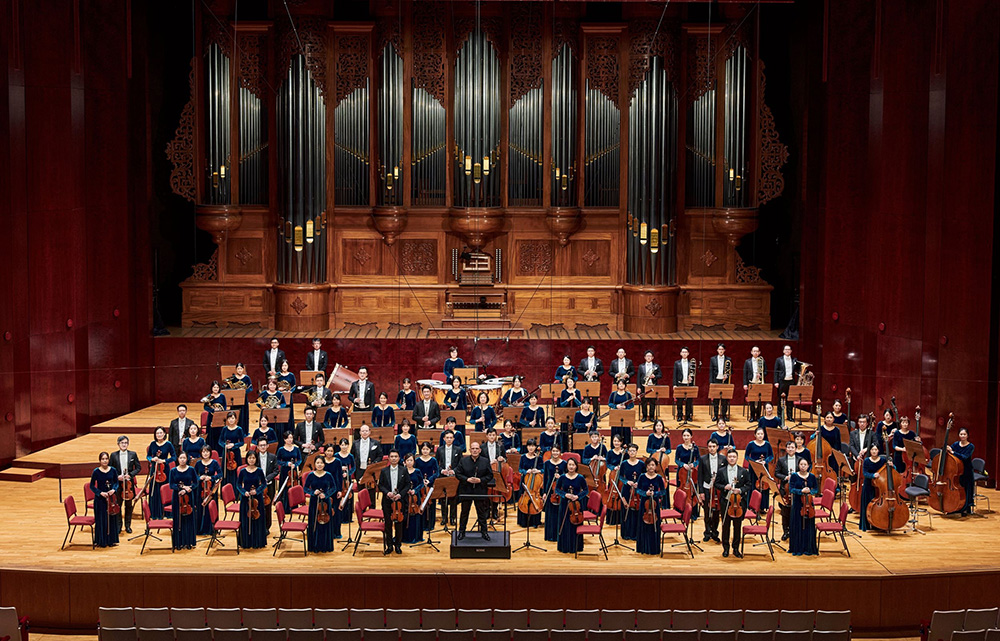两厅院「法国系列」打头阵的卡洛塔舞团,其演出的《唛唛族》及《唛唛族的小孩》,藉著简单的灯光服装、生活化的舞蹈动作,让人看见现代舞蹈充满幽默创意的面向。编舞家黎美光特为本刊专访了该团艺术总监及编舞家卡洛塔,让读者看见,这位卡洛塔先生「简单」之下的「复杂」。
卡洛塔舞团是由编舞家卡洛塔(Jean Claude Gallotta)于一九七九年在法国所创办。他这一次来台湾所演出的《唛唛族》Mammame及《唛唛族的小孩》L’Enfance de Mammame,充满了他对儿童及当时舞蹈风格现象的一些反应。是一个十九年前所编的作品,他当时创作的动机是想要放弃「编舞」的概念;他认为,舞蹈是代表一个社会现况的最佳写照,每一个时代的风格及特色都会被舞蹈所呈现出来。
在廿八岁之前,卡洛塔是一个画家,因为老师鼓励他「多到画室以外的世界去看,去画一些『会动的人』」,所以他接触了舞者与舞蹈,也因此走上了编舞、舞者之路。
在这次访谈的过程中,他说到他是个焦虑的人,所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以及创作上,他用「简单」来应用在他的编舞里。以下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大约认识一个法国编舞家卡洛塔先生,也希望从认识西方的创作中,看到台湾的舞蹈现象与特质。在越明了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显像,也会更清楚。
黎美光(以下简称黎)—我看你在《唛唛族的小孩》里面,有许多关于「爱」和「希望」的传达,我想要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你当时候的关心?
卡洛塔(以下简称卡)—我只是在表现一个已经绝望的人的渴望。我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焦虑的人,也许因为我本身的个性是这样,我总是会希望事情可以做得到很好、世界可以很美好。可是这种期待其实是一个对世界焦虑、绝望的人的期许。譬如说,那个「投射灯」,他们其实试了很多遍,可是投射灯一直没有回来。那投射灯是最后面、最后一分钟才回来。我觉得编舞其实也可以一直到最后投射灯都没有回来,希望并没有实现,也是有可能的。
创作就是要找到「情节的诗」
黎—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舞者、编舞者以及电影导演,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不同的角色?它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以及它的挑战在哪里?
卡—对我来说当一个导演、编舞家或舞者都是一样的,它的共同基础就是要找到「情节」,一个连贯的情节。你也许看不太懂它们在讲什么,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再看下去,而不会觉得好像前面接不到后面。然后我在这个情节里可以找到「情节的诗」,诗意跟那个节奏。。
黎—我知道你曾经在日本的静冈大学担任过系主任,就是一九九七年那时候,可不可以请你聊一聊,你对亚洲的接触,还有你现在也跟蛮多亚洲舞者一起工作,这些经验在你的创作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卡—一开始的时候,日本那边希望我过去组团,所以我就过去组了一个八个人的团,在学校里面。可是我其实没有完全在当一个编舞家。当时是三年的合约,我先组团,然后就开放征选一个日本的年轻编舞家来带这个团,之后再去选另一位亚洲编舞家,再继续下去,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在日本因为舞蹈跟戏剧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最后合作的经验并不如我所预期的那么顺利和完整,我后来就离开了。不过也是因为那个经验,我现在有日本的舞者跟我一起跳。
因为容易焦虑,所以喜欢创作「简单」
黎—通常我们在看舞蹈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舞蹈里面看到这个导演的个性,因为你之前有提到,你其实蛮焦虑的等等,可是我看了《九九双人舞》99 duos,然后我看《三代同堂》,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导演的个性是焦虑的,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发现,可不可以聊一聊,你说你自己是焦虑的,可是从作品不太看得出来。
卡—我其实不太清楚观众有没有看出我的焦虑,可是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跟人家相处或是生活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生活得越简单越好。而且我的舞作大家看得出来其实是很简单的,灯光、各方面其实都非常非常地精简。
黎—编舞这件事情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那在你决定编舞这个工作之前或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人曾经启发过你?是谁,然后是什么?
卡—在我成为编舞家之前,我其实是受到很多电影导演的影响,有高达、费里尼、布纽尔(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库柏力克、还有小津安二郎,然后唯一对我影响最大编舞家是康宁汉,然后还有约翰‧凯吉。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复杂,什么事情就是简化,一点也不要太复杂。我觉得我编舞的方式跟他们不像,可是这个精神是一样的。
黎—「简单」是最困难的,而且像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会特别地觉得说,真的很难得!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重要的舞团和舞作,他们的作品在全世界的舞蹈市场里面,我很少看到简单的。
卡—是的。我知道,要简单其实很难,但是这应该是一条正确的路。像我有一支舞,里面只有做一个灯光设计,从头到尾只有一颗灯,没有cue。其实一般的观众在看的时候,他都不会说,「怎么灯光这么少!?我都看不到!」其实是因为灯光并不是非常重要,观众会去注意其他的东西,动作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通常,直到我们跟他讲说,「刚刚只有一个灯光。」他才说,「喔,真的吗!?」他往往根本没有发现。这样子其实是引导观众去集中他们的视线。
为让儿童回到剧场编作《唛唛族的小孩》
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问过你,不过我可能还是要再问一次:当你在编《唛唛族》时,你同时想说要帮儿童编一出儿童看得懂的现代舞吗?
卡—没有。其实《唛唛族的小孩》这个作品是一年半前的。
黎—喔,原来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想要编这样一个作品?
卡—我一开始并没有想编这样一个作品,因为我根本不会!一直到后来,我发现怎么小孩子好像只会看电视,好像不会进剧场的感觉,那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让这些小朋友可以再进来剧场,不然以后他们好像永远都不会进来的感觉。
黎—谢谢。我其实演讲了十一场关于《唛唛族》,鼓励台湾的观众来观看《唛唛族》。现场那么简单的灯光,还有细腻的音乐,我以为真的有鸟叫声,结果是你在吹口哨……当初音乐在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你的音乐顾问合作的?
卡—通常我在创作的时候是没有音乐的,我先编舞,然后音乐家来看,之后音乐家可能就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创作,然后再来讨论。做《三代同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创作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音乐的,先有舞蹈动作,然后音乐家再来创作音乐,做一些搭配。
「我是一个生活的导演」
黎—可不可以聊一聊你的童年?
卡—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的导演,从小就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我常常建议可以怎么玩,所以,常常玩很多游戏,游戏中我希望大家都是自由的,可是我会去组织,什么人可以做什么事。我从小可能就是团体的头头,可是又是非常随和的,大家都很自由,可以随时发表意见,同时我又会给大家一些意见,你在哪个位置比较好,我在哪个位置比较好。
黎—《唛唛族》是一个十九年前编作的作品,直到目前共演了八十九场,为什么这个作品可以一演再演?
卡—我在创作每一个作品时,都希望它是超越时代、超越时间的。今年刚好是《唛唛族》来台湾演出,其实我常常会重演我自己的作品,之前是《尤里西斯》演最多场,后来是《唛唛族》变成第一名,也许是因为它比《尤里西斯》又更简单,在服装上及道具上,技术上也更简单,所以说可能也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吧!像《唛唛族》这个作品,它比较特别,它其实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地在吸收。因为它已经快演二十年了,现在进来的舞者其实都很新,比如说,日本人、韩国人,他们都有他们的文化背景,跟他们的跳舞的基础及语言,所以当不断地有新的舞者进来跳同样的一支舞的时候,那个舞就会不断地有活力。
黎—你的作品这么简单,就你个人也好、你的舞团也好都非常成功,你认为这个因素在哪里?
卡—我不知道!(笑)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当舞者,二十几岁才开始跳舞。我一开始想当画家,我的绘画老师叫我别一直待在房子里画模特儿,要出去画一些会动的人,所以我先去画运动家,有一天来到舞蹈学院,想说那里面有一些舞者,蛮好的,进去画画看。
结果一进去,全部都是女生,老师一看到我是男的,就说,「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跳」!我当时说,「可是我没钱学舞啊」,老师便说,「没关系,你帮我们舞者画画,我免费教你」。我是这样开始学舞,一开始只是想说,试试看啊,没关系。后来去参加编舞,之后就得了一个大奖,然后自己就想说,「我现在要认真做了,因为得了一个大奖」!从此,我又不断地吸收新的元素,像去纽约,吸收了很多那个年代(一九七○年代),如摩斯‧康宁汉及崔莎‧布朗等种种新的元素,算是大开眼界。但是,我是欧洲人,或许是有一种使命感,让我又回到欧洲。
黎—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看这个作品的感觉吗?
卡—好啊,好啊,太好了,我想听!
黎—对我来说,在亚洲的社会,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五十二岁,算是蛮重要一个舞团的负责人,在舞台上,却搞笑啊……我认为对亚洲的观众和舞者,如果他们知道你是编舞者本身,会是一个蛮大的解放。
卡—是!是!那是《唛唛族》跟《唛唛族的小孩》都一样吗?
黎—我觉得都一样!因为你,啊〜〜的,突然唱歌剧,或是碎碎念啊……其实那是一个蛮典型的法国味道,但是我认为你运用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法国人太多话的时候,你会很想打他,但你的那个多话就完全在舞台上达到一个很好的balance。
文字|黎美光 舞者,也是编舞家。伦敦当代舞蹈学校舞蹈硕士,曾为法国巴黎艺术村与桥头糖厂艺术村之驻村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