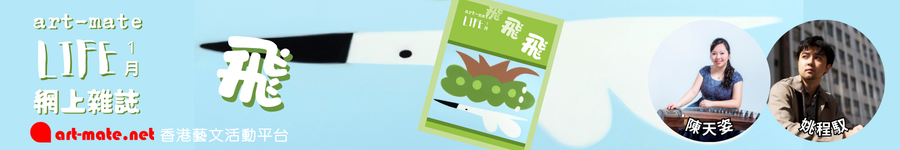当自由如空气般理所当然地存在,我们对自由的歌颂,相较于那些仍在不自由的拘禁下奋力呼求自由的人,总有几分锦上添花的虚空。不曾体会过受限与禁制,我们如何能夸夸谈论自由?从这个标准来看,伊朗籍的阿飒儿.纳菲西与中国的章诒和,则毫无疑问地,都可作为持续以书写追寻实践自由的代表人。
前些时候,有机会和电影导演杨力州说上几句话。他拍摄的纪录片《两地》即将在四月上映,描述已故文学家林海音的生平。问他,拍一个已不在人世的传主很困难吧?他说本来以为是,毕竟这是第一次以逝者为主角,但,他也因此找到了「自由」。
这样的自由说来有几分抽象。然而不久后,有两本书的阅读经验,仿佛从文字创作的角度,对我印证了杨力州口中的自由。
有时我觉得,自由不是一个该由我们奢谈的体验。当自由如空气般理所当然地存在,我们对自由的歌颂,相较于那些仍在不自由的拘禁下奋力呼求自由的人,总有几分锦上添花的虚空。不曾体会过受限与禁制,我们如何能夸夸谈论自由?
从这个标准来看,伊朗籍的阿飒儿.纳菲西与中国的章诒和,则毫无疑问地,都可作为持续以书写追寻自由,或说,实践自由的代表人。
为自己的故事做主
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罗莉塔》,数年前甫出版便造成话题。纳菲西在一九八○年代柯梅尼当政、女性恢复戴面纱等保守政策的情境下到大学教书,并秘密举行政府禁书的读书会。之后她因拒戴面纱被学校开除,并于九○年代举家迁往美国。
《在》书发行后,纳菲西的父母先后辞世。她的父亲曾任德黑兰市长,母亲是国会议员。《我所缄默的事》在父母故世后写就,不同于《在》中坦露伊朗对女性与文学的禁制,这次纳菲西的解剖刀犀利伸向家族,倾诉身为公众人物的父母另一面貌。在纳菲西诚实到令人招架不住的描述之下,母亲始终活在自己陈述的身世里,不愿面对与她真实相处大半辈子的父亲和一双儿女。深爱母亲的父亲,则在面对家庭和政治理想的双重失落中,埋首于波斯经典文学的研究。承袭双亲说故事能力的纳菲西,笔下的「故事」都是父母在世时不可能吐露的,然而透过双亲离世后的书写,纳菲西找到了诠释成长经验的自由,同时将自己从对母亲的不谅解中救赎,也让这部垄罩于伊朗纷乱年代的家族写作,从大时代到个人生命都显出一股无以名状的哀愁。
用我的笔窥探命运
章诒和以《往事并不如烟》、《这样事和谁细讲》等书,详细爬梳了作为改革派的父亲一代于文革时期的受难记,其作品至今仍是中国禁书。对亲友和自己遭受的折磨表示「到死不会忘记」的她,这回一改纪实自传的体裁,在《刘氏女》中以小说笔触描写文革女囚传奇。
称自己初次写小说,且「不写政治、不写制度」,还是看得出章诒和纪实本色。她化名为书中人物张雨荷,与其他来历不同的女囚打交道,更因政治犯背景而有机会帮人代笔「年终改造小结」,从而获知这些女囚的犯罪故事。
刘氏女杀夫的故事置之于今日也许不能再以「骇人听闻」形容,章诒和也无意著眼于残酷的分尸、腌肉过程,而是透过这样一则与政治无直接关联的「小人物列传」,呈现在欲念追逐下无路可出、循环于内心无间地狱的女犯悲哀。
章诒和在书中写道:「她的自述,是我生命中穿越黑暗的一次远征。」写作之时,刘氏女应已不在人世,而写出了这样故事的章诒和,将晦涩苦痛的囚禁生涯化为书写题材,她又从中汲取了怎样的超越和自由呢?
除了两位女作家以「存活者」、「挣脱者」的身分,以传记类型之作铭刻书写之自由外,来自塞内加尔的女作家阿密娜达.索.法勒也在台一次推出《还魂者》与《乞丐的罢工》两部小说,平实文笔铺陈荒谬的当代西非传奇,何尝不是另一种以书写控诉现实、取得话语权的越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