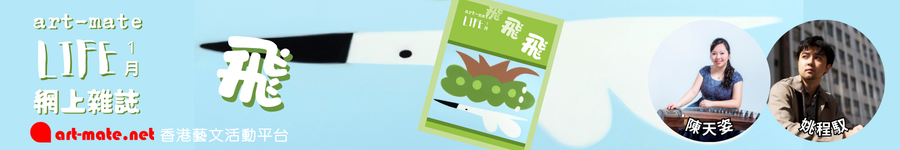陈老师对指挥技术的领悟之深,胜过任何一位我认识的国外教授,而他能以最简易传神的形容,一针见血地让人立刻了解事务的本质,记得第一堂课我就表达自己不善言辞,怕是不适合当指挥,他说:「指挥是靠手说话,不是靠嘴巴。」他也形容:「指挥乐团如同骑马跳栏杆,是马跳,不是你跳,但是你得使牠跳。」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时,我还是个对前途懵懂的台大心理系新鲜人,帮友人(陈老师的小提琴学生)伴奏一首莫札特奏鸣曲跟他上课。陈老师挺著硕大肚子,叼著烟,帮我翻谱,几天后听友人转述,说老师从我的弹琴中认为我可以当个指挥,就这样,开始了我与陈老师一段漫长的奇妙情缘,也因此渐渐在心中笃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没有乐团当工具的指挥课是很难进行的,尤其开始的几年,只有我与他一对一,有时对空比划,有时放录音带,有时他弹琴我指挥,有时仅仅空谈……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固定形式的「启发式」教育,对初学者来说,只能说是蜻蜓点水,上课时间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可以说,陈老师是以很自由及对待「同侪」的尊重态度教我(他拒绝收我学费),从不以「老师」的高姿态说话(他说:音乐是你的,我只是教你如何表达)。虽然上课方式很「另类」且即兴,但我喜欢这种被开导后先自我摸索、偶而再去被他以智慧话语点醒的感觉。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他如何在腼腆内向、从没真正在他面前比划过一段完整音乐的我身上,看出我的潜能、对我有如此的信任?他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个你没问题。」留下一脸狐疑的我。几年后,有了简文彬、刘孟捷、黄心芸的加入,上课变得具体也热闹多了,我也因大学音乐社团的实际演练经验,渐渐理解了很多陈老师提点的指挥原则。那阵子,我在示范乐队当兵,文彬是艺专学生,孟捷与心芸才小学毕业,正准备出国(他俩成天窝在陈老师家中练琴,做功课,游玩……),我们这横跨「三代」的学生,常常周末齐聚在他安和路地下室的琴室,轮流指挥、弹琴,总是乐声笑语不断,是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为学生清楚看到未来
也是那段期间,陈老师开始让我实际参与职业乐团的活动,从《茶花女》、《卡门》等歌剧制作,我在为歌手伴奏及参与整个过程中,累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当时的陈老师,从儿童合唱团、独唱者、导演排戏、到乐团排练样样自己来,偶而还负责歌唱家的接送,常常整天指挥到晚上手都抬不起来。他在排练场总是谈笑风生,神采飞扬,成为众人围绕的焦点。在多场他指挥的交响乐演出中,我担任乐团里钢琴或钢片琴弹奏(记忆最深的是:江文也《孔庙大成乐章》,我在台上弹钢片琴,刘孟捷弹钢琴)。他更不时会丢来一句,如:「你明天到示范乐队来,帮我指挥一下」这类的震撼弹。当时的我,却总是胆怯地临时爽约,一次都没出现,而他也都不生气。
陈老师好像能清楚看到未来;退伍前,如同一般台湾学子,我积极准备出国,他送我一句话:「学做菜要在厨房学,学指挥要在乐团里学。」并建议我留下来,当市交的助理指挥,他认为我经过一年历练后,去参加国际比赛,应可得奖。当时的我已获美国音乐学校的录取,哪听得下这句话,仍是执意要走,他就说:「你去学校看看,觉得不对随时欢迎回来。」我带著这句话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钢琴,并替指挥班学生弹琴,同时准备指挥班入学考试,在几个月内,我充分了解到陈老师那句话的深意;国外虽然各方面让我眼界大开,但以钢琴代替乐团的指挥班上课,如同隔靴搔痒,偶有的指挥乐团机会又是如此短暂,如同「大家轮流舔几口棒棒糖」(又是陈老师语)。因此,我在通过指挥班入学考试,得以于次年双主修钢琴与指挥之后,毅然给陈老师写了信,说我要回台湾。如是,在赴美一学年后,我这个没有音乐背景,在美国没有完成「学业」的无名人士,成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助理指挥。
一般的助理指挥,主要是负责在台下听音响,帮指挥、乐团修订谱子等工作。陈老师却让我一上任即「纯」指挥,一年内指了十几场的演出,包括大型制作及歌剧《弄臣》,以此经历,我顺利通过隔年法国贝桑松指挥比赛的书面资格审查,得以成为数十位被邀请的选手之一。经过三轮的竞争,也幸运地拿了第一奖,一切就如同他预测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