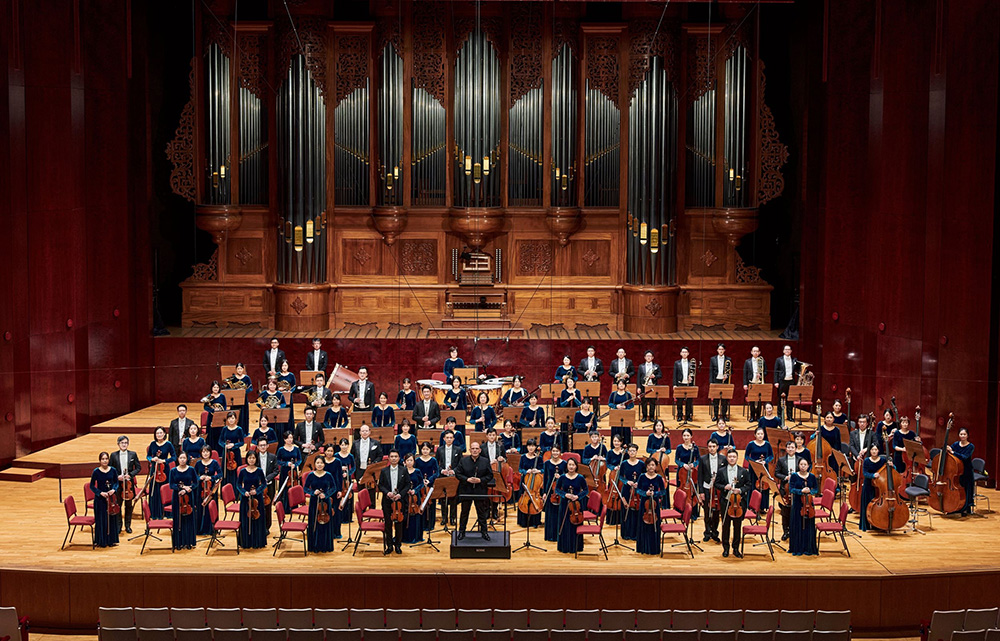2001年开始的流浪之歌音乐节(Migration Music Festival),至今已经进行了20年,自网路尚未如此普及的时代,「大大树音乐图像」借由国际的连结,将世界不同角落的乐音带入台湾。背后重要的推手——策展人钟适芳,除了流浪之歌音乐节的策划,自2015年起也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邀请下,策划「当代叙事影展」,持续以不同方式探索世界的流动状态。
流离的家族经验,开启广大的世界图像
「我是很有意识在做这些事,尤其是台湾尚未整理的离散故事。」谈起父亲与母亲的移动经验,钟适芳有满满的回忆:母亲因为跟著外婆到香港探亲,而再也回不去故乡,于是后来妈妈那边的亲戚都是香港人,粤语是童年的语言之一。父亲那端则有著更多的迁徙路径,1949年,因为海南岛离越南较近而往东南亚移动,未料抵达后却被当成战俘,好在有当地华人的协助被救出,之后在越南与寮国有很多世交。「我从小觉得寮国是世界中心,因为那边亲戚对小朋友很好。」1975年寮共执政,随著伯父伯母避难来台,家里餐桌上的食物有著更多的东南亚滋味。
移动,来自家族自身的生命经验。因此后来策划「当代叙事影展」也带著有这样的思维。对钟适芳而言,如果客家人要谈移动,就要有国际迁徙的视野与思考,因为那与我们有许多相似的状态。像是这几年她常到印尼邦加岛田野,当初在那里的客家人也如同奴工,只是华人谈历史不喜欢谈这样的事情。
迁徙:不只是流浪,更是融合与交流
在这样的生命经验之下,让钟适芳一开始就想要以「迁徙」为主题进行策展,「流浪之歌音乐节」先是有了英文名字Migration,后来在公部门的建议下才有了不同的中文意象。
「世上很多重要的风格,像是蓝调、爵士,都是经过迁徙而生。尤其是小的乐种,常经过个人移动,从一个圈子到一个圈子,或是一个女孩嫁到另一处,就将一首歌带过去、然后歌曲被传唱、或被改编,这些状态都是很吸引我的。」
在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音乐节、什么是「世界音乐」的台湾,钟适芳就开始在广播节目中介绍不同的乐种,也因此被欧洲广播联盟(EBU)列为观察员,有了许多资源,也于其中认识国际乐评和节目制作人。当他们听到钟适芳想办一个以「迁徙」为名的音乐节便十分支持,毕竟欧洲的历史包袱没办法如此直接地策展,因此第一届的流浪之歌音乐节便吸引很多欧洲乐评前来,捷克乐评也提供纪录片。人与人的连结和互信关系,在音乐节的起始便扎下的根脉,可以交谈的音乐伙伴,也是钟适芳策展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面向当代的人类学式策展
如同尼可拉斯・库克(NicholasCook)《音乐分析指南》所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词汇,其实无法包罗这么多东西,所以必须要借由其他形式长出。」对钟适芳而言,「从地缘或国际迁徙的地缘意识,其实是流动的,是同一个时代。」非音乐学系出身的她,因著自己的兴趣从文化角度认识与介绍音乐,以此确认音乐和历史文化的关系。
钟适芳强调因为流浪之歌音乐节不大,可容纳的东西不多,所以需要更精致去策展,对应主题,提供清楚的讯息。「除了音乐性,我必须去了解这音乐要说什么,或是音乐背后的意义。」因为对于乐人生命政治的重视,钟适芳谨慎地处理音乐人的故事,不过分渲染或消费,并有意识地延长音乐节的相聚与交流。「所以很多工作是要处理人,如何让一群人在很短的时间工作、相处,还要激发火花。」不只是进行一个一小时的演出,而是能让彼此了解、建立信任,标志出每一个独特的个人。
不只是策展行动,而是日常抵抗
2005年因为商业广告对手风琴音乐的刻板介绍,她策划了「手风琴,新定义」带入哥伦比亚、台湾与芬兰3种截然不同的手风琴乐音。2019年的「声音不见」,她邀请越南被打压监禁的社运歌手杜阮玫瑰(Mai Khoi),唱出越南人民的抗争生活,以及历史经验,尤其有一首讲台塑在越南造成污染的歌,更是钟适芳觉得是需要让台湾人知道的议题。
20年来,钟适芳都借由音乐渗透,打开听众的耳朵,同时带入创作背后的文化议题。这两年流浪之歌音乐节更与泰国连线,和多位艺术家与策展人合作,以「摩兰」(Molam)为主题,听见东北伊善地区(Isan)泰人的迁徙与劳动。他们的状态,也对应著台湾原住民的林班歌,就此拉出身分认同、移民与政治处境等轴线,以歌谣文本和劳动歌谣记事,来看当代迁徙的状态。并预计2022年于台北当代艺术馆进行共同策展,从音乐与当代艺术角度跨域对话。
左翼或是抗争,对钟适芳而言不是一种标志,而是每日的坚持。「批判对我来说是日常,批判和反抗都是日常,不一定要直接走到街上,只要发声、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就是在与什么对立了。」音乐节对她而言也是这样,所以她带入的每一个乐句,都是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