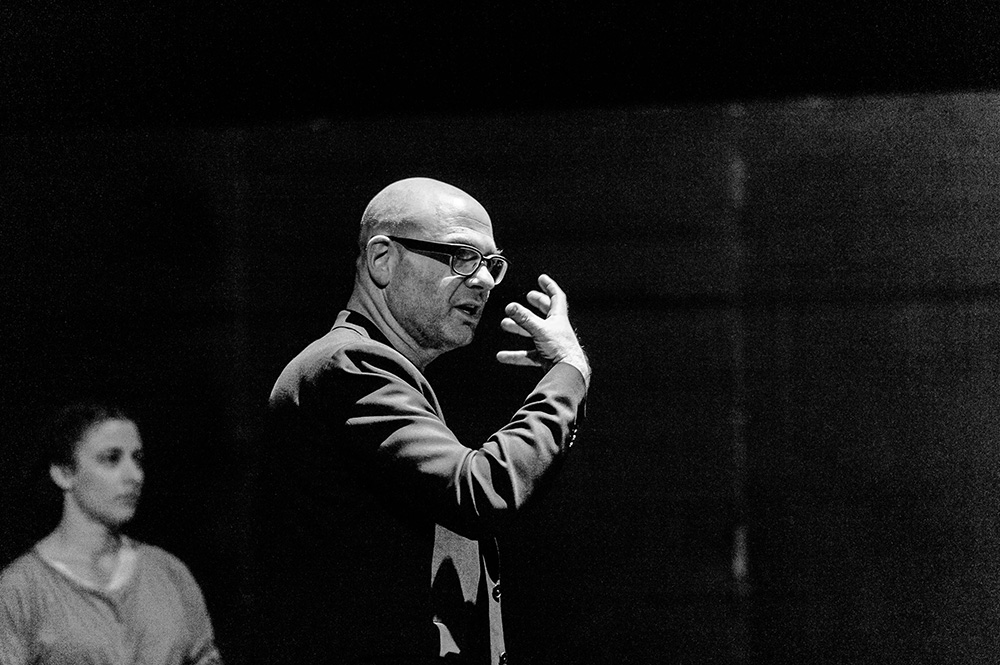2025/4/13 14:30
高雄 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
【2025卫武营国际音乐节】卫武营当代乐团:乐舞《美国新章》
2025/4/18 19:30
高雄 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表演厅
2025/4/20 14:30
高雄 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
奥古斯塔.瑞德.托马斯(Augusta Read Thomas)
- 生于1964年,就读西北大学音乐系时,从主修小号转至作曲。随后在檀格坞音乐中心和耶鲁大学,与著名英国作曲家Oliver Knussen及美国新浪漫主义音乐舵手Jacob Druckman学习。
- 1989年以当时最年轻女性之姿,获得古根汉奖学金资助开启作曲家事业。截至目前近40年的职业生涯,接受过全球各大乐团包括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巴黎管弦乐团等单位委托创作,并与布列兹、艾森巴赫等指挥巨擘合作。
- 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担任驻团作曲家最后一年完成的双协奏曲《星际颂歌》(Astral Canticle),入围2007年「普立兹音乐奖」决选(仅两部作品入选)。
- 2012年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该院创立于1780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研究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