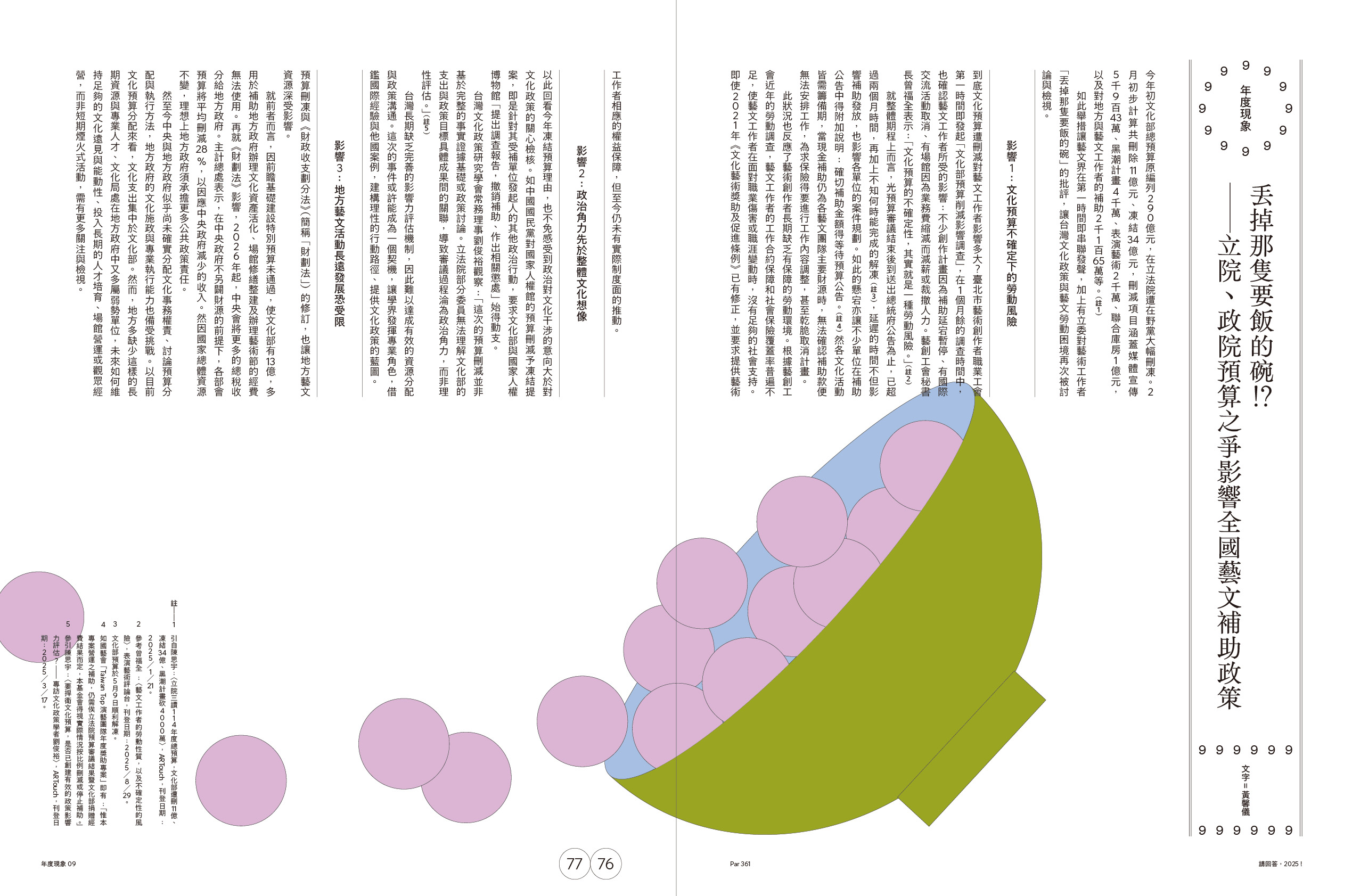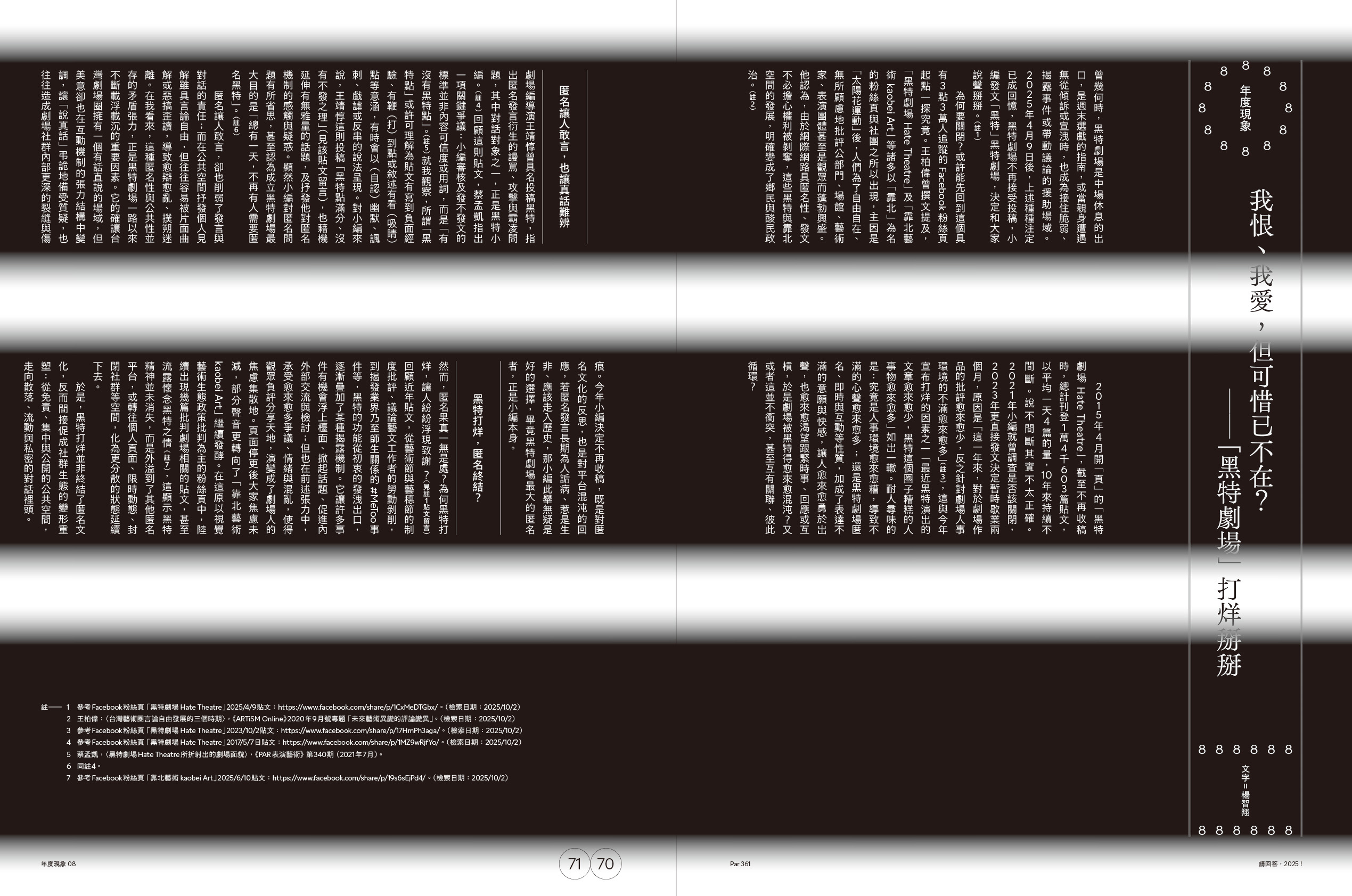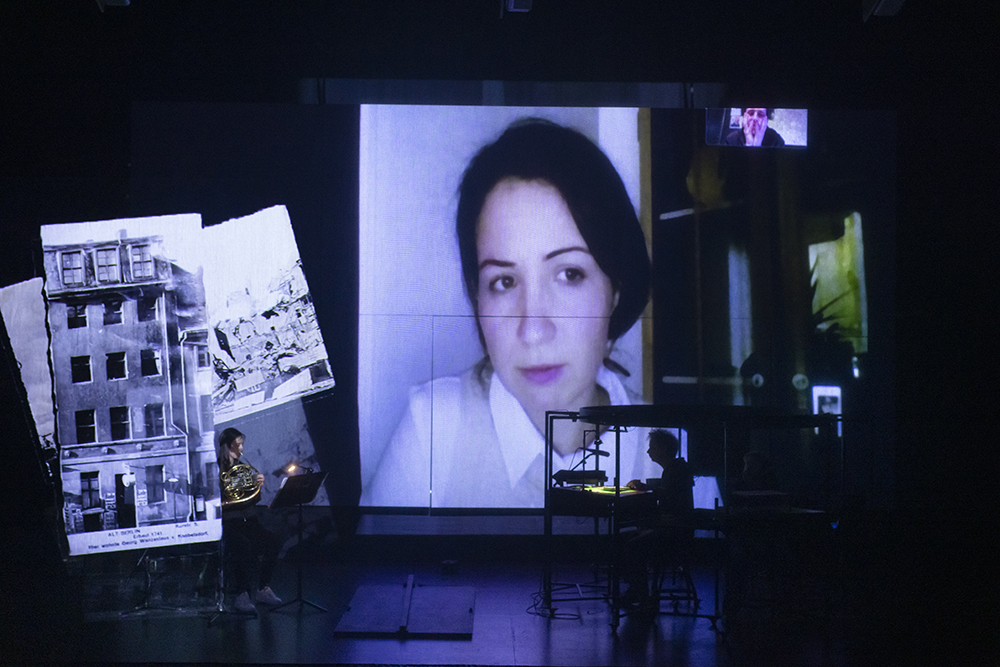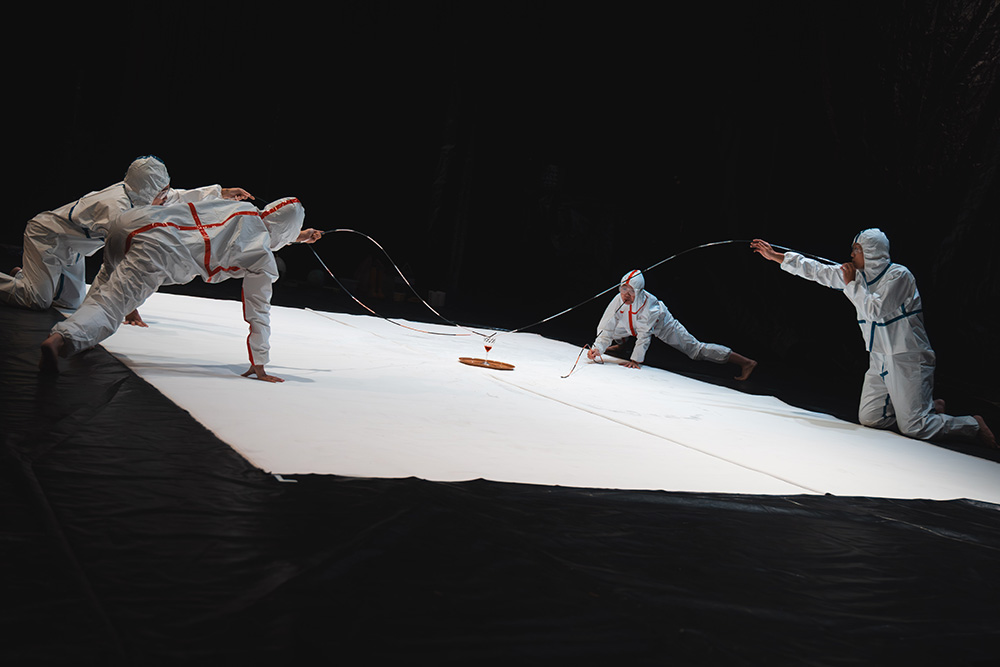秘鲁广场剧团(Teatro La Plaza)《嗨姆雷特》(Hamlet)的初始场景,是一段生产影片:一个婴儿正被从产道娩出,被接生、断脐、正式成为独立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并投入母亲的怀抱。而8名表演者们在这过程中陆续登上舞台,共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
对比被期待的新生儿,这些表演者实属于「不被期待」的唐氏症患者与智力障碍者。目前台湾平均每120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位是唐氏症宝宝,孕初期收到的各式产检资讯中,最被强调的即是唐氏症筛检。除了政府有补助的初期、第二期唐氏症筛检,也有非侵入式但较昂贵的NIPT(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检测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还有最为准确、却最为产妇犹豫孕中期是否要进行,须穿入肚腹的侵入式羊膜穿刺检查。「如果检测异常到底该怎么办?」在进行这些筛检时,皆能看到已成形、且有心脏跳动的胎儿,生与不生,在产前即为一个庞大且令人不安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