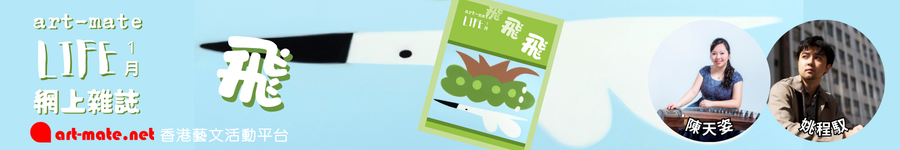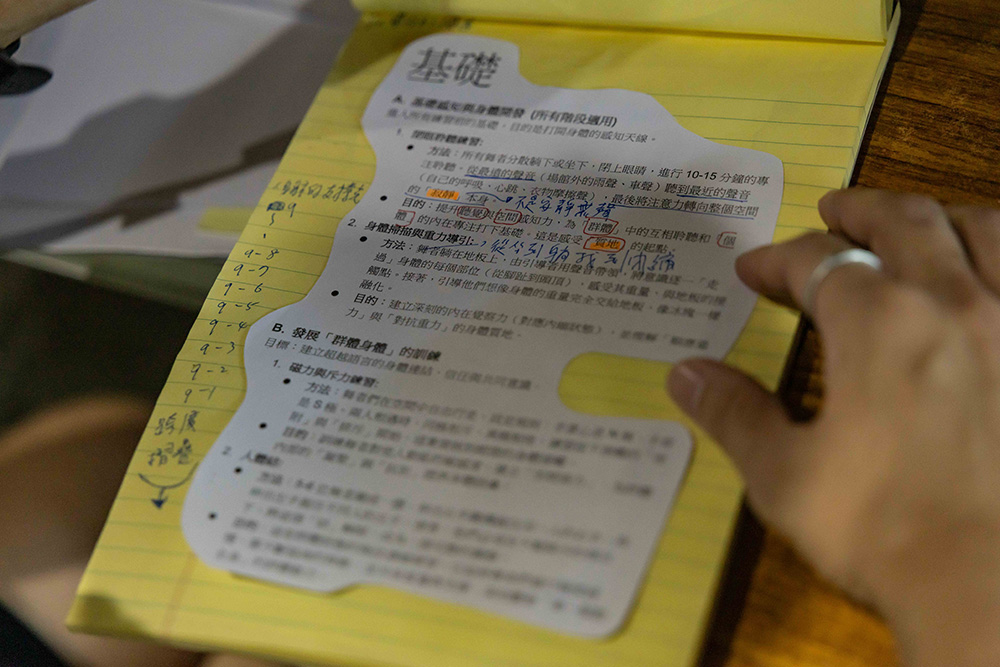8月底,TAI身体剧场位在花莲新城保安宫旁的铁皮工寮,一股腾腾热气盘桓不去,尽管稍一动作,汗水就会争先恐后喷发,舞者们仍一脸平静和煦,把身体往黑胶地板挪去。
Piya Talaliman李伟雄、Qaulai Tjivuljavus奥莱.吉芙菈芙斯、lrimilrimi Kupangasane巴鹏玮、lsing Suaiyung朱以新,以及新加入的舞者王秋茹,以各自的节奏和方法,在湿热的空气中暖身。不多时,负责今天排练指导的Piya往右下角落移动,以「脚谱」练习开始第一阶段的排练。
看著舞者身上晶亮的汗珠很快将他们背部浸润为一道光滑平面,黑胶地板上也流淌一道道水渍,我不禁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叹。编舞家瓦旦.督喜转过头来,安抚一般说道:「现在很热,可是只要一过4点就会开始有风吹进来,傍晚还会变冷呢!」尽管气候变迁让夏季一年长过一年,工寮里的他们依旧能鲜明察觉季节。
我的惊叹倒不是疼惜舞者溽热中大量劳动,以致汗水奔腾如瀑,而是一个念头豁然浮现:在这个追逐效率愈发高速的世界里,舞者恐怕愈来愈接近濒危的存在。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疯狂加速的世界中,身体能娴熟穿梭于现实和想像之境的舞者,或许会成为未来人类的关键物种——当多数人类被城市文明所驯化,惯于待在乾净明亮、无臭无味、清爽整洁的空调场所,且为了确保这种洁净无菌,身体与身体最好不断延长社交距离,确保廓清身心界线;与此同时,不畏湿黏肉身交缠,无惧彼此汗水交融,胆敢把身体抛进浓郁、稠密、潮湿、阴暗、搔痒、疼痛,勇于尝试多样的感官经验,因而有倍于常人的身体和环境适应性……这样的舞者,面对未来变数难测的地球,岂不比我们更多生存胜算?
100公里俱乐部历年里程
2018 花莲市—花莲富里
2019 花莲富里—台东土坂
2020 台东土坂部落—屏东来义部落
2021 屏东来义部落—台南吉贝耍部落
2022 台南吉贝耍部落—台中市
2023 台中市—桃园杨梅
2024 桃园杨梅—基隆市
2025 基隆市—宜兰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