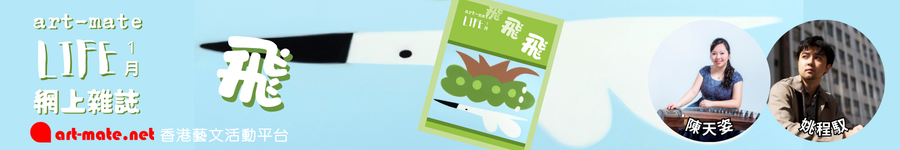舞蹈,乃由古代的祭拜儀式演化而來。在中國文字裡,「舞」、「巫」同源。即使在當代舞蹈中,儀式的本質也仍淸晰可見。儀式的基本作用之一是使人類互相了解,就此而言,它和藝術的基本功能「溝通」非常類似。檢視當代舞蹈大師的舞作,我們看到了屬於各個時代、文化地區,不同風格,不同表達方式的「新儀式」,肩負著洗滌人類心靈的重責大任。
舞蹈是一種最直接以人體肉身傳達訊息的藝術形式。經由舞蹈,人類把原始而本能的肉體運動──那些爲了求生、健康、避死、收穫……而施行的各種肉體運動抽象化了──抽除了實用的目的性,而留下純粹的動作本身,藉而來表現靈魂中純粹的慾望與情感。不需憑藉任何器具,人類發現自身就是一件樂器、一組機器、一部精密儀器可以用來歌詠敬拜、摹寫創化;而且這部舉世最優美精緻的儀器用來又是如此得心應手、自然流暢、貼合心意!因此,使用「身體」也就成了人類文明的濫觴;使用「身體」而成就了音樂、舞蹈、戲劇……這一切「藝術」的初始樣貌都是「儀式」。不待言,它實是無比端莊重要的人類文明要件,也更是一切藝術形式的根源始祖。
儀式是一種無言的交往方式
「儀式」是什麼意思呢?「儀式由傳統習慣發展而來,是一種普遍爲人們所接受的行爲方式,其基本作用是使人們之間互相理解。就此而言,儀式和語言有相同之處。」(註1)──也和藝術的主要基本功能──「溝通」有相同之處。「儀式是一種無言的交往方式。但人們往往強調它與神話的關係而忽略其本身的精神,因之就常從信仰系統中去尋求儀式的含義,以致造成過份強調信仰系統和神話的偏向。學者們近來轉向一種系統硏究──人體運動學,即無言的交往方式的硏究,將提供新的儀式分析方法。」(註2)因此,在此地對「儀式」一詞的理解,並不僅限於狹義的宗敎信仰或神話系統,而是較偏向社會意義的:它是一種集體潛意識的社群共同語言,也是一種集體意識的社會化行爲,包括有相通的意念及溝通與執行的實際行爲,是一種明確的符碼,同時即爲能指又爲所指。(註3)「指」的是什麼呢?一切可能爲人類精神魂魄所感知而相應的自然力和超自然力。這也就是藝術表現的範圍了。
舞蹈,作爲兼具時間性及空間性的表演藝術,它不似戲劇尙倚重語言的媒介,僅以空間動態的流變,配合聲音線條的穿織,造就在視覺與聽覺感官範圍內,更爲自由地對情感與理性開放的藝術形式。在舞蹈之中,濃情烈意、悲壯高亢、幽微婉轉、哀愁美麗……都更爲奔放寫意地直切人心;而以人體運動學之形式,將內容凝聚於舞台而射至觀衆群中,如此所造成的群體意識每夜在劇院舞台之上,提呈著屬於他們時代和他們自己的新儀式。
表演藝術的舞台景觀
舞台景觀指的是「舞台上一切可見因素的總組合」,佈景、衣飾、化妝造型,都屬於舞台美術;音樂、燈光變化則提點了情境氣氛,兼具敍事性;人體動作線條與舞蹈群體間的關係結構,則是舞蹈演出的主菜,這些視聽及感覺要素構成了全部的「舞台景觀」。人類原有的舞蹈動作經驗,會隨著劇情或作品風格的需要而變形,在千百年的創作開發過程中人們又認識到舞蹈本身就是語言,可以不須淪爲描述劇情的手段,而所有的佈景、衣飾、化妝造型、燈光設計,都是根據舞蹈作品本身的風格來設計,根據劇情、舞蹈語彙、意念與風格而創作的(註4)。西元一八四九年的《吉賽兒》舞劇景觀是非常自然寫實的林間景致,吉賽兒在此徘徊獨思。這個時代,歐陸開啓了浪漫主義。一九四七年,由史特拉汶斯基作曲,喬治.巴蘭欽編舞,諾古其服裝造型設計的舞劇《奧菲亞斯》在現代芭蕾的重鎭──紐約,由市立芭蕾舞團首演。我們看見造型簡捷線條優美的道具(奧菲亞斯的豎琴和黑天使的面具),其流線的造型反應了二次大戰後,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間隙之中,人類生活如何受到世界經濟生活方式的影響與主宰。這些在表演藝術的儀式之中均反映無遺,那使人體發出金屬光澤的燈光照明,那使人聯想到家用器具的造型美感,那自古不變的原始激情,都在肉體運動伸張之線條中展放。
回歸古典的渴望
一九六〇年代,在經歷戰爭和動亂的殘害之後,和平、回歸自然的聲音漸漸高揚。此時在共產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波修瓦劇院芭蕾舞團演出的《天鵝湖》中,也同樣有可供玩味的訊息。這堂舞台景觀和一八四九年的《吉賽兒》比起來,少了後者那份浪漫抒情的淸新柔美之氣,倒多了些肅殺的、恣情揮灑的奔放。
而爲什麼直到西元一九九三年的今天,我們仍引頸期待《睡美人》古典芭蕾舞劇的演出?因爲古典的穩定、均衡、頑強不破的美感,恰可以塡補安慰我們生活中的忙碌、破碎、疲憊、缺乏眞正的閒逸與隱私……種種現代人的後現代的痛苦。我們渴望回到田園與自然,回到母親的安詳懷抱,我們懷舊,充滿鄕愁。而遺憾的是:我們回首尋覓的大地之母,在我們的長久開發之後,溫柔氣息早已消失,看看臭氣層破處瀝下的陽光,其成份是多麼地肅殺啊!這正是現代生活著的人類,舉目所見或閉目不敢見的世界面貌。幸而自一九六〇年至今,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活在這一點肅殺之氣的持續性啓發和相應的反省成長之中。舞蹈,做爲表演藝術的大宗之一,也必然地繼續在藝術形式裏記錄人類眞象。
葛蘭姆的祭儀風格
一九五五年的瑪莎葛蘭姆作品Seraplic Dia-logue,以細的鑄鐵銲接成的舞台造像,一具三角形與圓形的大圖騰,成了視覺的焦點。大師作品一向充滿原始祭儀般強烈凝聚的張力,此齣也不例外;瑪莎是最爲了解舞蹈的根源,力量、意義的強度與深度,也是將強大感情力量,靈魂深處的眞切呼求貫注於舞台的現代舞蹈宗師。在另一齣一九五八年作品Clytemnestra中,可見另一印證。克蕾婷妮特拉是希臘悲劇《奧端斯提亞三部曲》的肇始人物,她在丈夫阿格曼儂出征特洛伊後,變節改嫁給丈夫的弟弟,而在阿格曼儂凱歸時將之謀殺,導致親子奧瑞斯特斯流亡異鄕,多年後方潛回國與姐姐共謀殺母殺叔,爲父報仇──在劇照中可以看見對母性的崇拜,藉著三人相疊積的禱求呼吿,以及傲踞寳座的女體聖潔的姿態表達出來。
「花原」上的碧娜.鮑許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以後舞蹈與劇場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在碧娜.鮑許正式將舞蹈劇場爲自己的創作命名以後,舞蹈敍事體的規模也就更爲擴大。一九七六年的作品The Seven Deadly Sins,有如街頭的示威抗議,振臂高呼口號──只不過舞蹈家們舉腿代臂。至此舞蹈的形式更爲開放,其內容也可納入更多社會性的事物。一九八二年作品Carnation,碧娜.鮑許最令人驚異處常是一大整片爲主題所充滿的實物景觀:滿台滿地的花朶,上面擺放一列椅子,人物與事件輪番自地上開放延展,似是如花原般遠擴而去,又如垂死花朶般肆放生命凋零之際的狂烈情緒。
模斯.康寧漢的「場」
另外,如模斯.康寧漢的作品,也同樣有著很強的「場」的張力:場面上的一切事物與流動,雖正如其名作Happenings般自由寫意、不按牌理而可隨意重組拼合,但是那整個「場」卻隱然直見生活眞相:邂逅、遇合、悲傷、失落、相愛、自閉、相處……一再自眼前流過不止息。那是一種令我們這些同樣生活在現代世界裡的觀者們泫然欲泣的無奈。値得安慰的是,我們穿越觀衆席與舞台所望見的舞蹈語言的純粹──那透明獨立的美感,撫平了我們心上的酸痛。
肢體燦放成舞蹈
最後看看崔拉莎普舞團呈現的優美動態:經由人身體的展放,燦放成舞蹈。人們彼此進行著無言的交往,而屬於儀式之體質的「心領神會」、「同神同感」性,使人們不僅欣賞著表演藝術的美,也因一同經歷了一場儀式的洗禮,而與疏隔已久的「他人」產生了交流與共鳴,不再孤寂。
註1:大不列顚百科全書,第十七冊,65頁,「儀式」條。中文版1987年新編,台北市丹靑圖書有限公司。
註2:同註1,66頁。
註3:「能指」及「所指」均爲西方當今流行的學科「符號學」的基本語之一。能指(signifiant)是象形地通過相似性來代表所指(signifié)的一種符號,而所指則爲符號的對象、價値與意義。
註4:參考「舞劇與古典舞蹈」,苣原英了著、李哲洋譯,台北全音樂譜出版社,1982年版。
註5:關於多國化資本主義、或稱二次大戰後晚期資本主義之釋義,可參見「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詹明信敎授講座、唐小兵譯,台北市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版),該書之引論至第三章。
文字|石依華 劇場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