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娜.鮑許
-
 柏林
柏林面對文化預算「深淵」 2025戲劇盛會精采落幕
今年5月中旬,第62屆柏林戲劇盛會(Theatertreffen)順利落幕。作為一年一度德語區最具指標意義的盛事,柏林藝術節的總監馬蒂亞斯.皮斯(Matthias Pees)以「歡迎來到深淵」作為開幕典禮的歡迎致詞,不只意指開幕演出《深閨大宅》(Bernarda Albas Haus)劇情陰暗壓抑,也同時影射當下文化預算被大幅刪減的慘況。(編按)
-
 舞蹈
舞蹈我們不要跳八股!但然後呢……
「科班生」是指受正統教育出身的專業人士;在黃懷德編作的《科班生之舞》,指的當然是舞蹈專才,更在這個作品中鎖定「舞者」的養成,反思廣納東西方舞蹈風格技巧的訓練對「舞者」產生的影響。 將近70分鐘的《科班生之舞》明顯切分為上、下半場。前半約35分鐘,由黃懷德獨舞;後半則以《春之祭》為樂,由5位舞者演出。僅管上、下半場,不管在編制或音樂的選取都大相徑庭,卻口徑一致突顯:「多元動作風格訓練」如何在「身體容器」造成動作美學的衝突。 在上半場,黃懷德用非常簡單的基本動作操演,明白展示芭蕾和戲曲身段兩種東西動作訓練的美學差異: 他站在舞台中心,將舞台分為左右兩半;同時,他也將身體切為兩半,一半展跳是西方的芭蕾基本動作、另一半展示東方戲曲元素抽取出來的基本動作。同樣是往身側旁舉的手臂:手心微向前、向下45度、大拇指緊貼中指,是「芭蕾」的手;但僅僅是提肘向後翻轉90度、反扣手腕、打開虎口,就成了「戲曲身段」的手。
-
 回想與回響 Echo
回想與回響 Echo《春之祭》 舞蹈的教育學
跳舞至死,斯特拉溫斯基(Igor Stravinsky)構思《春之祭》的唯一念頭。但以何種方式?最不舞蹈的方式,以芭蕾舞者最不芭蕾的一切身體可能性。於是音樂調性、節拍、節奏與重音皆不和諧且不符期待,舞者怪異顫動、跺腳、衝刺、失衡與顛狂,肢體無以名狀地開闔擺盪,在世紀初巴黎的展演中,音樂與舞蹈同時面向現代主義的最初洗禮,一場絕無僅有的盛宴,在最激突怪異的音樂中有最激突怪異的舞蹈,遠超越時代的作品引爆現場的尖銳衝突,被選為祭品的舞者恐懼、悲淒、奔突、纏綿眷戀,狂舞而死。由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編舞、斯特拉溫斯基作曲的《春之祭》首演(1913)像是一聲高亢的叫喊,撞開現代藝術的大門。 當年人們說:很遺憾看到像斯特拉溫斯基先生這樣的藝術家捲入這場令人不安的冒險中。60餘年後,烏帕塔舞蹈劇場的碧娜.鮑許(Pina Bausch)重啟這場冒險,以她的舞蹈語彙重編《春之祭》(1975)。舞者的腳被舞台上厚厚一層泥土揪住,往空中騰飛的天性從一開始就被抹除,在褐色的軟土層上舞者撲騰翻滾,滿身髒污,肢體的怪異收放與朝四方劇烈抖動的身體,彈跳、暴衝並急速定住,舞者一出場便被逼往失控的臨界狀態,以身體的動態在泥土上留下一痕痕印記,致敬60年前的兩位前輩毫無疑問。
-
 舞蹈
舞蹈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隘口
那一年我到了愛爾蘭西端的莫赫懸崖(Cliffs of Moher)。 沿著高矗崖邊的山徑步行,起初猶不知僅隔幾步之遙,臨海即是歐洲最高的懸崖,最高點高出大西洋的海平面214公尺。等到站立於可以俯瞰壯闊波瀾大西洋的崖邊,才會因其高度有點暈眩,腳底發麻。一時霧散雲開,海鳥遨翔,那些崎嶇風蝕的崖石,才從海平面向上層層疊疊展露其歷史皺摺下的面貌,海濤風湧拍盡,白色浪花飄散。 麥克.基根-多藍(Michael Keegan-Dolan)與舞蹈之家(Teaċ Daṁsa)所創作的《界》(MM),原文為凱爾特語(Gaelic),最常見的用法是指山路隘口或超越大型地理障礙的最簡單途徑(註1),既可援引為跨越「過去」的罣礙,指向「未來」可行的路徑,相對地,時間在此難以簡單線性地去區分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即是未來,而未來亦可能是回歸原初,循環迴旋,而人性的愛慾情仇仍然依舊輪迴不已。
-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追蹤 Follow-ups在教堂中起舞 與城市空間對話
德國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自2009年失去了重要領袖編舞家碧娜.鮑許以來,一直在尋求新的方向。去年9月,法國藝術家波赫士.夏瑪茲(Boris Charmatz)接任為該舞團第5位藝術總監,標誌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夏瑪茲是法國1990年代「新舞蹈」美學的繼承者,他曾帶領法國雷恩國家舞蹈中心(Centre chorgraphique national de Rennes),將其轉變為「舞蹈博物館」(Muse de laDanse),將舞蹈視為參與政治議題的社會雕塑,他挑戰了現代「擴延編舞」(expanded choreography)實踐,將作品於非傳統劇場場地呈現,並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和紐約現代美術館等地創作,對當代藝術的編舞轉向具有關鍵影響。 2022年,夏瑪茲接手了烏帕塔舞蹈劇場,並繼續推進他在2019年啟動的「陣地」(Terrain)計畫這個計畫是為烏帕塔舞蹈劇場開展法國和德國合作的項目,旨在探索「人體建築」(human architecture project)的概念,夏瑪茲試圖通過身體運動來建立可見性和彈性的建築結構,創造一個「編舞綠色空間」(choreographic green space),他希望能透過以動作和姿態為基礎的機構,來回應現代城市在氣候、城市規劃和社會設計等多方面的挑戰。 儘管風格迥異,但夏瑪茲和鮑許都看重舞者,認為舞者是在舞台上熱情地表現自己,而不僅僅是編舞的工具,他們也都注重打破第四堵牆,建立觀眾和表演者的關係。今年9月,夏瑪茲在烏帕塔近郊粗獷主義建築(Brutalist architecture)的Mariendom Neviges教堂,首演了與舞團合作的新作品《自由大教堂》(Libert Cathdrale),此作也陸續至里昂國際舞蹈雙年展等地巡迴演出。藉著到烏帕塔參訪的機會,筆者專訪了夏瑪茲,請他分享與烏帕塔舞蹈劇場合作的種種,及這次《自由大教堂》與其「陣地」計畫的連結。 Q:可否談談與舞團之間合作的關係,與如何協商碧娜.鮑許留下來的舞蹈遺產? 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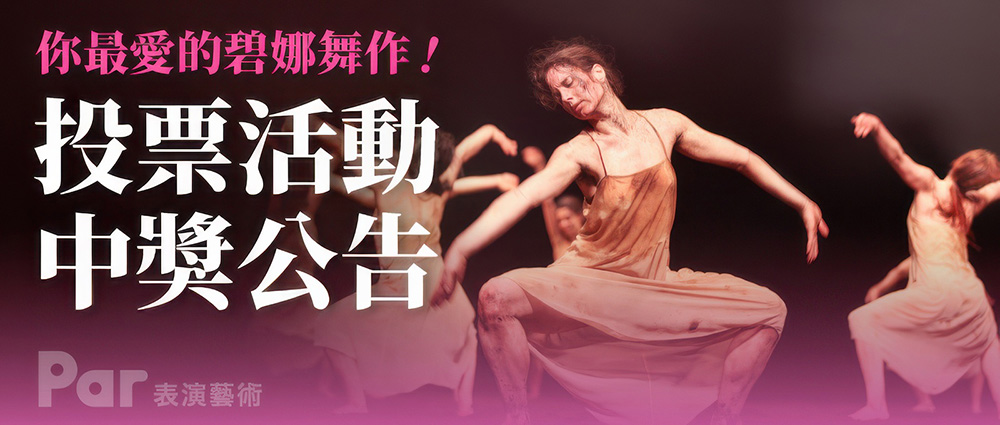
「票選你最愛的碧娜舞作!」投票活動中獎公告
「票選你最愛的碧娜舞作!」投票活動已於2025年12月31日截止,總票數為1923票,其中《春之祭》以439票(23%)獲得最高票。此外,感謝《PAR表演藝術》會員熱情參與,中獎名單已經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抽出11位幸運得主,並公布如下,《PAR表演藝術》將於近日以EMAIL寄出中獎通知專函,請中獎者注意收件匣,並請於2026年2月28日前協助回覆。
-

2026TIFA九國藝術家齊聚 邀觀眾重新發現劇場能量
2026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邁入第18屆,今日公布16檔精采節目,邀請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葡萄牙、丹麥、加泰隆尼亞與台灣等九國頂尖藝術創作者,推出共106場演出,於2026年3月8日至5月30日期間登場。節目將於2025年12月1日開放兩廳院會員預購,12月8日全面啟售。
-

碧娜.鮑許《春之祭》 北藝大新世代舞者傳承與再現
碧娜.鮑許的《春之祭》之前大多由歐洲主流芭蕾舞團演出,而繼碧娜.鮑許母校福克旺藝術大學(Folkwa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之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成為全球第一所重演《春之祭》的學院,透過年輕世代舞者的參與,展現經典重現的藝術精神,是一次極具意義的重製演出。
-
 焦點專題 Focus
焦點專題 Focus甩脫不掉的連環夢
考上戲劇研究所那年,我做了一個夢。漆黑的長夜,我和一群劇場演員狹路相逢,他們熱烈邀我加入一場宴會。宴會中人人歡聚圍坐,高談闊論,酣飲或者相互擁抱。身為新人,我感到羞赧而不知所措,直到當中有人把一根菸遞向我。我搖頭又懊悔,要過菸,裝作漫不經心地深吸一口,同時低頭看見自己身穿一襲黑色皮夾克。 那一剎我忽然明白自己身在夢中,要是菸熄滅了,或我脫下皮夾克,這一切就會隱沒,我將醒在一個自己不是劇場人的世界。我試著把這個發現告訴其他人,然而人人似笑非笑,但看我決定怎麼做。 一股強烈的睡意襲來,我費盡力氣向他們解釋,就算菸沒熄、我沒脫掉夾克,要是我在這裡睡去,就會醒在另一個世界。但他們仍一臉笑意跟著我身上的黑皮衣一塊如同日落般漸漸隱沒。躺在床上,我花了一番力氣確認自己醒在一個我考上戲劇研究所的世界。感謝老天,我不會成為「不是劇場人」。 * 跟著這夢境滑入我腦海的,是江紅的夢。這個《如夢之夢》的角色,是我還未決定考研究所前,在當時還叫國立藝術學院的戲劇廳看的劇中人。江紅在遇見五號病人那天早晨做了一個煎蛋的無間夢中夢,她問自己:要是煎第五顆蛋時就確認自己清醒,那麼她會不會擁有一個不同的人生? 要是穿皮衣的我沒睡著,或是在夢中脫掉了我的皮衣,那麼現在的我會是一個怎樣的劇場人?我會滿足於當個穿梭後台的黑衣人,還是不顧一切地埋首一部接著一部劇本寫?會留在當年懷抱鐵粉心情加入的劇團繼續當個行政經理,還是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執導幾個戲?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成為台上的表演者,這倒是不管我在夢裡抽幾根菸或脫幾件衣服都能夠確定的事情。 我會更快決定離開最後一個劇場正職工作《PAR表演藝術》雜誌編輯投入乍看毫不相干的樹與植物文化書寫嗎?並且一邊依然和劇場保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邊對「為什麼從表演藝術跨到毫不相干的草木世界」一類的提問暗翻白眼不耐煩。 * 我不知道如何向人們解釋:從來沒有不相干。就算我雙腿一劈跨入的是科技界、餐飲界還是新農業,它們都不可能是和表演藝術毫不相干的世界。表演藝術已撲天蓋地滲透我。 身為一個自由文字工作者,當我以編輯的角色構思一本書的編排時,每位費心找來的撰稿人在我眼中好比是碧娜.
-
A Bigger Picture
戲劇,是為了回憶,抑或開拓?
看碧娜搜索結集的創作素材全是回憶,集體個人,反映文化社會,反映未來現在,所以看她的戲,是making sense of (one)self in this big big world,每個人那麼渺小,但又唯一,每個人都只得一個自己,卻與數不盡的人同悲同喜。 這是一個每個人一生都適用的問號,用來了解最基本的一個字,人。
-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
總編輯的話 Editorial閱讀碧娜,重新想像她的舞蹈現場
碧娜.鮑許持續對著舞者、對著我們提問,用她的排練清單、用她的經典舞作,這些疑問最終構成了作品、化成了無數令人驚豔、讚嘆,備受震撼又真切迷人的畫面,也讓觀舞者思考更多的問題,激發了無限的想像與可能。在本期雜誌中我們試圖重新閱讀碧娜,在她的編與舞之間,抽絲剝繭,從舞台的自然與奇觀、數不盡的男女關係和兩性糾葛,及其巧妙運用的曲目樂音等三種視角,看它們如何為作品建構出獨特且不凡的魅力。 用空心磚砌成的高牆、縫隙間淌流出的火山熔岩、鋪滿舞台的泥炭紅土,或是位於舞台上的深池、小型游泳池,當中甚至還有一隻河馬碧娜的舞台,包含了許多自然的成分,更是人工打造的奇觀,各式各樣的土石、令舞者痛苦受傷的水,還有,台灣觀眾曾有幸在廿年前見證了、那滿台的康乃馨。 本月碧娜.鮑許烏帕塔舞蹈劇場,受國家兩廳院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之邀,再次登台,我們也邀請了曾經目睹《康乃馨》一作,並受其影響深遠、印象深刻的三位創作者作家成英姝、建築師阮慶岳與香港劇場編導鄧樹榮,分享當年欣賞《康乃馨》後所感受的衝擊,或是分享屬於《康乃馨》的華麗與哀傷。而我們也邀請到插畫家朱疋,以碧娜.鮑許的舞作發想,為此專題獨家繪製多幅畫作,重新再現她的舞蹈現場。碧娜的舞蹈,激發了無限創作者的靈感,且讓我們在看罷《康乃馨》後,再隨著插畫家的筆,一同跳進舞的想像。 人稱劇場金童的法國導演托馬.喬利,四月也將帶著全長約四小時的莎士比亞名作《理查三世》來訪,如果您曾納悶,為什麼好像時常看見這個劇本在台灣、在世界各地上演呢?本刊也特別蒐羅了各國導演的近期《理查三世》作品:包括英國導演魯伯特.古爾德、德國導演歐斯特麥耶,更訪問了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王曉鷹與這次來台的導演托馬.喬利,談談這位莎翁筆下近年來復排次數眾多的劇碼,在他們心目中,又有什麼讓人又愛又恨的邪惡魅力?讓我們隨著導演的視角切入,看看這位英國歷史中,從地底下到舞台上,被人各自解讀的君王。
-
特別企畫 Feature
閱讀碧娜的幾種方式
「你對愛的感覺如何?」 「你想對一個人溫柔的時候,你會怎麼做?」 「當你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你在聖誕節時吃什麼?」 「你的法則是什麼?」 「你們覺得以失去而感到可惜,或遺憾那些不再存在的事物是什麼?」 「你害怕著什麼?」 在碧娜.鮑許的排練清單上,還有成千上萬個問題。這位總是從問題出發、徹底改變當代舞蹈風景的編舞家,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每部新作品都不從動作啟動,而從問題開始。有些是直接的問號,更多是拐彎抹角地提問,她問自己,問她的舞者,或許,更多是問前來劇場的人們: 「你為什麼來?你在問自己什麼問題?」 本期嘗試以三重視點男女、舞台、音樂觀看這位握有問題的鑰匙的編舞家如何通往我們的靈魂,在她離去這麼久以後,仍不斷地以每個不會死去的作品,輕輕地附在我們耳邊,悄聲說:問自己這些問題吧。去經驗、去發現,你可能感覺混亂,可能找不到答案,都沒有關係。
-
特別企畫 Feature 視點之一:男人與女人
舞不盡的世間男女 說不完的愛恨慾怨
舞台上,她╱他們互相挑逗、擺佈、叫囂,或許溫柔款款,卻更似暴力相向這是碧娜.鮑許的舞台,男男女女,愛恨嗔痴,各式各樣的糾葛,盡現舞作之中。透過九齣作品,讓我們看見碧娜.鮑許如何看待男女關係,無窮無盡的人間風景
-
特別企畫 Feature 視點之一:男人與女人
舞不盡的世間男女 說不完的愛恨慾怨
舞台上,她╱他們互相挑逗、擺佈、叫囂,或許溫柔款款,卻更似暴力相向這是碧娜.鮑許的舞台,男男女女,愛恨嗔痴,各式各樣的糾葛,盡現舞作之中。透過九齣作品,讓我們看見碧娜.鮑許如何看待男女關係,無窮無盡的人間風景
-
特別企畫 Feature 視點之一:男人與女人
舞不盡的世間男女 說不完的愛恨慾怨
舞台上,她╱他們互相挑逗、擺佈、叫囂,或許溫柔款款,卻更似暴力相向這是碧娜.鮑許的舞台,男男女女,愛恨嗔痴,各式各樣的糾葛,盡現舞作之中。透過九齣作品,讓我們看見碧娜.鮑許如何看待男女關係,無窮無盡的人間風景
-
特別企畫 Feature
她與他,這樣與碧娜共舞
她與他,她們與他們,溫柔地、激情地、暴烈地,或相互擁抱,或彼此玩弄,或行禮如儀,或劍拔弩張在碧娜的舞台上,世間情事如是繽紛流轉
-
特別企畫 Feature 視點之二:舞台上的自然與奇觀
跳上崎嶇濕漉舞台 舞出真實痛苦人生
碧娜.鮑許的舞台,往往讓觀眾一見難忘,卻也讓舞者痛苦萬分,如同現實的世界,有土石瓦礫,有斑斕植物,還有到處流淌的水這些艱困的舞台逼使舞者思考「為何而跳」,他們的妝花了、晚禮服濕透了,離開舒適圈,冒著受傷的危險,重新理解身體的痛苦以及心靈對自由的渴望。
-
特別企畫 Feature 視點之三:傳奇音樂家
巧用奇音妙律 與舞同行畫龍點睛
在重量級德國電影導演文.溫德斯的記憶中,不朽的碧娜往往有音樂相伴,而音樂的巧妙運用,也正是碧娜.鮑許舞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重點。透過五位傳奇音樂家之作在碧娜舞作中的現身,讓我們認識碧娜.鮑許的巧心慧思
-
特別企畫 Feature
未竟的承諾
《康乃馨》何能帶來那樣大的衝擊?我的人生後來每遇消極茫然,便自問誰是「我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一個人」,答案總是碧娜.鮑許。她那份強大的人類里程碑式的創造力我望塵莫及,但我認同那種「全天下人都那樣想然而我不」,是需要一個大而豐富的內核作為對抗的力量,這個內核仰賴紮實的美學養成,不滿足於經驗的貧瘠。
-
特別企畫 Feature
哀傷就是我的本質
死亡必然華麗,否則生存的艱辛,要如何去訴說。優雅必須被陌生者踐踏,否則我們如何懂得緬懷、以及哀悼與懊悔?每一個流星般隕落的零碎事件,都是浩瀚天體遣來的神秘訊息,也是引領我們繼續黑暗前行的指引明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