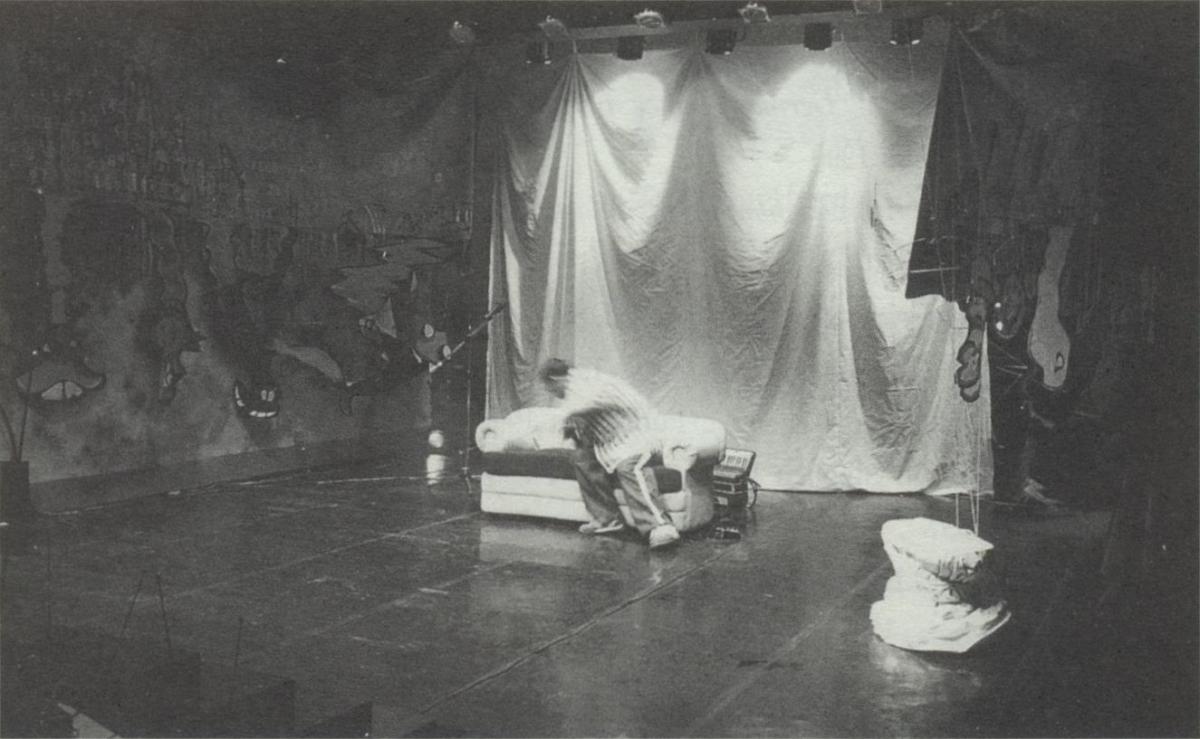在一九九九年末一片迎新送舊聲中,台北小劇場聯盟舉辦的港台劇評人交流座談會悄悄展開,會中沒有過多的爭論,留下的是對過去的回顧、展望與自身處境的擺盪,呈現著世紀交替間港、台劇評人的不可承受之「輕」。
閻鴻亞(以下簡稱閻):在台灣,因爲演出的時間很短,我們看到劇評時通常演出已經結束,所以市場導向的機制不大存在,而是一種馬後炮式的,爲這個作品蓋棺定論。這樣常常引發讀者與創作者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評論並不是一個橋樑,而是變成一個挑釁者,在台灣這也是很刺激的現象,我常常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對這樣的現象,我想兩位台灣的劇評人也非常了解,因爲他們本身旣創作,也寫評論,對這樣的現象應該有很多想法,我們先請香港朋友來說一下香港劇評的現象,再來進行交流座談的部分。
香港劇場「後八九」與「後九七」時期
梁文道(以下簡稱梁):我先講一講香港劇場生態,香港不像台灣這樣分爲大劇場與小劇場,通常我們用另類劇場這個名詞來談,因爲另類的包容性比較大,在香港有些另類劇場一直都在大劇院裡做作品,從來沒用過小劇場。那這些年香港的另類劇場情況可以說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身分以及定位,這也許跟整個藝術政策與藝術發展局成立之後的生態有關,不能否認,在跟政府拿錢的機制中,不只是營運組織的改變會發生,甚至對劇團作品也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因爲每個人都想建立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尋找自己的定位,於是每個人都是另類。所以大家的作品都不一樣,關心的問題也不一樣,不像台灣的小劇場運動曾經有過一些共同的議題,例如本土化。這樣的情況大概近十年開始有些改變,從座標上來說,有兩個重要的時間,一個是後八九,一個是後九七。
八九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九七年是香港回歸。這之間開始浮現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香港的文化身分的問題,開始成爲一個趨勢。因爲在政治制度的巨大轉變中,藝術家一時無法處理這些巨大的改變,所以從文化身分出發是必然的趨勢,在九七年無論是文學與劇場,我個人認爲不錯的作品常常是建構一個虛幻與眞實共存的香港,將這個過分眞實到無法表達的香港的轉變,做成虛幻的。
那現在過了九七,我們稱之爲後九七階段,有點回到之前所說的,「各做各」的階段。比較不同的,也是最値得注意的是年輕一代創作者的出頭,他們沒有比較重的包袱壓在背後,所以一九九九年的另類劇場現象,我可以挑一些新的創作者的特色來說明;這些創作者都很年輕,他們可能以前演出過進念二十面體的戲、林奕華的戲或陳炳釗的戲,現在自己開始組團做自己的作品,香港藝術中心從去年開始一個「Wave次世代」劇場的活動,也給了這些人出頭的機會,提供了這個現象被注意的焦點。我把這些作品的定位稱之爲「後林奕華」、「後進念」,「後」的意思是有延續,也有超越與不同,這些年輕創作者從以前的經驗中學習到,比如說林奕華看問題的方法,將這個方法用在林奕華不會討論的問題上面。
其中我很欣賞的一個劇團叫做「有耳非文虫仔竇」是去年Wave的作品之一,去年也來過台灣,他們做作品的方法輕鬆、快樂、沒有負擔,作品沒有嚴肅的主題,他們探討的主題是「可愛」,跟以前美學推崇的悲壯崇高完全不同。我們常常說這個很可愛,Hello Kitty很可愛,可愛是一個很重要的商品與價値,那劇場裡有沒有一種可愛的表現方式?或是探討可愛的可能呢?另外一個團體叫做「冶丁」,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作品叫做《荷爾安妮二之文藝復興》,他們之前跟進念、林奕華做過一些戲。我們知道進念跟林奕華都是知識分子,作品主題卻常常是流行文化;我跟「冶丁」開玩笑說他們基本上是不認識字的,但他們的主題卻是最知識分子的大題目,第一個戲談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形象,第二個戲談文藝復興,眞的談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喔!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就是眞的沒有負擔,才能這樣自由地尋找各種主題進行新一代的劇場創作。
小西:剛剛梁文道談到新一代創作者出頭的現象,劇評也是一樣,香港近兩年出現一些新的劇評家,就是香港演藝評家協會與香港大學合作開課培訓出來的,協會也有經紀人的角色,會在報紙跟劇評人之間做一個橋樑,替劇評家尋找媒體發表作品。這帶來一些劇評家角色上的改變,像我以前剛出來寫劇評時,就是看戲給文章,角色很單純,但是從協會開始運作以後,劇評家也開始當老師上課、編刊物、介入組織運作文化政策,還有更深的介入作品創作過程,香港最近有很多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有劇評家當顧問,跟導演保持互動討論,這些都跟以前很不一樣。
關於刊物方面,協會之前跟藝術發展局拿錢辦了一份叫做《打開》的藝術評論刊物,但是今年八月之後就因爲沒有錢而停辦了。我覺得這沒有關係,因爲現在可以發表劇評的刊物已經多了,不需要特別去辦一份刊物來做劇評發表的地方,這些都是演藝評論家協會正面的功能。但是我個人擔心的、想提出來討論的是其中很明顯的一種發展的方向,就是「專業主義」,在這個劇評家越來越專業的發展中,我一直覺得劇評不應該只是談作品好或不好,而應該是觀衆與作品之間的橋樑。但是在以前因爲藝術發展局的補助並沒有藝術評論的項目,所以劇評家運作讓他們注意這個項目,讓他們承認劇評是一個專業,我贊成這個方向,但是覺得在這個過程中會忘記另外的事情,就是跟觀衆之間距離的問題,在越來越專業之中,也產生跟觀衆越來越遠的問題。
台灣劇場「八〇」與「九〇」年代現象
紀蔚然(以下簡稱紀):我講一些我最近思考的問題,就是小劇場從八〇到九〇年代變了很多,若是劇評沒有跟著相對的改變,將會產生一些問題。我們知道小劇場的八〇年代,我用一個形容詞來說,就是「不可承受的重」,主題很沈重,形式很沈重,政治性也很重。到了九〇年代來了一個大翻轉,變成「不可承受的輕」,八〇年代嚴肅面對生命,嚴肅面對歷史,嚴肅面對社會都被一個字取代,就是「遊戲」──play。
在這裡我借用最近看到一個人寫的文章來談,他說劇場不能沒有責任,但是責任可能會使劇場有不孕症,施展不開來,所以應該要有遊戲作爲平衡。但是遊戲只爲遊戲會淪落爲fun。我覺得九〇年代的小劇場就是只有fun,所以讓觀衆離開了小劇場。但是九〇年代末期的現在,又有從fun提昇到play的情形,像我最近看了陳梅毛的戲,他就不只是戲耍而已了。所以我覺得劇評要跟得上創作,首先要破解神話,小劇場八〇年代的神話,不要再把八〇年代當作失樂園看待,覺得現在的作品都比不上以前。之後呢,以前劇評所採用的標準例如結構的有機、節奏的一致、調性的統一,可能都不被現在的小劇場所接受,造成你做你的,他寫他的,之間完全沒有交集的情況產生,所以必須重新思考用什麼標準來檢視現在的作品,也就是劇評界是不是還要守著以前的美學標準來看未來的創作,這就是我提出來的問題。
王墨林(以下簡稱王):如果我沒有誤解的話,紀蔚然說的是年代改變與形式創新的問題。其中我想談的是個人位置的問題,比如說在年終藝術節作品討論中,談到陳梅毛去年的作品在香港評論很好,台灣評論不好的問題,這讓我思考到其中很多立場的差異,不只是一個美學進展的問題。剛剛紀蔚然所說的反省,我覺得在台灣這剛好是一個假象,因爲沒有先討論整個小劇場的總結,我們自己所在的位置,跟整個生態的問題,總結之前到底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像紀蔚然之前說八〇年代是太沈重的、有問題的,這個我贊成,可是這是把「小劇場運動」其中的「運動」兩個字抽掉之後,站在劇評家只從作品好壞的立場上看出來的結論。也就是說,這還沒有反省到劇評家的位置問題,要反省應該更深刻的、全面性的反省。
我個人最近看了一些戲,像是台東劇團、金枝演社,其中發現不管走本土路線的、走都市路線的,都有一個很濃厚的元素在裡面,就是:肉慾,情慾,性慾。這個現象不是從單獨作品的美學中看得出來的,這些東西讓我想到村上龍的小說《寂寞國殺人》,其中講援助交際、色情行業,整個都市到處都是色情場所,爲什麼?太寂寞了。台灣也是一樣,每個人都太寂寞了,所以作品中充滿了幹,幹,幹,而且通常不是安靜的討論寂寞,都是很直接的東西。
我要強調的是,要反省可以,可是在我們面前的是什麼?整個社會的現象是什麼?藝術跟資本主義的掛勾,藝術跟社區營造的掛勾,藝術跟補助機制的掛勾,整個生態的遊戲規則建立在「人治」上面,一些人到處當什麼委員,藝術節的評選委員、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評審委員,這些東西我們不反省,那我們要反省什麼?憑什麼我一個人,紀蔚然一個人躱在家裡反省?要反省應該是整個生態,大家一起來反省,不是一個人的反省。沒有資源的人在這裡談反省幹什麼?別人都在搶資源,到處掛勾,我們在這裡反省什麼?
閻:梁文道剛才說的是後八九到後九七的香港文化身分認同之後,產生了新興一代的輕鬆風格。這個跟台灣小劇場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的發展也頗相同。那爲什麼台灣從八〇年代的政治沈重、九〇年代的戲耍之後會走向情慾,我覺得是在尋求一種身體的解放;這個我想從九〇年代戲耍風格比較明顯的台灣渥克跟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兩個劇團之中就開始有這種身體解放的味道。渥克開始用很俚俗、低俗的風格,魏瑛娟用身體的形式遊戲,之後,其他劇團也開始這個身體解放的趨勢,但是可能朝向一個比較快速與方便的方向,就是「幹」。
我覺得王墨林在八〇年代就提出身體論的看法,是提早了至少五年,之後才出現這種身體解放的趨勢。這種趨勢現在已經有點氾濫,好像每個戲都要談情慾,不談就不夠力。剛才紀蔚然談到劇評標準的問題,我個人是希望劇評能夠有前瞻性,像八〇年代的鍾明德、王墨林,他們試圖解釋整個現象,甚至有領導走向的企圖,我們在九〇年代的劇評家身上是看不到的,而通常是一種美國消費傾向的評論,我去看戲,跟觀衆說戲好不好,然後在這個方向上走向專業主義,這可能會造成劇評對劇團或創作者缺乏一種長期的觀察與理解的問題。
王:講到八〇年代的評論,我提過一個問題,就是文化評論與劇場評論之間差異的問題。在日本有個人叫做野田秀樹,非常紅,紅到稱爲野田秀樹現象,所以很多評論家談這個現象,卻比較少談到作品本身美學的問題。台灣也是一樣,張小虹、王浩威用文化評論的觀點談小劇場,可是沒有談到作品的美學,到今天田啓元過世了,可是一般人還是不知道他的作品到底是什麼,只知道跟同志文化或性別文化有關。所以我反省我自己以前的劇評,覺得有個錯誤,就是太快地試圖建立一套觀點來解釋這些現象,太快地以爲這個觀點可以護衛這些作品,護衛當時被老一輩學院派批評的前衛的作品,我想我們應該更仔細地觀察,以免太早把一切蓋棺論定,放到什麼招牌底下。
紀:剛才談到身體與情慾的解放,我個人的觀察也是如此,但是我覺得是解放乍現就馬上退化,語言退化到口腔期,而身體則退化到肛門期,《夜夜夜麻》就是個例子。小西剛剛提到劇評專業主義的問題,這個也是會讓我在心裡皺眉頭的名詞,我想我們要避免專業主義可能會落入僵化的危機,在談論作品責任的時候,要思考劇評的責任是什麼。
梁:我想劇評的專業化不是我們決定要就可以有、不要就不會有的。這是環環相扣的東西,是整個劇場生態之中的一環。像美國就是因爲商業劇場非常發達,劇評也成爲整個工業之中的一環而存在。而東南亞,像台灣跟香港就沒有發達的劇場工業,劇評的專業化常常是跟政府有關的。我曾經是香港演藝評論家協會的董事,這個組織的專業化過程跟藝術發展局這種政府的補助機構成立是相關的,我們必須進去裡面進行政策與補助基準的意見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機器就會要求你的資格,所以香港成立了很多的聯盟,來讓藝術家得到一種專業的資格,但是得到資格之後你還必須要護衛、延續這個資格,所以會跟學院掛勾開課,得到一張證書。然後跟媒體掛勾,比如說一群人跟報社的編輯談把整個劇評的供稿接過來,說你放心,我們這裡每個劇評家都是有證書的,大家都很高興。
那新人怎麼進去呢?就從這整個制度進去,上課拿到證書後開始供稿。所以我想在我們思考要不要這個專業化之前,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機構要求的專業跟資格到底是什麼的東西?這個專業資格的取得跟標準是不是有足夠的彈性?我們整個社會都在朝向制度化的方向在走,這個方向可能很難抗拒,所以追求其中的彈性與包容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
記錄整理:陳梅毛
時間: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地點:fnac法雅時代媒體店
主辦單位:小劇場聯盟
主持人:閻鴻亞(導演、詩人)
座談:王墨林(台灣資深劇評人)
紀蔚然(師大英語系副敎授)
小西(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會員)
梁文道(香港藝術評論聯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