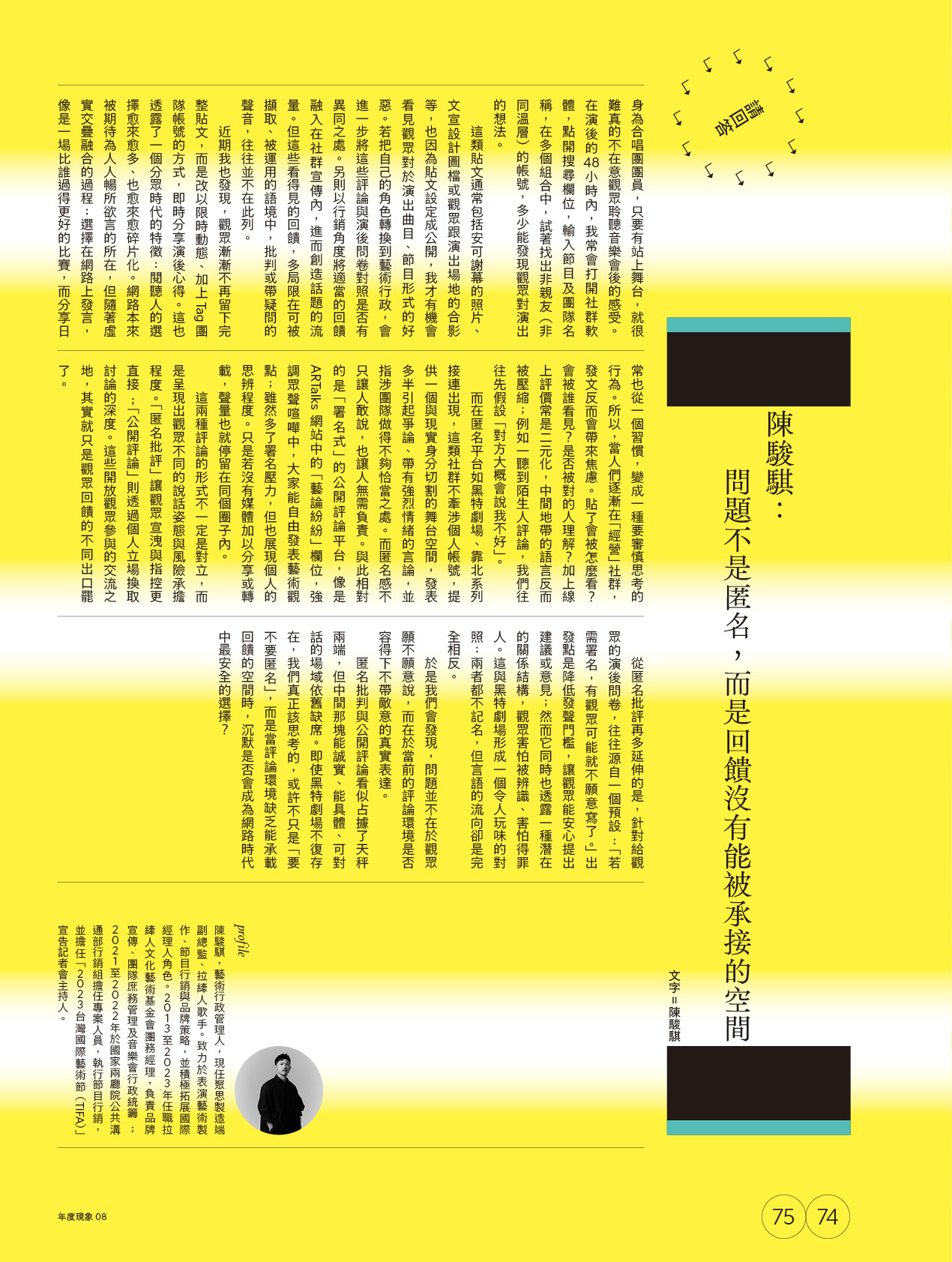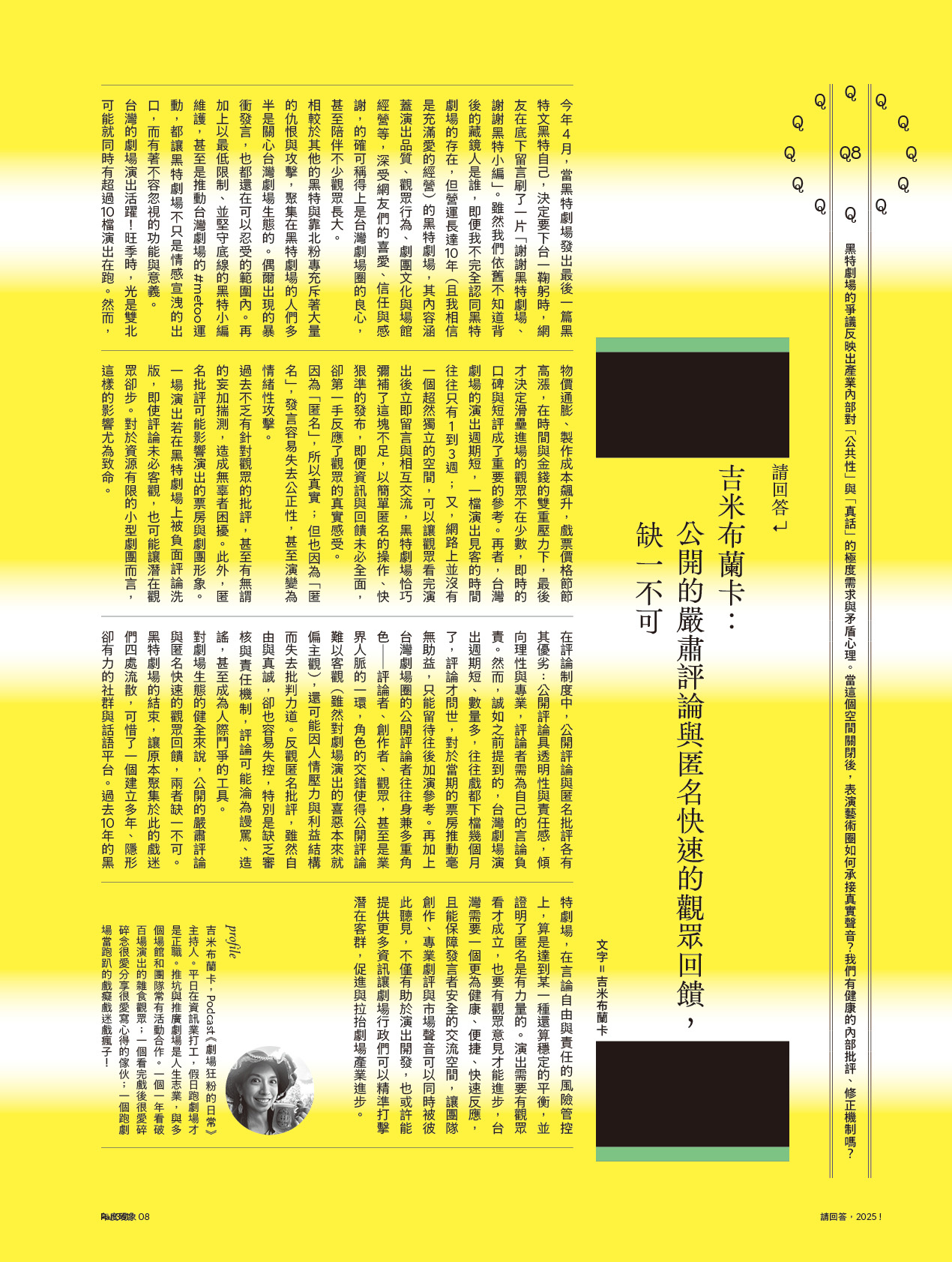收到編輯部邀請書寫一篇我們為什麼需要表演藝術時,我想了想,為什麼需要特地談論「表演」?今天全球化數位時代裡,我們人類有沒在表演的時刻嗎?表演研究學者泰勒(Diana Taylor)2016年寫了一本小書:《表演》(Performance)。在書裡,她談論表演的內涵指涉。如泰勒所言,狹義的表演是發生於特定時空的行動進程,透過行為重複(repetition)創造改革與創新的可能。
泰勒另外提到,表演預設了有觀眾存在,哪怕觀眾只是鏡頭(camera),也算在內。這邏輯是對的,但推論程度還不夠逺。由此衍生,這裡感興趣是廣義有關表演的思考。想一想,假設今天你/妳一個人在房間內,拿出手機上Threads、IG、TikTok閒晃,發自拍、廢文,或留言跟人筆戰,那個形象真的就是「自己」嗎?所謂「線上重拳出擊,線下唯唯諾諾」,這網路流行語其實已經說明,數位時代的人類無時無刻都處於表演狀態當中。哪怕自己是在物理獨處狀態中,媒介裝置仍然會讓人類處於特定角色扮演裡。當今書市一堆教人做自己的心靈雞湯書籍、自我成長課程熱賣,如此情況正好折射出,真正的「我」難以捕捉的現實,突顯了在數位時代中「真實自我」的模糊界限。簡單說,我們都活在表演中的角色裡。
如果接受這個邏輯,再看看台灣當代過於飽和,每週讓人疲於奔命的表演藝術市場,現狀其實很值得玩味。
假設1990年代小劇場運動時期,很多藝術創作者以狹義表演作為發聲管道,是為了衝撞眾多社會禁忌。至於當代的表演藝術生產,則有國家補助機制、新自由主義強力主導的市場、媒體科技飛快進展等各種元素多管齊下。創作者擁有充沛、乃至於可能過剩的資源刺激,表現他們偏好表演的角色與故事,在展演中活出他們想像的樣子。而觀眾則以追星、追夢的角度,每週去不同場域,期待看到能震撼自己的表演。這樣是一個正向循環嗎?不好說,取決於我們觀眾怎麼看待自己的表演的關係。但是,不管願不願意,當代人類都已是表演者。亦是在這樣的命題下,當代應該怎麼思考表演藝術跟人類的關聯,就成為關鍵課題。
作為溝通實踐的表演場域
在此不妨先正視一個事實,表演藝術相關門票錢比起電影等其他媒介的費用貴上不少。其中問題不多說,亦不關一般觀眾的事。重點在於,為什麼表演藝術作品票比較貴,踩到雷的機率比其他娛樂高上很多,觀眾還願意付錢,難道真是為了藝術奉獻?不能排除此原因;不過另一種可能,是演出作品裡有自己的親友、師長、或是「六度分離」內能連得上的人參與。花錢觀看作品,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戲也是去social(社交)的。
請別誤會,這不是壞事。
如同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在經典著作《遊戲人》(Homo Ludens)提出的,遊戲(play)本來就是人類本能之一。表演自然也有遊戲的成分在內,表演藝術正是這種遊戲本能的精緻化表現。不管是怎樣的演出場域,觀眾為作品付錢時,其實也是付費購買了那一個演出構成的特殊時空裡,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機會。正是這個互動的現場性與隨機性(不知道會遇到表演者之外的誰),讓人願意負擔相對高昂的票價。
無意否定表演的藝術價值,只是想講,藝術本身的內涵不見得比人跟人的網絡連結來得重要。在表演藝術共享的時空中,觀眾不只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表演事件的共同參與者。即使是靜默的觀賞,也是一種積極的參與狀態。這種獨特的互動性,讓表演藝術得以突破日常生活的慣性思維,創造出新的感知與理解可能。正是這種深刻的人我互相體驗,使表演藝術在各種藝術形式中保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表演與文化傳承的糾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梗圖?這個梗圖整理了日本動畫中重病快要死亡的女性角色,指出她們都有同一形象:頭髮會綁成一束,前垂在肩膀一側。據學者指出,這個打扮的樣式來自歌舞伎的「病鉢卷」(やまいはちまき),也就是用特定髮飾(如紫色)來表現人患重病的樣子。這樣的文化符碼由傳統走到現代,構成了日本次文化的角色代表姿態。
很多學者提出過類似看法,即表演是文化符碼、敘事的反覆回收與運用。由此角度來看表演藝術時,作品好不好看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關鍵,在於一個文化群體能夠透過表演藝術去活化、轉譯與傳承固有的非文字記憶。在台灣,傳統表演藝術如歌仔戲、布袋戲,也不斷與當代元素對話,創造出新的表現形式。
話雖如此,在各式理論與美學名詞大字面前,表演與文化傳承的關係顯得極為微妙。建立在表演傳統的樣態之上,打出種種名號的「創新」實驗不斷出現。偶爾確實會見到出色作品。但是更多時候,有些演出讓人懷疑創作者有沒有好好思考過,創新與傳統的關連是什麼?
另一方面,堅守特定傳統的表演又未必能獲得當代觀眾青睞,因而面臨消失的危險。在光譜左右兩極之間,成功的案例往往建立在創作者對自我有深刻理解,並且能將所想之事傳達給觀眾上。是的,又回到溝通的問題上了。成功的作品有多少,又有幾齣曾經重演過,這些是更大的產業問題。無論如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表演與文化傳承的糾葛會持續下去。
表演的未來該怎麼看
表演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更是人類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態。廣義來講,人類時時都在表演的狀態內。狹義的表演,在作為藝術之外,還有著不同的實用方面的考量與價值。
進入大AI科技主導時代之後,創作者有更多工具可以使用,不過未必能因此吸引更多觀眾來欣賞作品。有關表演藝術的挑戰,或許是觀眾在哪裡。觀眾生活中同樣多出不少以往沒有的裝置,可以體驗更多表演的可能性。例如,VRChat、Roblox等平台的興起,展現了表演結合科技的無限演繹方式;而AI生成技術則為傳統人類意義上的「創作」帶來新的想像空間。
在這個科技層面上,狹義的表演藝術必須和眾多其他媒介競爭,因為人類的注意力與金錢都有限。與此同時,一個人有意願的話,他╱她能利用不同媒介公開演出,每個人都可以是字面意義上的表演者。方方面面加總起來,專業表演藝術的吸引力變得更加薄弱。
對當前或未來人類來說,與表演藝術建立關係的重點,是什麼樣的形式與內容能帶來自我認知的另類可能性。簡言之,表演與科技或其他藝術形式不應是競合關係。表演藝術的核心價值並非取決於技術的先進程度,而在於它能否為觀眾、為「我」帶來未知的體驗與反思。在人人都可能成為表演者的時代,專業表演藝術的價值或許就在提供一個深度對話的場域和契機。觀眾透過共同參與(拜託,坐著動腦也算,別再一直叫人走路了)表演事件的過程,得以重新審視自我與他人、社會、世界關連的多樣性。這種深層的溝通體驗功能,應是表演藝術在數位時代得以永續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