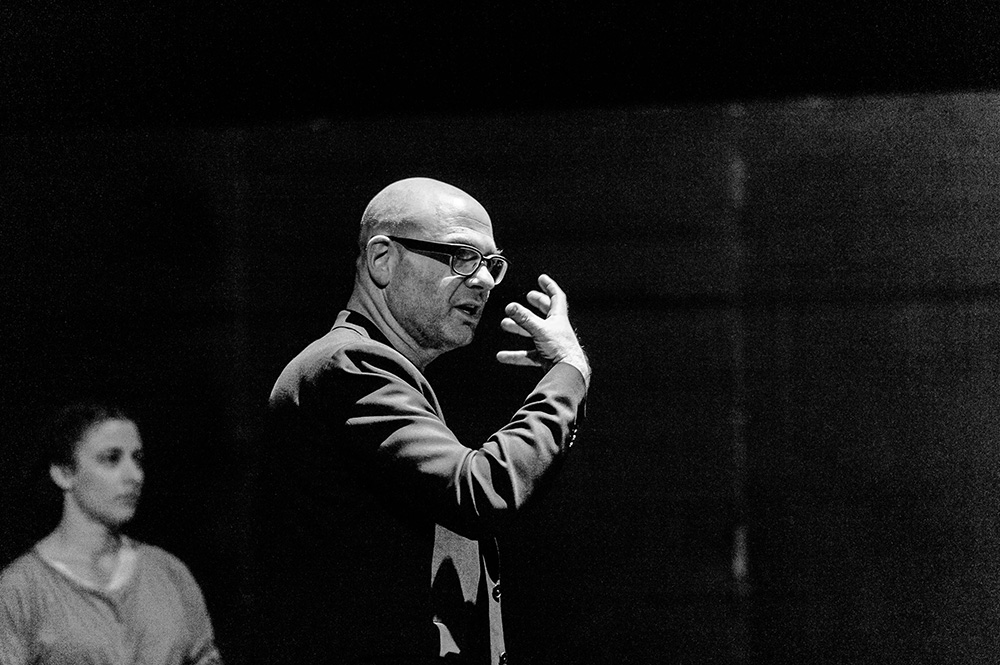Q:你的作品常被形容為「馬戲劇場」(circus-theatre),融合多重藝術語彙。你認為這是當代馬戲的趨勢嗎?
A:對我而言,多重語彙是必要的。某些主題以語言表達更具力量,但有時雜技動作與技巧才是我們與觀眾之間最強的橋梁,是傳遞情感與思想的方式。
我總是從主題出發,再尋找最合適的表達形式。馬戲藝術、技藝與平衡永遠是基礎。
就像《奔跑者》,人們或許會問:這是劇場、舞蹈,還是馬戲?對我來說,標籤和分類並無意義。
Q:夜店馬戲團幾乎是捷克當代馬戲的代名詞,你如何看待當代馬戲與傳統馬戲的關係?
A:20世紀初,捷克曾擁有歐洲最大之一的馬戲團,不僅為娛樂,其目的也有教育性——讓人們能見到平時無法看到的動物。那時沒有網路,也沒有動物園。傳統馬戲的魅力在於氛圍、大帳篷與圓形舞台,但如今少有作品處理戲劇性、敘事性或結構創新。
傳統馬戲無法適應時代,也無法找到新的出路。有人爭論是否應在舞台上使用動物,但若從那角度看,所有涉及動物的運動也都該結束。
對我而言,馬戲藝術是多元而繽紛的——從最商業化的太陽劇團,到最實驗的表演;從公共空間、畫廊,到教育性、科學性、政治性與非政治性的創作。傳統馬戲無法涵蓋這樣的廣度。

Q:你如何形容捷克當代馬戲的特質?它目前面臨哪些機會與挑戰?
A: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創作自己認為重要的主題。作品建立在強大的戲劇傳統之上,結合舞台設計、音樂、服裝、燈光與音效等創意元素。
捷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學校,因此難以培養新藝術家與下一代。我們自學成才,花了多年才達到受過專業訓練者的雜技水準。如今觀眾已無法分辨誰是自學、誰是學院出身。捷克當代馬戲仍深受劇場影響,強調敘事與主題深度。
Q:布拉格舊屠宰場區的 Jatka 78 是你們的基地,這個空間如何影響團隊的發展?
A:擁有這個空間讓我們獲得自由。我們親手翻修——成員、團隊、朋友,甚至觀眾都參與其中。劇場內設有畫廊、大排練廳、小舞台、訓練場、教育中心、餐廳、物理治療室、服裝工坊,還有製作、行銷與技術團隊的工作空間。我們同時經營第2個場地,名為 Azyl78 的大帳篷。
自有空間讓我們能製作其他劇院無法容納的計畫。我們能在舞台上完整排練1個月,使用全套舞台、燈光、音效與服裝。這在其他劇院幾乎不可能。
我們也能給年輕世代提供舞台、駐村計畫,並接待國際團隊。「擁有自己的家」帶來巨大自由,但同時也帶來責任。
這個場地也讓我們得以實現籌備5年的專案,由阿喀郎.汗(Akram Khan )執導,預定於 2027 年 10 月在布拉格首演。
雖然這地方原本是屠宰場,但在這11年間,我們舉辦了多場「為亡獸的彌撒」(Mše za duše mrtvých zvířat),那是一種大型文化行動與和解的慶典。

Q:《奔跑者》在形式與內容上完美融合,作品的創作過程為何?
A:主題永遠是核心。《奔跑者》談的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關於生命,關於時間無法重來。人生就像跑步機在運轉:當生命從指間溜走,意味著什麼?當我們跌倒、遇見他人、追逐某物時,究竟是什麼?什麼是孩童般的遊戲精神,什麼又是危險?
這些是我們起初問自己的問題。當找到答案後,我們思考如何將它們化為舞台語言。《奔跑者》就是這個過程的成果。

Q:《奔跑者》中有多處極高難度的技術片段,特別是結合跑步機與大環的段落,能否分享其中的技術挑戰?
A:若表演者沒有經過數月適應跑步機,他們絕不可能完成現在的動作。距離首演僅10天時,我們才從速度5調升至10——那是巨大的差距。同樣在首演前10天,我們第一次在跑步機上放入多個前所未有的物件與材質。
這正是我心目中的馬戲:整場演出發生在一條移動中的跑步機上,就像有人在彈跳床上。只有具備技術、經驗與技巧的人,才能在舞台上真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