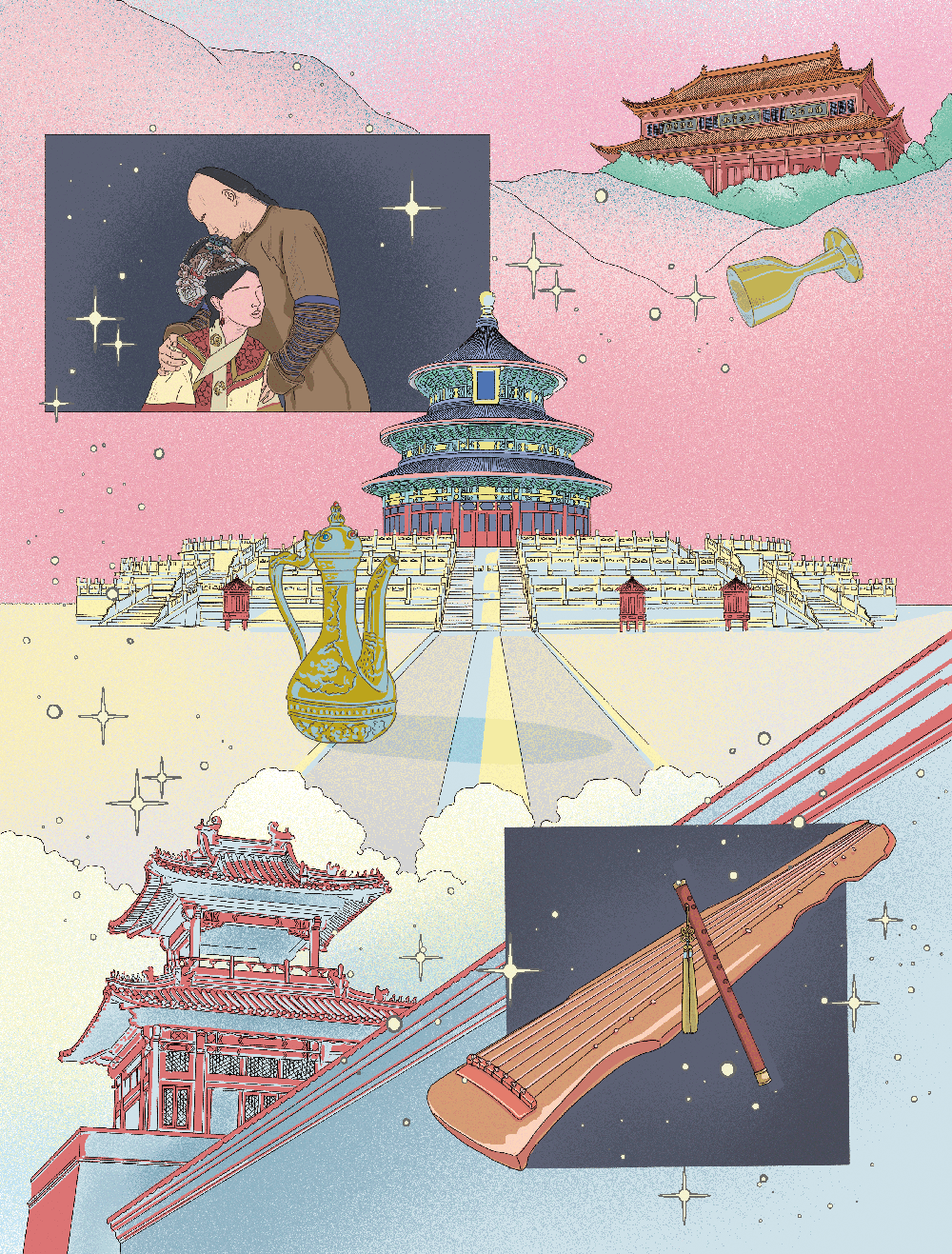将废话变成有意思的弦外之音是纪蔚然剧本语言书写的长处之一,但是那种本质消极的人生观在创作过程中书写「放弃」的心情也跃然纸上,对观众懂或不懂、欣赏或厌烦的不放心更呈现在喋喋不休的辩论与斗嘴之中,形成一种矛盾的忧郁,渲染所致,戏剧的推动与发展也不免胶著在一片暧昧之中。
创作社《一张床四人睡》
1999年6月17〜24日
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三年前从《黑夜白贼》开始,久违剧场的纪蔚然再度开始了他的舞台剧本的创作,《夜夜夜麻》、《也无风也无雨》到最近创作社演出的《一张床四人睡》,纪蔚然的舞台剧作呈现出两种明显的主题,一是以家的毁灭寻找救赎,一是以男子中年危机的忧郁编写靑春的挽歌。《黑》剧与《也》剧属于前者,《夜》剧属于后者,《一》剧则似乎徘徊在二者之间,从一个「吻」戏的排演出发,到人际关系的全面崩离,借此探讨情爱与欲望、毁灭与救赎、真实与虚幻,无怪乎《一》剧的英文剧名题为Kiss of Death,比起中文剧名,英文显然贴切而诗意多了。
剧作者忧郁特质的呈现
尽管有著耸动的剧名,尽管剧中粗鄙的语言连连,甚至性与欲的事件和话题不断交错搬演或讨论,《一》剧却不同于剧名般喜闹情调的暗示,呈现出一种论文式的理性论述,剧作者想要与观众沟通,阐述自己的哲学思考与美学辩证的一种急切心态充满著全剧。纪蔚然笔下的世界往往呈现一种矛盾的荒芜,一切似乎都不可信,一切在追求黑白分明、井然有序的答案中落入暧昧的灰色地带。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剧作者为何在演出的节目单中表明要暂别舞台剧本的创作,也正如在一篇报纸的访问稿中他自己说的,他的剧本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但他却不知道他的观众在哪里,这种忧郁的特质表现在《一》剧中,正是对于语言逻辑与精准的质疑、对剧场真假的不安与恐惧、对所谓表演真实与否的错乱与挣扎。
剧作家明明写的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表现在剧场中却有著虚幻的迷离,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玩笑中仿佛真有情感,严肃的讨论却变成一句开玩笑的嘲讽,或者也可以说,语言和文字其实是难以准确地表现出剧作者所感受到的世界。这倒不是说剧作者没有笔力以描述所思所想,事实上,剧本中呈现的语言有诸多机巧与俏皮之处,可以将废话变成有意思的弦外之音是纪蔚然剧本语言书写的长处之一,但是那种本质消极的人生观在创作过程中书写「放弃」的心情也跃然纸上,对观众懂或不懂、欣赏或厌烦的不放心更呈现在喋喋不休的辩论与斗嘴之中,形成一种矛盾的忧郁,渲染所致,戏剧的推动与发展也不免胶著在一片暖昧之中。
毁灭与救赎的主题
从结构上说,《一》剧以时间顺序的推移为发展,从排戏开始,到散戏结束,事件本身极为单纯,或者可以说情节的舖衍对剧作者而言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论述手段,当剧情表现只为了证明一个莫名其妙的「吻」背后真正的意义,剧作者似乎也以一出戏的诞生到完成,企图证明著「剧场究竟是真实或是虚幻」,或者「生命与情爱欲望究竟是真实或是虚幻」,这点从戏剧人物为「演员」的身份的选择上可以窥见。但是剧中不止一次地,透过剧中人诉说「剧场是虚的是假的」、「演戏是一种骗人的艺术」,更不时对所谓写实主义者所信奉的剧场规则、表演方法等等的嘲讽与质疑,过于沉重地直接诉诸剧中人物彼此的言谈,然而在本质虚假的剧场中,剧作者又企图创造舞台上的真实,至少必须让他的戏剧人物被观众所信服、所接受。表面上的一切似乎都不重要,剧作者关心的是暗潮汹涌的潜在主题,毁灭与救赎之间,在剧作者的笔下成为一种宿命的牵连,或者,剧作者真正质疑与关心的是,有没有一种救赎是不需要透过毁灭而达成的?
对比于赤裸裸的议题辩证,剧作者也运用了一些意象来突显其生命态度的暧昧本质,雾与吸血鬼便是其中有趣的例子。戏剧发展的下半场,四个剧中人物到「雾社」去闭关兼游玩(又是一个表象与真相的矛盾),阴错阳差地因为小杜的建议,将老齐和小杜两夫妻、小刚与安娜两情侣分为原本不该配对的两组人马,他们在雾里迷路,于是旅馆中,老齐和安娜假戏真做地上了床,完成了一年前不明真相之「吻」的毁灭欲望,另一组人小刚和小杜则在排戏的真戏假做中,完成了圣洁灵魂的救赎,情爱的真与假在淸明中无法看透,在雾的迷蒙里却得以淸醒领悟。如果这不是讽剌,便是一种无奈了。此外,小刚从第一场开始,便穿著吸血鬼的衣服排戏,表面上是角色的戏服,其实说明著人类噬血的本质,有趣的是,人不是吸血鬼,吸血鬼是人创造出来的,它在剧中是戏谑的讽刺,而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人的内在本质,刻意突显出真相与表象之间的微妙对比,再一次强调了剧作者关心的主题。
导演弥补论述沈重
剧作者醉心或耽溺的暧昧纠缠,在剧场中的实际表现便让人有所期待,导演黎焕雄以其一贯的诗意手法,和剧作的内在意涵做了相当程度的结合。在画面处理上,导演往往利用视觉的停留,制造出三角关系的画面构图,让两组不同空间的演员在多场景空间共存的舞台上定点或动或停,形成一种延伸的张力,也突显出剧中人物的紧张关系;四名男性检场人或潇洒俐落的换景动作,或如雕像般摆出姿态的神情,或将演员排戏的幻灯打向剧场四周墙壁的举动,创造出另一种诡谲的氛围和复杂的真实虚幻并陈的意象,而布景道具的移动和斜角度的灯光投射,更使舞台上制造出一种倾斜的感觉,直接指向剧中人物关系逐渐崩离的寓意。而西洋流行音乐的使用,在因为辩证而有所疏离的情节发展中,多少带有一点颓废的煽情,扩散出一种抒情的基调。种种的处理,在视觉及听觉上弥补了剧作本身论述沉重的缺憾,但同时却也为剧场的演出喷出一片迷离的烟雾,矛盾与忧郁的特质,便透过种种的舞台技巧流露出来。
作者分身四角辨证
由于剧作者对于角色的设定有其特质,主要呈现出灵与肉、前卫与传统的不同对比,在演员的选角及服装设计的搭配上显得十分贴切,然而剧作者语言模式的单一倾向却使得角色的语言特质大为减弱,明白地说,整出戏我们听到的是剧作者一人分饰四角的分裂辩证,而不是真实人物生活中的语言,当然,若将此转换思考为剧作者呈现在剧中对写实风格的不信任与质疑,意外地便形成一种统一的命题。四位演员各有特长,朴实无华的表现在真实表演与技巧娴熟之间不断游走,上半场略显乏味尴尬 ,下半场由於戏剧冲突明显增强而流露出情感的强度,于是因为论述而导致的疏离加入了情感的调剂,戏剧人物开始被关心,剧作者用大量篇幅的讨论反而不如这一点点情感的认同与交流来得有力,这里,或许稍稍解答了剧作者为之困扰的表象与真相之间的矛盾。戏,究竟是要感动人还是引发辩论,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
从剧名《一张床四人睡》粗浅联想,原以为这是一出关于情色的喜闹剧,编导却不流俗地将情欲锁定在人性本质的探索而非笑闹的宣泄,是一种値得肯定的表现。我们的剧场是不是能有勇气接受这样不太商业的方式,我们的观众是不是有智慧接受这样诉诸思考而非官能的知性表达,値得我们密切注意。但愿这种坚持不是一厢情愿的剧场人的梦想,而可以成为未来台湾剧场的另一条路。
文字|王友辉 剧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