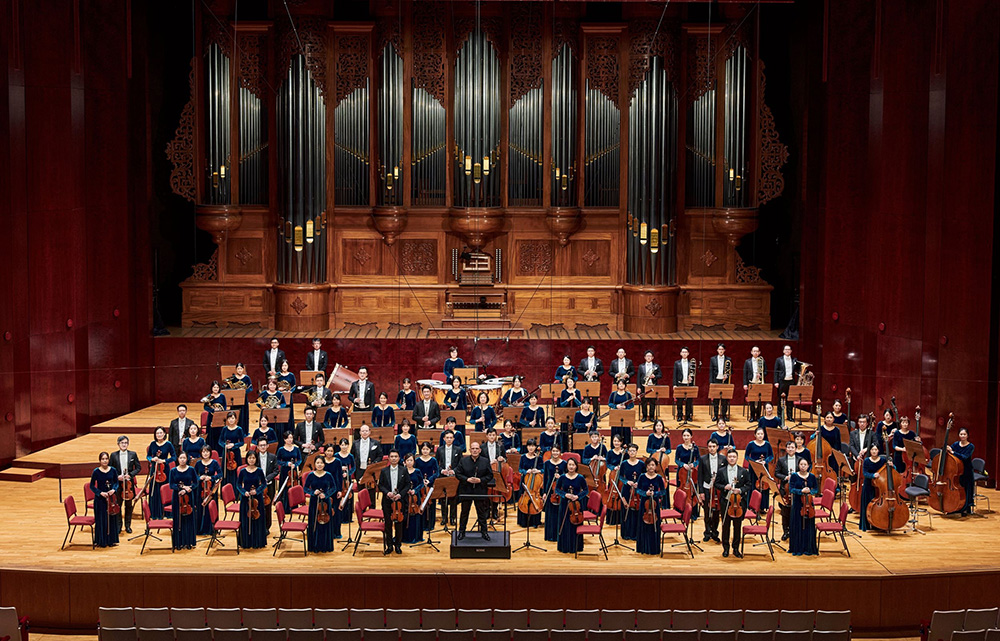张晓雄的作品,经常碰触不同的「记忆」,像是《天堂鸟》以东南亚最常见的植物象征母亲的形象,其中一段曼菲、郑淑姬和杨玉琳母女三人舞,令人动容;《Bevy》重新拼贴旅人在不断地被放逐、到自我放逐的过程中,一段又一段逝去的时光之间,过往旅程的记忆片段;《支离破碎》则处理舞者和逝去的父亲之间的对话。「『记忆』或许是我舞作中永恒的主题」张晓雄如是说。
台北越界舞团《支离破碎2—浮士德之咒》
3/15~17 7:30pm
3/17~18 2:30pm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INFO 02-27730223
人物小档案
▲出生于柬埔寨,少年时负笈中国,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现为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副教授。
▲1983年移民澳洲,进入南澳表演艺术中心主修现代舞,展开专业表演生涯。曾任澳洲希尼 ONE EXTRA舞团、澳洲国家当代舞蹈剧院、坎培拉VIS-A-VIS 舞团主要舞者。
▲1989年获选为澳洲最佳男舞者。1996年开始落脚台湾,近年往来于台湾、澳洲、香港及中国等地教学及编舞。
▲重要编舞作品:《BEVY》、《天堂鸟》、《支离破碎》等。演出作品:《沈香屑》、《芦苇地带》、《囍宴之后…》、《花月正春风…一个不能排练的即兴曲》、《骚动的灵魂》、《蚀》、《天国出走》等。
去年大概是编舞家张晓雄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年了。三月底,就在舞蹈圈好友罗曼菲的告别式后不久,他发现自己脚底下长了恶性肿瘤,最坏的情况必须截肢阻断癌细胞扩散。跳了大半辈子舞的张晓雄,怎么也无法想像少了一条腿,不能跳舞的日子,一向乐天知命的他想了一个礼拜后,就跑到医院找医生报到,「我那时候心里想,不能舞蹈了,还好我有一台电脑,存了很多照片,全是过去拍下的舞蹈摄影,这么想,就想开了。」
这个生命重大的转折,像是老天开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第一次手术广泛切除脚底表皮层后,竟奇迹地发现癌细胞并没有继续蔓延;保住了一条腿,也不需要作化疗,生命的无常让张晓雄看待事情的方式更豁达,他语调开朗,一派淡然:「去年是我的本命年,四十八岁属狗的都很惨,现在好一点了,慢慢等筋肉长回来,应该还是可以跳舞吧;不过脑子以为可以作很多动作,身体却还不能跟上,有时候我还蛮享受那个疼痛的,慢慢去习惯吧,要放松一点不要太急。」
在逆境中不断将生命推向高峰
原以为大病一场后,张晓雄会放慢创作的脚步,但他紧接著说:「或许我这个人命比较硬吧,越是挫折环境越能激发出一些东西。所以去年手术结束后,我推著轮椅回到排练场,用萧斯塔可维奇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编了一支献给曼菲的《浮生》,那首曲子原本是献给二次大战的幸存者的,旋律很heavy、很激昂澎湃,我听了整整二十年,觉得那时候是最好的时机,有那个分量。然后去澳洲编了一台《迷狂之旅》,又带著越界的舞者到北京双城艺术节重演《支离破碎》。」
在逆境中不断将生命推向高峰的力量,或许源于他从小在逃难中求生存的成长背景。生长于时局动荡的年代,编舞家张晓雄从出生地柬埔寨,因一九七○年中南半岛战争扩大的波及,流亡到越南。当时才十一岁的他,被迫和家人离散,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度过颠沛的一年,其间他历经小贩、家庭代工、印刷厂工人、包装工人等童工生活,这些童年场景对他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一九七一年底,张晓雄一家团聚,结束流亡生涯,他转往大陆杭州附中念书,加入学校舞蹈队,才正式踏入舞蹈的领域。
生命的美,往往帮你渡过难关
张晓雄说:「中学时我经过学校的舞蹈社团,看到同学们一面唱歌一面跳舞,虽然唱的是革命歌曲,整体形式却洋溢著愉悦快乐,让我这个孤独的小孩很感动,心想这正是我生活中缺乏的部分。」从小流离失所,因为害怕孤独,所以拥抱舞蹈,是张晓雄想要跳舞的起点;但说到底,也是遗传了母亲对美好事物追求的热爱:「我记得逃难时,母亲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但就坚持要带著咖啡;文革的时候,我回北京探望我妈,穿过壅塞的胡同,走道上挤满了受文革迫害的群众,一进去就闻到一股可口的香味,我妈打扮非常时髦,一身洋装漂漂亮亮,在酒精灯上烤对虾,这画面是蛮有趣的,回想起来,她几次在战乱死里逃生,无不靠的就是对生命的热情;生命的美,往往帮你渡过难关。」
虽然大学念的是历史和文学,不过张晓雄从没放弃过跳舞。一九七八年暨南大学复办的第一年,他帮学校创立了第一个舞蹈社团,带领二十四个同学南征北讨,参加各种舞蹈比赛,拿了些奖。甚至他们全家从大陆移民至澳洲的前夕,张晓雄在等待签证核发的八个月中,他也参加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课程,学习各类型的中国古典舞。进入澳洲后,因为母亲的关系,张晓雄义务到中华会馆授课,并在因缘际会下展开专业舞者的生涯。
张晓雄笑说,当时澳洲跳现代舞的人认为他身上充满了葛兰姆的技巧,但他压根就不知道葛兰姆是谁,「或许是因为东方舞蹈的身型技法和葛兰姆从东方探索源发的舞蹈技巧很相似吧。」张晓雄表示,决定当个现代舞者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赌注,因为在中国想成为职业舞者的人,超过十五岁就是痴人说梦了,何况当年他已经是二十五岁「高龄」。于是,他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在南澳表演艺术中心修习现代舞,而他也不负期待,在校期间跳舞和创作都有辉煌的成绩,屡次以学生舞作打入澳洲最重要的阿得雷得艺术节,毕业后还进入澳洲国家当代舞蹈剧场担任重要舞者。
「记忆」是舞作中永恒的主题
或许身上融汇著深厚的东西方舞蹈技巧,张晓雄的创作机会颇为人所称羡,经常往来于澳洲、香港及中国等地教学及编舞;如同他早年的流离奔波,这样的各地往返对他而言早就习以为常,不过在他内心深处还隐隐思考著文化认同、寻找一个落根之处的想望。于是,一九九六年在罗曼菲的邀约下,张晓雄来到台湾,参与台北越界舞团演出,并在北艺大舞蹈系开课,这一待就是十年。
张晓雄的作品,经常碰触不同的「记忆」,像是《天堂鸟》以东南亚最常见的植物象征母亲的形象,其中一段曼菲、郑淑姬和杨玉琳母女三人舞,令人动容;《Bevy》重新拼贴旅人在不断地被放逐、到自我放逐的过程中,一段又一段逝去的时光之间,过往旅程的记忆片段;《支离破碎》则处理舞者和逝去的父亲之间的对话。「『记忆』或许是我舞作中永恒的主题,我永远记得十一岁离开家里的时候,唯一从家里带走的,只有一桶饼乾桶和一床小时候盖的被子,记忆是无形也是人家拿不走的东西;对记忆的储存和整理伴随著我整一个青少年时期,甚至可能影响我一辈子。」
也因为早年生命中有一大段的空白,张晓雄学摄影,把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透过胶卷,存进记忆相簿,从中学时第一次拿起海鸥牌相机,小心翼翼地拍出仅有的六张底片,到现在累积大量的摄影作品。去年罹病时,他埋首相片中,将两万多张照片一一扫进电脑里,数百封家书和朋友来信,也重新影印整理成册;而走进他在关渡山头的住居,更让人有闯入时间之屋之感,里头尽是古董橱柜、家私等古物,时间于此凝止。
总是凝止在最美丽的时刻
看著张晓雄为新作《支离破碎2—浮士德之咒》拍摄的相片,背著一对翅膀的男子,肉身仿佛被遗忘的神祇,堕落人间的折翼天使,在欲望俗世翻腾、束缚著,寻求救赎而不可得,死亡迫在眼前,青春的美好稍纵即逝。
如电影般高潮迭起的人生,张晓雄以不急不徐的语调说来,像是说著别人的故事,尤其当他娓娓述说他年幼经历中南半岛战争的身世时,那战火轰隆、流离失所的斑驳沧桑,自然唤起电影或小说中相似的场景记忆,或因此,不自觉地为张晓雄的身世渲染上几笔传奇色彩。我想起来,那样的疏离感就像希腊电影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总是凝止在最美丽的时刻,而「战争」毕竟是个对我们这一代而言,太过遥远且生疏的名词,我们却因对那样场景或多或少存有恻隐的想像,而触动内心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