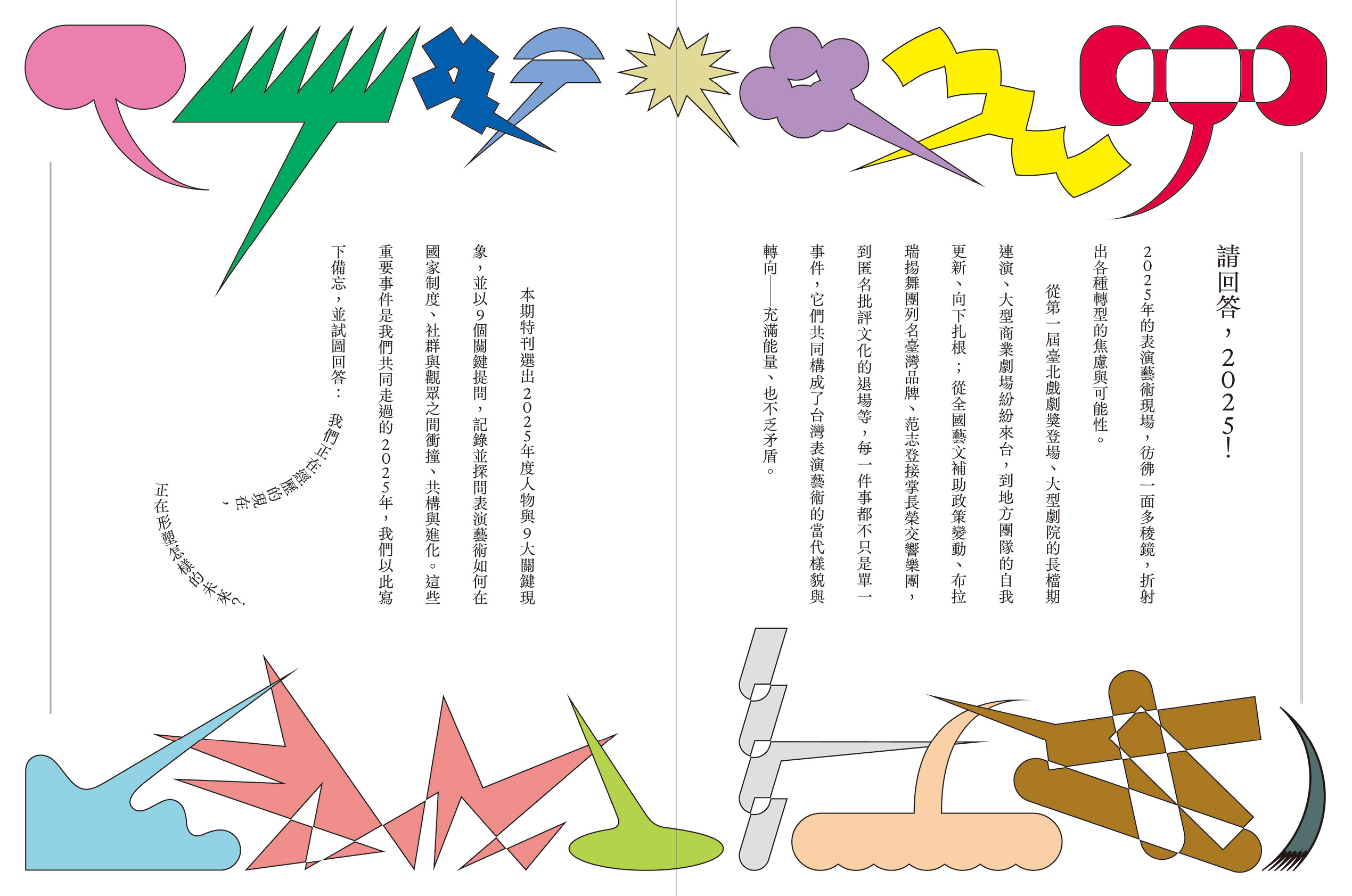在创作社演出的外场,常常可以看到李慧娜忙里忙外的身影,但无论多忙,她也鲜少露出焦虑神色,总是露出亲切的微笑。很难想像,她不时在为制作的资金缺口伤脑筋,就这么扛著剧团、走著钢索,一路过来廿一年,「做我们这行,都舍不得错过好玩的事,即使过程中很烦躁、很繁琐,但每次大家彼此激荡创意,真的很有乐趣。但,好玩之外怎么存活?问题总是这样来来去去。」李慧娜依然笑著说……
原本只是帮忙朋友剧团,时光的聚光灯开关开关,转眼廿年。
李慧娜读辅大大众传播系时就加入话剧社,从社团呈现到系上的年度剧展,她无役不与,当时和她一起做戏的包括纪蔚然、王孟超等人,几乎就是「创作社」的预备班。她毕业后第二年开始在《新象艺讯周刊》上班,担任戏剧、电影及建筑版采访编辑;一九八二年,新象为了制作《游园惊梦》将办公室改组、编整出一班制作团队,她成为制作人秘书,初登场便是规模恢弘的大型制作。新象是台湾首个大规模举办综合型国际艺术节的单位,刚离校就被推入前线,李慧娜仿佛直攻百岳的登山初心者。一九八六年她去义大利念了艺术行政再回新象复职,而后出国回国转职又兼职直到创作社成立。
创作社今年搬家,从靠河边的中华路搬到靠市区的中华路,原址新址顶多一公里距离,背后却是无中生有的考验与该去该留的挣扎。原本办公室位于政府资助的艺响空间「圆场」,不须烦恼租金的驻地让剧团有往前冲的本钱,现在却须面对一年多出三四十万的房租。她原本心想趁这时机退休,但终究如过去一样,她又发现剧场好玩的事,和办公室伙伴咬牙挺住硬是把创作社拖了一公里远。路程虽短,并不轻松。李慧娜笑说办公室一切尚未安顿好,地板脏不用脱鞋,但,地板看起来其实比平常人家还要整齐,会客桌上各式零食暖点有条不紊地摆放,采访时正逢寒流,才进门李慧娜就把暖炉搬来共享。她始终希望在身边的人都能因她而温暖。
她参加的教会有个年过六十才能参加的松年小组,她总和妹妹说,组里都是阿姨伯伯那些长辈。去年某天上教会,妹妹惊呼说:「姊,妳可以参加松年耶!」好险,高龄化,小组也把年限提高到六十五岁,但也只剩五年。创作社还能在她手上多久?假设平稳健康地活到八十岁,廿年要分多少给创作社?离去有时,她开始想怎么分享与传承。先不想创作社未来怎样,先把眼前的家搬好。对「创作社」来说,有李慧娜的地方就是家,至少眼前还有好几个有趣计划等著她去实行,也许转眼又廿年。
Q:进入艺术行政这行多久了?
A:我毕业后第二年到新象上班,直接被拉到与世界接轨的高度看表演,原来艺术节可以这样办。当时大家对艺术行政这工作很陌生,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亲戚描述我的工作名目,只说「我们是在办表演活动」,亲戚还以为是歌厅秀。以前政策没有特别照顾表艺圈,卖票还要课蛮重的娱乐税,推票比现在更难。当时场馆缺乏,除了国父纪念馆、中山堂就是南京东路的体育馆,直到两厅院完工才有比较多选择。当时也没有完善的售票系统,比如在国父纪念馆演出六千张票,通通都要手工划位再亲自去票口派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去问售票状况做票务的平衡流通,作业相当繁复。
一九八六年,我去义大利念艺术行政,回国后再去新象上班。九一年,我到牛耳经纪公司参与规划国际儿童艺术节,做了六年,中间还去英国念艺术评论。九七年,创作社成立,廿年间曾经有七年我没拿薪水,除了其中两年同时在《PAR表演艺术》杂志工作有薪资收入,这期间主要靠翻译写稿维持生计。扣掉出国念书,我总共做了卅四年的艺术行政。
提供行事历时,李慧娜为了单调不饱和的行事历有些担心,怕我们素材不够。然而,旧历年刚结束,除了大型艺术节,剧团多还在养精蓄锐,为接下来三季频仍的制作累积能量。正常上下班的作息,以及自制餐点共享的悠闲午后,在进入制作期就成为不可多得的奢求。在迁入不到三个月的新办公室里,李慧娜和同事常忆起不远处的剧团旧址「圆场」,虽然老旧、尘埃霉斑、时常漏水,忙到彻夜加班时,李慧娜也毫不犹豫住过几回。她回味晨起一片静谧,到附近散步买菜,回到办公室也还有大段时光,语气中满是怀念,身为艺术行政必须面对的琐碎忙乱,比起路上偶然眷顾的植栽花树,竟也如同微小尘埃。(邹欣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