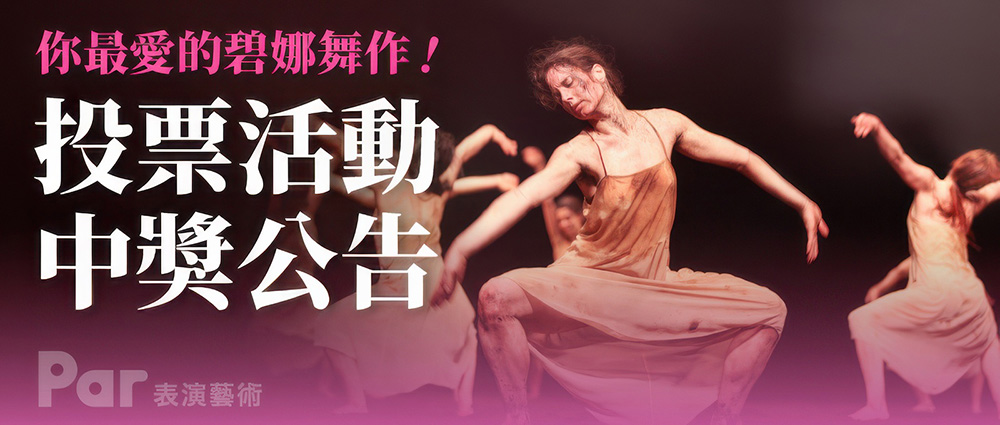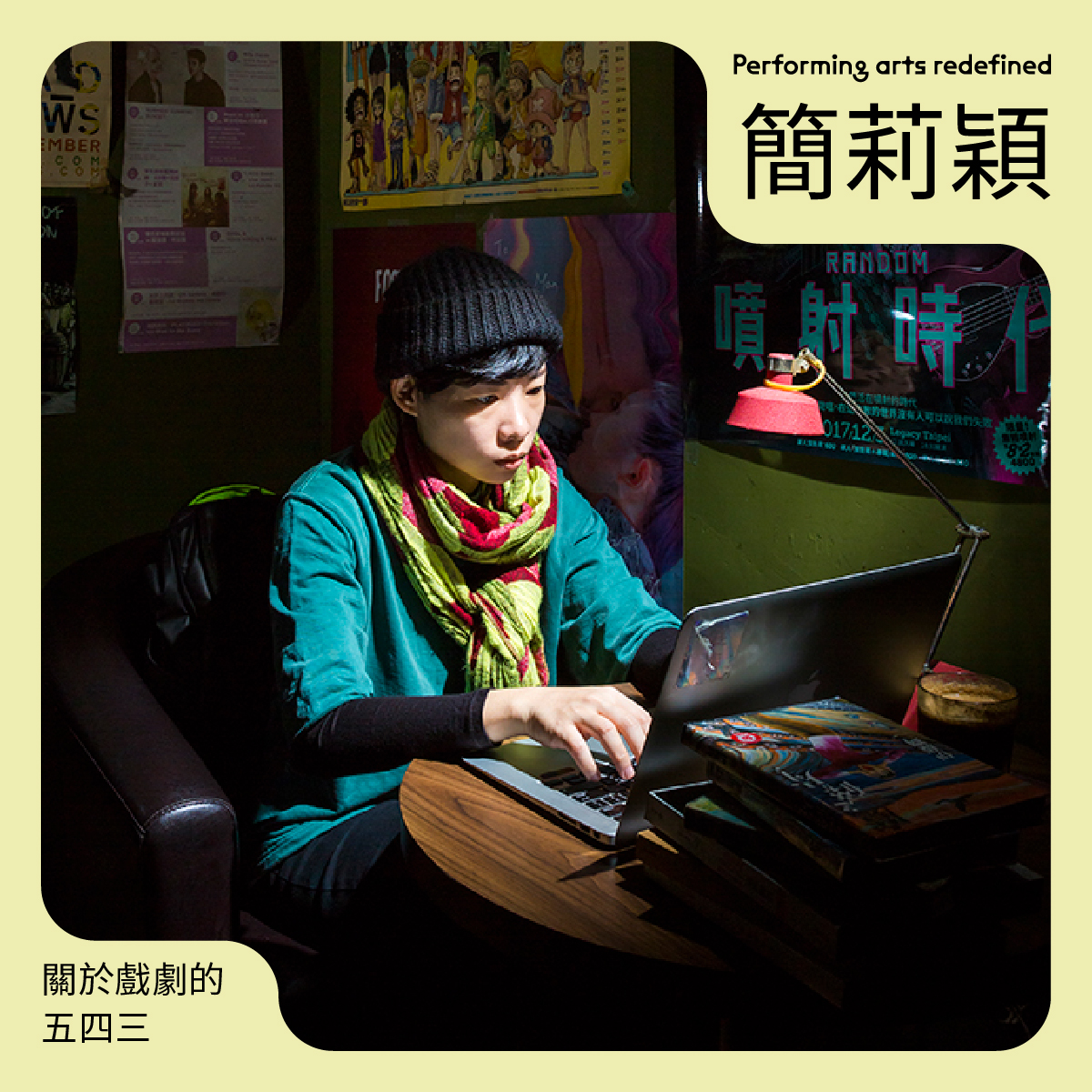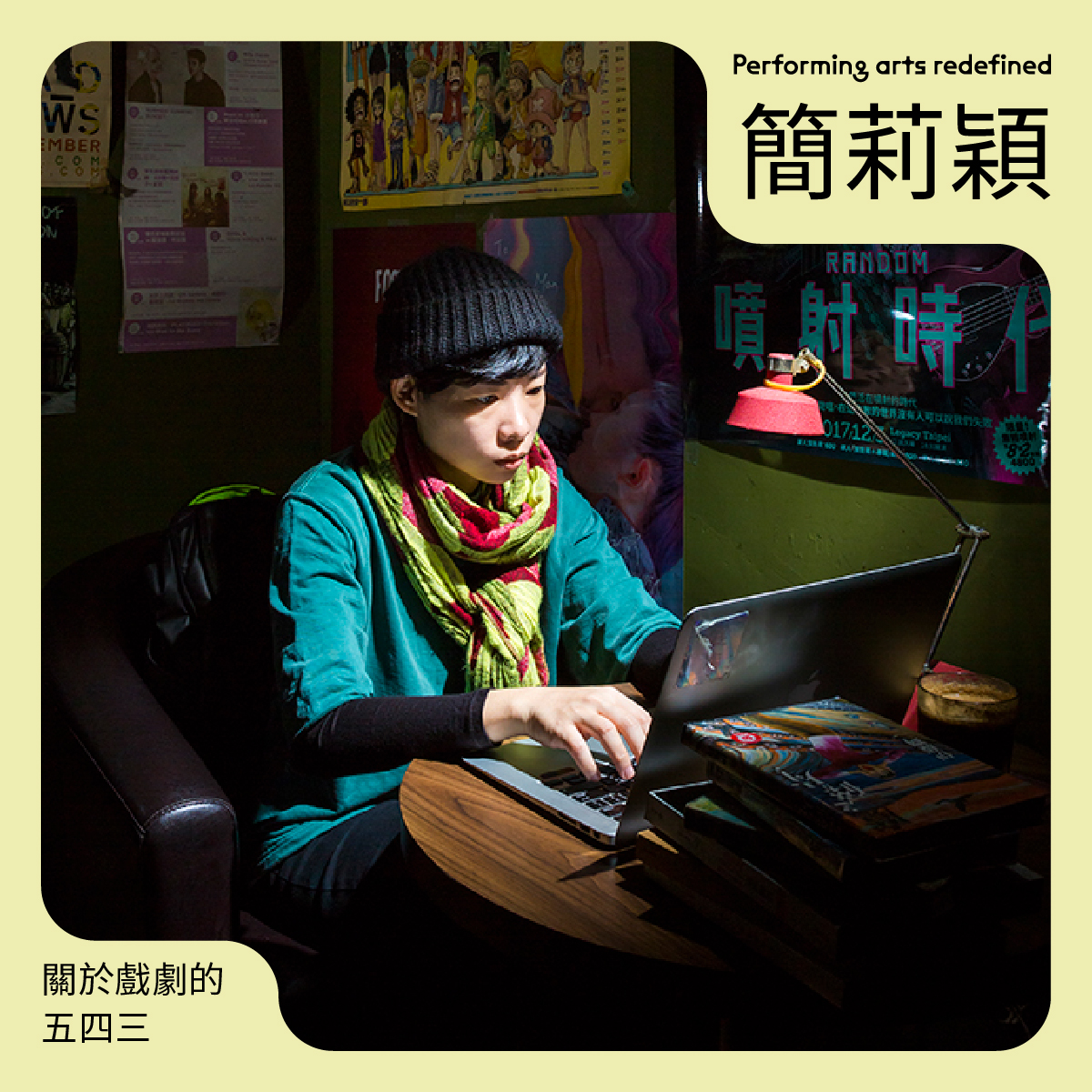本文将以杨孟轩教授描述台湾外省人离散研究的《逃离中国——现代台湾的创伤、记忆与认同》为引,从离散「外省人」视角,到台湾本土认同的多族群语言、地方书写;透过分享杨教授这本2023年出版的研究,鼓励拥有外省记忆的后代,重述自己的记忆与历史,除了否拒本土族群(闽、客、原、新)的自我追寻,或许值得有更多积极的作为。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现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杨孟轩在《逃离中国——现代台湾的的创伤、记忆与认同》这本研究,丢出一个提问:为什么第一代移民很少有回忆逃难的经验?为什么2000年后开始,陆续有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齐邦媛《巨流河》、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等外省后代以家族为座标,爬梳集体记忆的著作出版?
杨孟轩透过口述访谈、文献资料,以「创伤」、「记忆」、「离散」三大理论支柱,试图剖析1945-1950年在国、共两个残暴的军事集团对峙中(比如湖南饥荒、长春围困战饿死了大量平民),这群跟著国民党来台的战争移民,如何处理他们的创伤,与怎样形塑自己的文化与身分认同。
杨孟轩提出一个学术上的讨论:外省人的双重性,认为他们既是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抵台后又握有政治分配的权力,杨提出了外省人经历的4个社会创伤:一、1949年的大出走;二、1950年代末的返乡梦碎;三、80年代末期的探亲梦碎;四、1990年代后面对「台湾本位」的焦虑。
每一次社会创伤,外省人就会从记忆资料库中,提取一段记忆来疗愈伤口:1949年后,有大量回忆对日抗战胜利的书写,特别是通俗旅游文献,许多人将台湾的经验与过去在中国的逃难,特别是重庆的经验相比,也深信最后的胜利返乡必定到来,「战时过客」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成为中影拍摄优秀抗日电影的重要基础。到了1958年,蒋被迫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知道回不去了,外省人的重要记忆又开始改变,「文化乡愁」取而代之,他们开始大量组织同乡会,出版湖南文献、贵州文献等,此时却面临第2代子辈对此兴趣缺缺。1980年代,解严后开放探亲,有成千上万的外省人返乡,这是第3个创伤,也就是返乡后人事已非的风景,在外省人的返乡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日思夜想的亲人,变成唯利是图的陌生人,此时台湾民主化以及台湾主体意识的兴起,「成为他者」作为「外省人」的恐惧,年轻一辈「外省人」关怀长辈、怀念家乡,「老兵文学」及「眷村文学」开始兴起,剧场界当以赖声川为首的创作为代表,也为后来第3波的文化记忆「讲述大出走」(narrating the Exodus)奠下重要基础。
是以,这就回到了杨一开始丢出的问题,「为什么外省人二代,开始产出大出走的记忆?」作者认为,这是为了证明:「为了构筑以在地为基础的『外省台湾人』认同。……他们为父母及祖父母在1949年被压抑的伤痛做见证,不只为了减轻自己在民主化台湾所遭受排斥与污名化的创伤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坚定主张,自己也值得成为岛国新生的想像共同体其中一分子」。
杨孟轩的爷爷、外公家族皆是二二八的受难者,父母在他10几岁时带他移民加拿大,绝口不提上一辈的遭遇,一直到回台湾做研究之后杨才认识家族的历史,但在访谈外省二代的过程中,杨从咎责的愤慨到理解了当中的复杂。
除了社会意识的变化,自己就读戏剧系以来,从翻译戏剧、戏曲改编与赖声川为首的戏剧作为代表,再到如今以台湾社会为创作主题,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言作为演出语言,从业10几年来有极大的变化,我认为,白恐主题的戏剧,并不仅仅只是如王墨林在之前PAR的剧评所言,是「执政当局的转型正义政策的宣导」,群体身分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是构成自身的重要元素,远在自己出生之前的事,建构了一个族群的身分认同。任何历史类型的戏剧,都需要更多元的图像,当然,也包括「外省人」图像,是以,与其否定重述过去的戏剧之必要性,不如去探问,拥有不同身分记忆的创作者对记忆的怠惰:白色恐怖并非单单本省福佬人所有,根据杨书中的资料,1950年代初期,外省人占台湾人口约10~15%,但被检肃为匪谍的,外省人占了一半的比例,这代表外省人受国民党迫害的比例,是本省人的6到7倍。而许多本省作家、政治人物在70至80年代对外省老兵的关心,也在当代族群政治的严重分歧中被遗忘。
这本书引述的访谈跟文献都有血有肉,有人情绪激动,有人掉头就走,有人不满「外省人」一词,在戏剧中,「细节」就是让人产生同理的要素。我也是念了原住民系因而了解自己作为都市汉人,资源比原住民丰厚许多。作者指出,「与受害者有关的人不会因此就特别神圣,与加害者的关联并不构成原罪」。如何进一步去理解彼此的记忆,试著说出自己的记忆,或许会是进一步凝聚身分与文化共识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