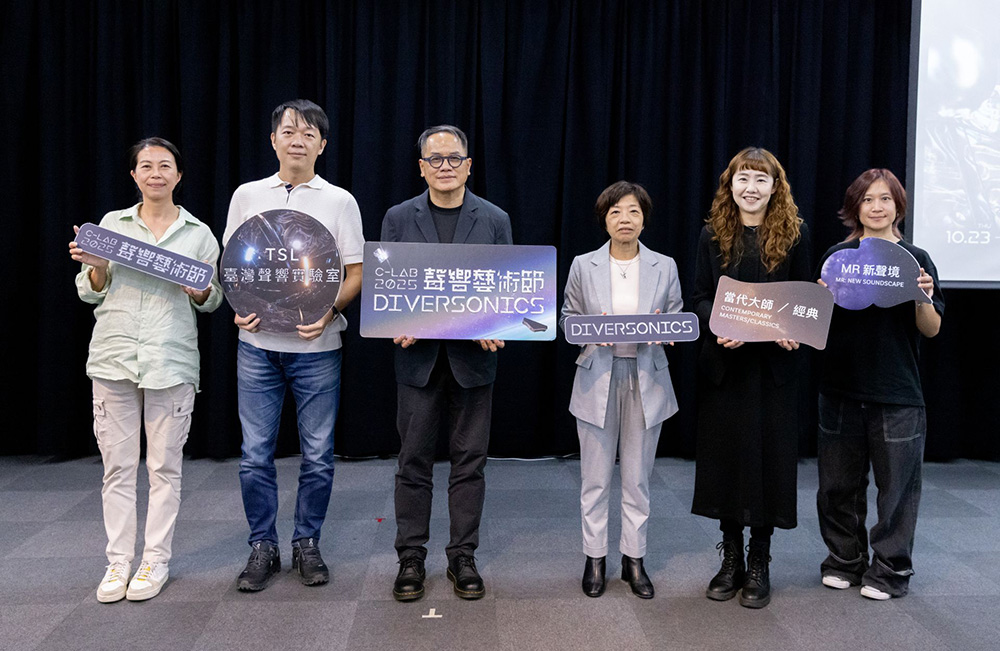当舞蹈不再只是技艺展演,而是生命故事载体,我们是否能在身体的记忆中,找到那些被遗忘的自己?复象公场2025年带著《打人的狗》回到台北,用最真挚的身体语言,书写一段横跨30年的成长自白。
这个故事始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提问:「为什么而跳?」舞者王珩从8岁学舞至今,长年累积的不仅是精湛技艺,更是反复涌现的困惑与驱动。2019年起,她在素人舞蹈课程中观察到一个动人的现象:成年学员虽背景各异、专业水准不同,却都带著属于自己的身体故事,每个动作都流露出最真诚的情感。这让王珩深刻体悟,动作不只是技术,而是每个人生命故事的展现,「舞」与「人」密不可分。
延续「身体记事创作计划」的核心精神,《打人的狗》于2024年在高雄春天艺术节首演后,持续巡演累积丰富的交流经验。2025年,复象公场将这部作品带回他们熟悉的台北,为观众呈现一场最诚实、最深刻的身体记事。

主角王衍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荒诞与真实的交织。从小被母亲以各种理由「唬烂」著学舞——跳舞能防身、能强身、能爱国、能出国、甚至能成为美国人。这些看似荒谬的理由,在王衍的成长过程中一一出现,又一一崩解。从踢踏舞、芭蕾、中国舞到歌仔戏,从假德国老师到太极拳表演者,每一个转折都映照著台湾社会近30年来的变迁。
结合编剧李承寯的文本与导演李承叡的敏锐观察,团队将《打人的狗》塑造成一部兼具私密性与社会议题的作品。在这个单人剧场中,王珩一人饰演约12个角色:母亲、老师、德国学员、美国评审、歌仔戏团长……每个角色虽是路人,却都在关键时刻推了主角一把,影响著她对自我的认知。

「其实最真实的,是在妈妈的身上。」王珩表示,虽然剧中许多角色都是虚构或多人缩影的拟人化,但母亲这个角色承载著最深刻的真实。天下父母心,总希望孩子能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得更高更远,不必重复前人的辛苦。母亲将自己未竟的梦想投射在孩子身上,而孩子最终走的路,却未必如父母所愿。
「没有一个人是出于完全的恶意,」王珩以温柔的态度理解这份代际传承的复杂性。「加诸于身上的期待,不是故意要让你难受的,而是他们相信的事实。」这种理解不是妥协,而是在回望中获得的智慧,了解后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也明白父母的出发点。

从90年代到当代,台湾经历了多重拉扯——政经变动、身分重塑、价值观更迭。《打人的狗》不只是王珩个人的生命记事,更是整个世代的自白。在准备过程中,她发现故事里的年份串起了我们共同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小在舞蹈班被推著学舞,到最后会有这么大的失根感,或是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感觉。」
在这个真假难辨、身分模糊的时代,王珩透过舞蹈与表演,不断提问那个一直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这个关于国族叙事、自我寻找、社会关系的宏大命题,被浓缩在一个母女关系的故事里,荒谬得让人发笑,真实得让人心痛。
「这是一个跳著跳著就哭了的故事。」王珩以身体为笔,书写台湾舞蹈史,也书写我们共同的成长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