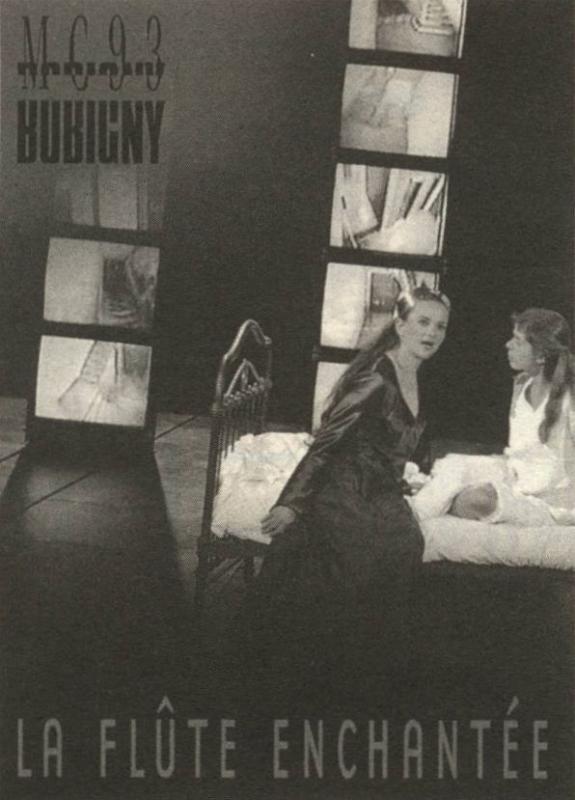被英國重量級劇作家品特稱為「詩人」的作家莎拉.肯(Sarah Kane),其作品大膽衝撞歐洲政治、社會、家庭與性的禁忌,並描寫舞台上難以表現的酷刑、屠殺、食人、強姦與亂倫,藉以嘶喊出對世界的恐懼與狂怒。《四點四十八分,精神異常》速寫具有自殺傾向的精神病患的耗竭狀況,充滿了激情與譫妄,表現了作者的全部力量。
若要重新尋覓其必要性,在愛、犯罪、戰爭或瘋狂裡的一切,戲劇都應該給予。
──亞陶(Antonin Artaud)
《四點四十八分,精神異常》4.48 Psychose的演出是去年巴黎秋季的戲劇盛事。在崇尚樸實無華風格、藝術要求嚴格的法國導演克勞德.黑紀(Claude Régy)執導下,伊莎貝拉.雨蓓(Isabelle Huppert)第一次擔綱主演、詮釋於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在倫敦自縊身亡,享年二十八歲的英國劇作家莎拉.肯的遺作。
被禁錮的絕望與疏離
雨蓓在暗闃中自觀眾席間走道以輕悄的小跑步,踏上巴黎「北方滑稽歌劇演員劇場」邊界不明的舞台空間,在一小時四十五分的表演時間裡,直立定點、寸步不移。她紮了個自然的少女馬尾,身著藍色短袖圓領衫及象徵叛逆的直筒皮褲,足登籃球鞋,使她略帶稚氣的嬌小身材,產生雌雄同體的幻覺。在開場時漫長的沉默中,她彷彿被莎拉.肯遺囑般的詩文穿透,情不自禁地淚珠盈眶,但毫不眨眼。演出中,她雙臂貼身下垂,偶爾緊張地舉起,雙拳緊握,偶爾痙攣似地展開。幽靈般的臉色,空洞的眼神,雨蓓以奉獻、被禁錮的絕望英雌姿態,成功地扮演了這個瀕臨自殺邊緣的疏離者角色,贏得觀眾與劇評的一致喝采。
黑紀在雨蓓背後架設了一片特殊材質的簾幕,雖呈金屬光澤,實際上產生了像金屬牆的功效,不但可供投射,也同時能讓字與數字投射到劇場的背景牆上。這些投射因此被切割成兩部分,有的超越簾幕,直到投影在劇場兩側的樓廳和牆上,使得觀眾感受到建築物的佈局被打碎、弄亂和擴大,而被轉換成一個心理空間。雨蓓和劇中另一演員瓦特金斯(Gérard Watkins)隔著簾幕對話,兩人從未面對面,象徵著無法溝通的困境。
流星般的烈焰生命
被英國重量級劇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稱為「詩人」,也被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劇作家博德(Edward Bond)譽為「新英國戲劇」(New British Theater)中最重要的作家莎拉.肯,其作品吸引了英國當今二十到三十歲一代的年輕戲迷。一九九五年,她的第一篇劇作《摧殘》Blasted在倫敦皇家宮廷劇場(Royal Court Theater)首演時,引起媒體的騷動,迅速成名。在如流星般倏忽即逝的烈焰生命裡,她總共寫了五篇影響英國當代劇壇深遠的劇作,現在在歐洲各地不斷地被搬上舞台。
莎拉.肯大膽衝撞歐洲政治、社會、家庭與性的禁忌。在她最暴烈的作品中,喜歡描寫舞台上難以表現的酷刑、屠殺、食人、強姦與亂倫,藉以嘶喊出對世界的恐懼與狂怒。因此她的劇作充滿了挑釁、猥褻與顛覆性,令人想到亞陶的「殘酷劇場」;作者本人也曾承認亞陶與她劇本的相關性,但她直到寫作《四》劇時,才讀到亞陶驚人的論述。
《四》劇宛如一首長詩,沒有角色,也沒有舞台指示,在表面的鬆散結構下並列內心獨白、對白的斷片、交談的片段、一連串的藥物名稱、病狀、字與數目字等等。作者主張的「形式即意義」,不僅體現在文體的音樂性上,同時也體現於文本在頁面的排版上:重複地另起一行、右側的評注、自由的字距與行距等等。此外,劇名中的「四點四十八分」無疑指出黎明前精神清醒的極限時刻,也是劇中陳述者自縊的時間(「四點四十八分/當自暴自棄造訪時/將自縊而死/聽著我底戀人呼吸的聲音。」)
速寫自殺前的耗竭
《四》劇速寫具有自殺傾向的精神病患的耗竭狀況,充滿了激情與譫妄,表現了作者的全部力量。開場時,在意識清醒的短暫片刻,陳述者以一連串重疊排比的問句自我質疑:「可是妳有朋友。/妳有很多朋友。/妳給予妳的朋友們什麼?使他們如此支持妳?/妳給予妳的朋友們什麼?使他們如此支持妳?/妳給予什麼?」她不自覺地、深刻地拒絕一切並厭惡自己的身體:「我好胖!」、「我的臀部太大」、「我討厭我的生殖器官」;同時表明在接受醫學治療時,體重暴跌暴增,和描述與不知所措的精神病醫生破洞百出的談話,更自稱為「破碎的陰陽人」。
莎拉.肯自殺前不久公開談到《四》劇時說﹕「在人的頭腦裡,現實與各式各樣的想像之間的屏障完全消失,以致你分不出清醒生活和幻想生活的區別……你不再知道該在哪兒,也不知世界從哪兒開始……所有都屬於連續的一部分,各種各樣的界限開始崩潰。」再者,文末一連串的祈使句,透露出她對愛的需要與幻滅:「確認我/見證我/看我/愛我」、「看著我消失/看着我/消失/看着我/看着我/看着。」在吐出最後一句話「請把簾幕打開」之後,她便告別她的精神煉獄,她的痛苦、黑暗和疲乏,永遠地沉寂了。
導演引導生命物質的交織
導演黑紀已屆八十高齡,今年是他第五十年的劇場生涯。這位對現今法國四十歲一代導演有深刻影響的大師,不依靠劇院機構或常設劇團,特別致力於當代戲劇作品的首演,其中大部分是法國以外的作品。他經常與在世的劇作家合作,最近幾年則發掘了三位歐洲新生代劇作家──挪威的佛思(Jon Fosse)、蘇格蘭的哈洛爾(David Harrower)和莎拉.肯。黑紀於一九九一年獲得法國「國家戲劇大獎」(Grand Prix National du Théâtre)的肯定,三年後再度榮譽加身,獲頒「巴黎市舞台藝術大獎」(Grand Prix des Arts de la Scène de la Ville de Paris)。
對黑紀來說,他導演的主要工作在重新處於文本寫作之前的狀態,試圖感覺話語和動作的起源。對於表演手法,黑紀選擇極簡的原則,他說:「我不相信聲音的練習,也不相信肉體的表達。」他反對所有歐洲傳統劇場的寫實主義,關注「如何引導每個人,以自主的方式,革新自己對世界的感覺。」他以緩慢的節奏、燈光投射佈景的優勢,以及疏離的美感,來達成這個目標。
黑紀細緻縝密地執導了這部莎拉.肯的天鵝之歌,雖然整體演出過於均勻地抑鬱,忽略了文本中某些劇烈的掙扎,仍然讓我們無聲地聽見,在套上命運的繩結前,這個罹患精神分裂症的陰陽人,是如何勇敢地說出「我」這個字。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傾聽充分流瀉的文體
專訪克洛德.黑紀談《四點四十八分,精神異常》
地點:巴黎的「北方滑稽歌劇演員劇場」
時間:二○○二年十月五日
訪問整理:蘇真穎(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前言)戲劇學校學的、電視上演的及百分之九十五舞台上的呈現等等一些慣用的表演方式,正是謀殺作品文體的表演手法;我們聽不見文體,文體不活躍。我的嘗試是繼續致力於文體的傾聽,讓文體被聽見和充分地流瀉;倘使文體能被確切聽見,那麼就能建立傾聽者想像中的表演。
蘇真穎(以下簡稱「蘇」) ﹕您是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戲劇導演之一,現在「北方滑稽歌劇演員劇場」正在上演您最新導演的《四點四十八分,精神異常》;您為什麼對莎拉.肯的《四點四十八分,精神異常》感興趣?
黑紀(以下簡稱「黑」)﹕我不止感興趣而已。對我來說我最關注的是,我們發現了一個仿效許多前人,比如貝克特(Beckett)、品特(Pinter)、畢希納(Büchner)以及其他人,甚至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新文體;然而莎拉.肯發明了一種隨着每部劇作轉變的寫作方式。
她總共寫了五個劇本。在前三個劇本裡,都有極端暴力的行為如雞姦、口交、閹割與拔卸肢體及眼睛等的描繪;在這三部劇作之後,她認為其實這些暴力行為的呈現對她來說都是隱喻,也許她希望停止在舞台上表現這些暴力,而決定往後將寫作當成語言的錘鍊。
僅僅頁上一字,即成戲劇
她最引起我共鳴的是在《四》劇中所說:「僅僅頁上一字,即有戲劇。」( Just a word on a page and there is the drama)。 實際上我所嘗試的就是放棄所謂的奇觀式演出,如佈景、動作、機器裝備、燈光、映畫和複雜的音效等等,而以語言的處理為優先,並且訓練演員讓他們的語言被聽見,來證明語言能傳遞感覺、運載感覺。同時,如果以某種方式述說語言,將會讓語言的形貌被看見。因此,我選擇避免創造過多的形像,甚至絲毫都不要,也沒有什麼佈景,反而使用流動而無限制的元素如燈光,讓文本來創造並影響觀眾的想像。觀眾看見文本希望讓人看見的,從他們聽到及看到的線索開始想像。
莎拉.肯的文筆十分艱澀、十分赤裸,事實上,她以一種絕對直接的方式直指「存在」。同時,她面對人生和社會的態度非常極端,也就是說她不想死,但是她也不想活。無疑地她因為不知該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也無法和她不能接受的世界聯繫,終於導致她走上自殺一途。
蘇:兩年前《四》劇在倫敦首演時有三名演員,為什麼您只以伊莎貝拉.雨蓓(電影《鋼琴教師》的女主角)與傑哈.瓦特金斯的兩人對話來演出?
黑﹕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詮釋方式。莎拉.肯說她不知道這裡面有多少角色;因此與其說這是一個劇本,不如說是一首詩,而她想證明一首詩也可以是戲劇。不管是像倫敦的三人演出還是幾人,都是情有可原;不止是莎拉.肯,從許多憂鬱症、自殺的病例來分析動機,我們知道精神分裂症會增殖人格,因此我認為由同一個人詮釋多重人格比較有趣,感覺也比較強烈。
多重人格的演出詮釋
伊莎貝拉.雨蓓特別具有這種詮釋多重人格的天賦,連續詮釋幾個非常不同的人,甚至在肢體有所區隔。只是在這齣戲裡有許多的拼貼,和寫作風格的變化,實際上還有好幾個文體。除了設法讓觀眾聆聽和想像這些文字被書寫的原貌,我還保留了短篇幅的對話語氣,並且避免讓觀眾以為這只是一段主角與醫生面對面隔著一張桌子、在精神病院裡的對話。
透過演出,這些對話變得抽象,同時這或許發生在她的回憶裡,並任由她重新組織。她對殺她的醫生感到莫名其妙,卻又帶著激情的愛。她嚴厲批評精神科的治療方式,更嚴厲批判她所謂的化學性腦葉切開術,亦即大量使用抗憂鬱劑來試圖救人。我們雖然可能把某些人從某些事情裡拯救出來,但同時我們也可能奪去他們的生命,使他們的身體變壞,改變他們的思維,也剝奪了他們真正的人格,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即使是對所謂進步的精神病醫學,我們也要對其提出質疑;同樣地,更要探究它的極限。事實上,縈繞在莎拉.肯腦際的念頭之一就是消除界限 ,跨越極限;而對我們的社會來說,就是打碎所謂正常與不正常的界限。當我們正視社會和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我們發現它病入膏肓,各國元首似乎也是病入膏肓,很奇怪的是這些「病人」以什麼名義決定其他特別有天賦、特別聰明而超越普通思想的人是病人,而他們不是?繼俄共與德國希特勒之後,是制度決定了作品思想有礙當權者的人,必須被送進精神病院和勞動營等等而無法繼續寫作。我認為,莎拉.肯的劇作說的就是這件事,她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見證人,一個以自殺作證的見證人。
沈默與傾聽的關鍵
蘇﹕和您之前的作品一樣,我們在《四》劇中聽見大量的沉默。您對劇場中「沉默」的處理有何看法?
黑﹕我們應該將沉默視為一種語言,而不是什麼語言的停頓。演員總是發出聲音,又很快地激動起來,說得太快而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從那裡說出來,為什麼說,或隨便說而不留意台詞的文體,只造成動作與聲音的混亂,什麼都無法辨認,這是一種絕對的蒙昧主義,也是大多數劇場演出的情況。無論如何,在我們歐洲地區是這樣,我希望在你們國家不一樣。
蘇﹕您努力讓您的演員避免角色分析與自然主義的扮演原則。那麼要如何指導演員飾演如此極端的自殺者?
黑﹕只要其他事情不假裝,專注於作品就好了。在作品裡潛在著真正的內容,還沒有完全具體化,也還沒實現,然而卻能激發比現實表象更強烈的想像。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作品世界的潛能狀態,並懸浮在想像事物的世界當中。要達到這個境地,只需要聆聽作品就夠了,一切都在作品當中。當它是一部真正的作品時,演員的表演方式就在作品裡,導演也在作品裡。因此,除了傾聽文本之外,沒有別的,我希望演員們專心傾聽文本,而我們傾聽專心傾聽文本的演員。
當然!我們也花好幾個月的時間研討文本,我們經常重新翻譯作品,朝各方面探索,嘗試聯繫作品裡作者無意識的部分,而那部分確實非常廣大,這是工作的本質,作者的作品正好揭露了持續存在而無意識的事物。如果我們好好傾聽,可以感覺到文體的根源,感受到從作者身體發出的聲音,如何釋放寫作中沉澱的東西。重要的是,不要裝內行,自以為是天才或戲劇家。歸根結柢,戲劇學校學的、電視上演的及百分之九十五舞台上的呈現等等一些慣用的表演方式,正是謀殺作品文體的表演手法;我們聽不見文體,文體不活躍。我的嘗試是繼續致力於文體的傾聽,讓文體被聽見和充分地流瀉;倘使文體能被確切聽見,那麼就能建立傾聽者想像中的表演。道理非常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