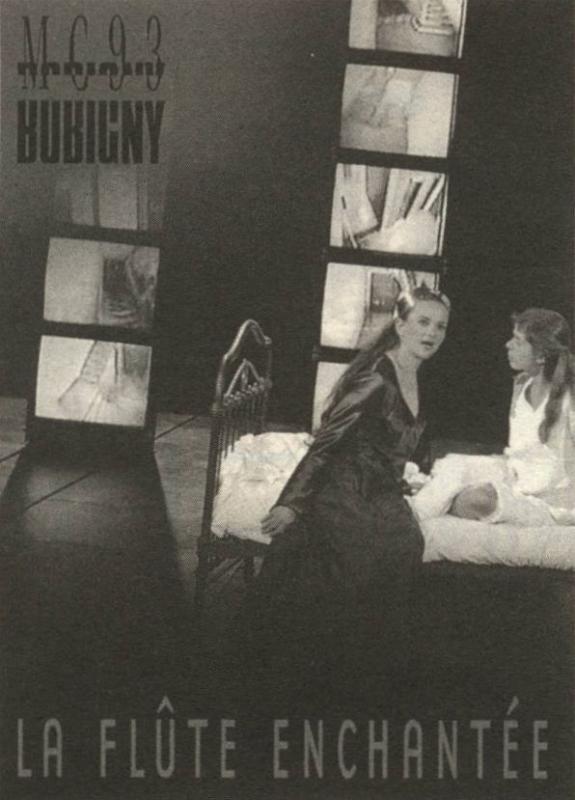由於對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神秘主義與古代神話傳說充滿興趣,
加上他的激情和同性戀傾向,巴索里尼將他的多元藝術創作視為一種戰鬥。
他以詩意的文體,展現對他人、世界與當代歷史事件的批判關係﹔
他的六篇劇作皆籠罩在悲劇的氣氛當中,在詩意、哲學與政治形成的張力下,充滿了亂倫、詛咒和激烈的情慾。
以電影作品揚名的意大利導演巴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也是劇作家、詩人和小說家,一生總共撰寫了六齣戲劇,在他生前和死後十五年間,幾乎不曾在法國舞台上演出,雖然他的傳奇持續地激發著法國戲劇、文學及電影界的思考。直到新一代的法國戲劇導演──從前任「傑哈.菲力浦劇場(Théâtre Gérard-Philipe)總監的諾爾德(Stanislas Nordey),到現在執導其劇作《皮拉德》Pilade的默尼耶(Arnaud Meunier)──被這個「烏托邦狂人」的「絕望生命力」所魅惑,前仆後繼地將巴索里尼的劇作搬上舞台。
《皮拉德》自今年二月下旬起在「巴黎─小城劇場」(Théâtre Paris-Villette)上演,直到三月中旬結束,頗受好評。值此同時,法國電影資料館舉辦的巴索里尼影片回顧展三月初剛剛閉幕,今年初春的巴黎實在非常「巴索里尼」!
擄獲當代年輕人的共鳴
這些年輕導演們在巴索里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被暗殺時,還是少不更事的年紀。自一九九○年起,諾爾德首開先河,在他首演巴索里尼的《風格野獸》Bestia da stile,也是他的成名作時,才二十七歲。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碰到結合政治與詩意的文體,」又說:「我與巴索里尼相遇的震撼,好比上一代與布萊希特相遇的震撼。布萊希特吸引我的興趣,但他所寫的不是我的故事。」接下來,諾爾德陸續首演了巴索里尼的三齣劇作《皮拉德》、《卡爾德隆》Calderón和《豬圈》Porcile。對於自己和巴索里尼的故事,他表示:「所有我做的劇場演出──鍛練正面(frontalité)與口語──都來自於他。他有點像是給我書讀的哥哥,擴大了我的文化修養,塑造了我的世界觀;我對郊區及無居留證人民的支持行動來自於他(註1)。但是,同時,他是一位很可怕的朋友,因為我們不知道在他之後能搬演什麼。」
去年,同為二十九歲的默尼耶與朗貝爾-維勒(Jean Lambert-wild)不約而同地加入諾爾德的行列,完成了帕氏全部劇本的法國首演:前者在傑哈.菲力浦劇場首演了《阿法布拉茲歐》Affabulazione;後者在巴黎山崗國家劇院首演了《狂歡酒席》Orgia。透過朗貝爾-維勒以下的一番話,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巴索里尼對他們這一代導演的意義:「令人驚奇的是:他變成了我們的交集!不管我們是否曾經執導他的劇作,在我們的討論裡,這個交集點超越了美學的區隔。透過他,『我們在公共服務上所採取的態度與行動」成為我們的辯論主題。」
以話語為主的劇場主張
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神秘主義與古代神話傳說充滿興趣,加上他的激情和同性戀傾向,巴索里尼將他的多元藝術創作視為一種戰鬥。人們常常將他貶抑為馬克思、佛洛依德或基督的諂媚者,對於這些簡化的標籤,他始終深感憤慨。在戲劇創作方面,他以詩意的文體,展現其私生活,及自身相對於他人、世界與當代歷史事件的批判關係,其中特別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嚮往與幻滅。他的六篇劇作皆籠罩在悲劇的氣氛當中,在詩意、哲學與政治形成的張力下,充滿了亂倫、詛咒和激烈的情慾。
在一九六八年發表的《新戲劇宣言》裡,巴索里尼提倡一個「話語的劇場」(le théâtre de parole)。對他而言,當時的兩類劇場表演,都該遭到批判:第一類「饒舌的劇場」,比如自然主義及布爾喬亞戲劇,只是喋喋不休,誇張諷刺地模仿當時的生活對話;第二類是「動作與叫喊的劇場」,比如亞陶(編按:主張殘酷劇場理論)、葛羅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編按:主張貧窮劇場)和生活劇場(The Living Theater)(編按:發源於美國紐約外百老匯,由導演Judith Malina 和作家、設計工作者Julian Beck於一九四七年創立,強調集體即興和肢體動作的開放),只是把語言對話簡化為次要的聲音工具。這兩類劇場都有「對語言對話的怨恨」,拒絕神聖化的台詞,和布萊希特的劇場一樣,皆屬於過去式。
在布萊希特的時代,我們可以從內部改革劇場主張;而今,有問題的是劇場本身。就在這樣的精神下,作者主張一個「以話語為主的劇場」,這與基督教福音的語言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重點在於鞏固語言的純粹性;這種表演主張毫無掩飾而純粹的口語行為,沒有任何以動作和表情造成的模仿效果。觀賞這種劇場演出,與其說是看,倒不如說是傾聽。據帕氏所說,這種新劇場訴求「布爾喬亞裡有教養的群眾」,「以寫實主義的方式」,使之觸及「和先進知識分子團結」的工人階級。這也是一種「在腦中,而不是在社會環境中」尋找空間的文化儀式,從而由此對社會大眾提出尖銳的質疑。
古希臘神話的現代省思
《皮拉德》寫於一九六六年作者因為潰瘍發作的住院期間。在這一個月裡,他重讀上古希臘悲劇作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es,525~456B.C.)的作品,尤其是《奧勒斯提亞》Oresteia三部曲,特別為其中第三齣《和善女神》Eumenides所震撼。在此劇中,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設置了第一個仲裁私人紛爭的人類法庭,以審判歐瑞斯特(Oreste)──他為了報殺父(亞格曼農Agamemnon)之仇,手刃了生母(克萊提娜絲查 Clytemnestra)及其情夫(伊吉瑟斯 Egisthes),艾氏在此描述了民主的創造與建立。巴索里尼深受感動,遂著手撰寫《皮拉德》,作為《奧勒斯提亞》的續曲,也是他個人對這則古代神話的現代省思。
《皮拉德》以自由詩體寫成,包括楔子(prologue)與九場科白(épisode),場景分布於山上,革命派陣營、森林中和阿果斯城內的幾個地方:廣場、舊王宮前、國會前、法庭與墓地。開場時,歐瑞斯特被人類法庭無罪釋放,回到故鄉阿果斯,他宣佈自己不是回來當國王的,而是雅典娜派遣的使者。他放棄遺產,意圖改變城裡蒙昧主義的制度;他要求人民成立一個法庭,來決定他是否繼承其父王位,或者讓賢,並委託一起長大的堂兄弟皮拉德,帶領人民邁開民主的第一步。歐瑞斯特的姐姐伊蕾克查(Electra)象徵著大多數人的保守心態,不贊成弟弟的革命行動,依然被復仇女神(les Furies)支配,崇拜「偉大的過去」,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可能。歐瑞斯特被迫與代表過去的勢力結盟,帶領城邦迎接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與歐瑞斯特的選擇相左,皮拉德離開阿果斯,到鄉下去與貧困的農民和工人共同發起以失敗收場的叛變。皮拉德這個角色體現了作者身為知識分子的理念:不相信神聖不可侵犯的秩序,善於提出問題,且不就答案為藉口。
《皮拉德》藉古喻今,說的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年代義大利的歷史:它逐漸脫離法西斯主義的枷鎖,進入六○年代的消費社會時代。在消費社會的時代裡,文化被平均化,個人主義高漲,大眾享樂主義成為新的宗教。舊社會的平衡遭到破壞,農村人口外流到城市的情況嚴重,摧毀了帕氏珍視的農民認同,而換來的不過是一個沒有一點特殊之處的平凡人。作者寫作此劇的時候聲稱,布爾喬亞就像一個傳染病,《皮拉德》儼然是一篇反消費社會的強烈戲劇。
正值探討民主的真諦
在「巴黎─小城劇場」上演的《皮拉德》裡,導演與其「壞種子劇團」(La Compagnie de la Mauvaise Graine)的年輕演員們,成功地分攤角色與闡明文本,使觀眾能夠體會晦澀難懂的作品。此外,導演巧思運用傀儡來扮演代表既定秩序的城邦居民的歌隊,並以手持面具來扮演農民和工人的歌隊。傀儡的造型樸拙,沒有個別特徵,乍看之下,猶如灰黑漂浮的幽靈,但演員們以右手靈巧操縱傀儡的頭,配合左手各種不同的手勢,使傀儡們展現活潑的生命。
本劇導演默尼耶說:「《皮拉德》是一首關於我們的生活、社會及有點日趨衰老,而重新被提出來討論的民主的偉大詩歌。這齣劇不僅連接了民主的基礎本質,也與它現今的狀況有所共鳴。」此時,伊拉克戰事將近平息,這齣「主題劇」(註2)正好激發我們去思索民主與正義的真諦。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註:
1.在巴黎的部分郊區,聚居了許多外國移民和非法偷渡者,因為失業和文化適應不良等問題,年輕人時常發生暴力衝突,並犯下集體強姦的惡行,乃法國社會習稱的「敏感地區」(quartiers sensibles),譬如傑哈.菲力浦劇場座落的巴黎北郊聖德尼區(St. Denis)。
2.主題劇(théâtre à thèse)「闡明哲學、政治或道德論斷,力圖使觀眾信服其根據,同時勸誘他們運用思考能力,勝於運用感情。」( Patrice Pavis, Dictionnaire du théâtre , Dunod, Paris,1996, p.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