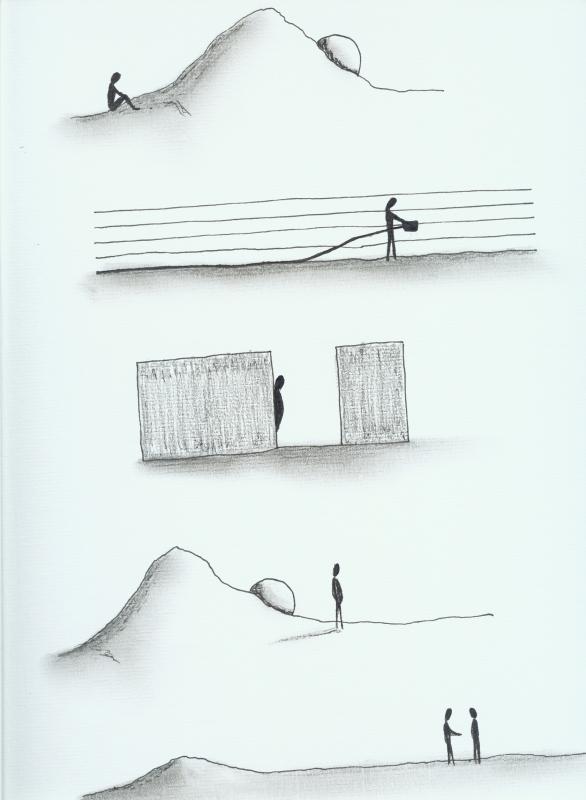「亞洲相遇亞洲」戲劇節從一九九七年創立,持續地進行亞洲各國劇廠工作者的演出交流。今年的第四屆選在東京、台北兩地舉行,台北另名為「亞太小劇場節」,將推出印尼、伊朗、孟加拉等地的前衛劇場演出,並有由日、港、台、越四地劇場工作者合作的《夢難承‧二》,可以讓台灣觀眾看到不同於西方的劇場創意,也讓我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這些地理上接近、文化上卻陌生的亞洲鄰居們。
第四屆「亞洲相遇亞洲」戲劇節的交流,近一、兩個月分別於東京及台北兩個都市舉行。台北更以「亞太小劇場節」為名,讓亞洲表演藝術工作者相遇之餘,除了輪番公演外,還能透過座談會彼此交流。
印尼自立劇團
動盪心弦
這次參與演出的印尼自立(Mandiri)劇團,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導演Putu Wijaya是印尼著名作家和新聞週刊的編輯。他在峇里島(Bali)長大,深受峇里的傳統演藝色彩影響;每次演出時都先拋出爭議性的弔詭(paradox)於觀眾面前,如打開魔瓶,讓怪魔肆虐,動盪心弦至終,演出結束時也沒有給予什麼結論,還是讓結果懸空。筆者曾經看過Wijaya演出新加坡劇作家郭寶崑之《棺材大窟窿》。劇終時,他還是把不合尺寸規格的棺材,懸掛在空中;從那次演出形塑出來的風格,便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他們表演過程關鍵意義。一如《西遊記》故事裡唐三藏一行人找到的是無字天書,這齣戲的爭論還是留給觀者去思索。
在他的作品《戰爭》中,也同樣地,先提出爭議性的問題,以戰爭是達到和平的手段作為演出開場白,然後全面地在舞台上呈現搏鬥影像,宣示戰爭開始。Wijaya從傳統峇里皮影戲的手法褪變為人體與影像搏鬥,皮影幕還因此穿破開來,演員的身體突然從觀眾眼前出現,讓情感性的投射再也不成幻影。殘酷與幻象在兩個國度之間交叉迂迴地走,對比強烈鮮明,對觀眾造成的感官震撼和刺激,至劇終仍是高潮不已。他的作品不僅深具藝術價值,富含當代意義,更是源自亞洲的戲劇傳統。
《戰爭》作品系列是針對九一一事件前後的思索與反省持續發展出來的演出。這次Wijaya特別將新作《和平抑或零度》帶來台北首演。目前世界充滿著仇惡和互相猜疑,戰爭永遠要滅毀和平,到處是血腥、暴力和死亡。什麼正義和真理都與謊言混淆了,大家都覺得絕望地迷失,軟弱無助。劇名暗喻人民不是被征服,便只能垂死,既無方向可尋,若尚可一絲生機,就走回零的國度,從虛無開展,不須任何條件,一切回歸虛無。「零度」不單是虛無也是涵蓋著一切,那裡有著深遠、親切友善、美滿質樸和愛意。成立十二年的自立劇團,其新作仍舊帶著似真似幻的魔幻色彩。
伊朗Bazi劇團
原創反諷
伊朗德克蘭大學的學生罷課,防暴警隊包圍著大學四周,示威與動盪的氣氛,讓人覺得好像處在革命的前夕。伊斯蘭革命衛隊專橫的勢刀早已退減,但政府盲目愚民的行徑已結束了嗎?事實上就在一天晚上,突然又來了一大群無知的亂民流氓闖入大學,把學生毒打不休。在這樣情況下,還能進行任何演出活動嗎?當今伊朗電影聞名於世,誰知曾經有幾位導演拿著影片出門參加國際影展時,當時全被政府充公了。五年前的伊朗雖然解禁,但對藝術家、作家們而言,能享有的自由,僅僅只是在進行思想入罪的伊斯蘭法庭下,打著瞌睡似地被假釋出來而已。
因為美國禁運管制,伊朗經濟破落,保守勢力被迫不得不打瞌睡。不同於廿三年前,柯梅尼革命之前流行的實驗劇,目前伊朗劇場作品都帶有濃烈的黑色幽默和諷刺權威的荒謬。部分創作者開始從事實驗劇場創作,即使伊朗接近歐洲,文化深受西方影響,然而作品的骨子裡都有著原創性和非西方的魅力。
Bazi劇團導演Attila Pessyani是伊朗罕見的前衛小劇場創作者。他的作品都不用對白,而Bazi在波斯語裡是指一種在默劇與幽默喜劇之間的傳統表演風格。筆者看過Pessyani其他的作品如《停止!閉嘴!》Stop!Shut up!,劇中充滿著詩意的悲劇氛圍,還隱約透露難以言傳的悲憤。全劇描繪劇中角色唐哥柯德要挽救阿富汗境內即將被塔里班政權炸毀的大佛,卻成為人質被困;那種受困又無言可辯的張力,一直延伸在戲劇情節裡,還穿插多媒體的影像,喚起我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這齣戲結構出一個指桑罵槐的幻想,對目前的伊朗社會而言,仍是一次冒險的幽默呈現。
這次他們帶來的《夢中的暗啞》The MuteWho was Dreamed在台北、東京兩地公演前,曾於去年在紐約和蘇格蘭公演過,獲得極高的評價。該劇以兩個女性的師徒關係為中心鋪陳,在一個大囚籠中演出。劇中的老師無論透過任何努力或方法,那聾啞的女徒就是不受教;全劇以教育就是被壓迫者唯一的反抗武器,來表達內心深沈的沉默與仇恨。整出戲看起來像是帕洛夫(Pavlov)的制約反應心理學的世界,而囚籠也讓人聯想到這世界總是充斥明顯的規範,活像一個縮影。這究竟是對政教合一制度的控訴?還是革命前夕的一種歷史記錄?仍有待台灣觀眾玩味。
共同合演的實驗
《夢難承.二》
這次「亞洲遇見亞洲」的活動目標之一,在於提供亞洲創作者之間相互觀摩舞台藝術表達語言的機會,所以隔年都會舉辦一次跨國合作演出。第一次嘗試的演出為《夢難承》,二○○○年曾在香港、東京兩地演過。香港的「撞」劇團由源自香港民眾劇社的成員成立,經歷過廿年之久的國際合作演出經驗。日本的DA.M劇團於一九八六年在東京的高馬場成立,延續七○年代早稻田地區小劇場運動的餘波。他們一直嘗試肢體語言的表演方法,較具含蓄抽象的形式,也算是日本當代小劇場運動發展至今的先鋒。
第一齣《夢》劇是以香港與東京兩地人們的焦慮和妄想為主題,企圖誇大一個無邊無際的妄想和惡夢。倘使觀眾能夠理解此劇的內涵,便一如注射了預防未來精神衝擊的疫苗,也許可以算是一種免疫方法吧!「撞」劇團不走「導演論」的路線,而是以演員為主,並且大部分作品都是演員即興演出。他們與日本雖有文化隔閡,但合作過程圓滿,而且彼此都獲得寶貴的實驗劇場交流經驗。
續《夢難承.一》之後,這次在台北和東京演出的《夢難承.二》,加入了由台灣資深劇場評論人王墨林策劃的台灣「新寶島視障劇團」的三位演員。基本上,這是一齣預設好的即興演出;視障人士如何感受其他演員而能互動表演,對參與者而言是個難度頗高的嘗試。「撞」劇團成員湯時康,近來研習了來自美國「行動劇場」(Action Theatre)中的即興表演,這次將要求演員拿出自我壓抑的記憶,走進別人的夢境裡來發揮。
此外,還有來自越南新進前衛藝術團體「新時代」(The New Age Group)之一名演員參加演出,這齣戲可謂日、港、台、越的聯合之夢,希望藉此經驗擴展為亞洲的夢,尋找當代實驗劇場表達的共鳴,更冀望未來能有更多國家參與這樣的合演。
孟加拉亞洲演劇中心
實驗傳統
顛覆史詩的創新演出《裂股》Urubhangam,由來自孟加拉的亞洲演劇中心(Centre for Asian theatre)演出,《裂股》一劇原指來自南亞洲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最後戰爭的一章。一直以來,梵劇都有既定的感情表現方式,觀劇者也能透過文化符號而跡可循,然而該劇卻一反經典的規條。比如梵劇中的悲愁、憤怒和壯奮,便必須對應既有的演出格調:憐憫、激烈和英勇。傳統表現戰事的方法多用對白交代,但《裂股》導演K.Nilu為道出反戰的意念,則直接展示激烈的戰爭場面,試圖強調戰爭摧毀文明。
Nilu使用的肢體表現、雜技與舞蹈等等,完全充滿南亞洲的動作色彩,也運用許多現代的技巧。這樣的實驗與亞洲各界當代的戲劇創作者類似,從傳統裡尋找適合的表演元素,並朝前衛邁進。該劇團是孟加拉唯一定期推出作品的劇團,在過去悠久的表演歷史中,他們也曾演過毛澤東時代的樣板戲,可見Nilu是大膽的實驗劇場創作者,他尤其對京劇雜耍極感興趣,又嘗試融合南亞色彩的動作,這更是「傳統遇見前衛」的奇觀了。
部分在東京參與「亞洲遇見亞洲」的戲劇團體,這次無法赴台北參加演出,如來自伊拉克之NAAS劇團。東京的主辦者早在戰爭之前便聯絡到這群伊拉克的劇場工作者,當時有一部分在伊拉克境內,另外一部分人主要流亡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開戰前後那段時間,他們有的跑回家園或被迫逃難,失去聯絡,於是在柏林的戲劇理論學者與戲劇統籌El Amari,為這次在東京舉行的「亞洲遇見亞洲」,集結她流亡歐洲的戲劇工作同胞,一同前來日本。
可以想見這段過程,與我們在電視畫面上所見的「真實」完全不同,也許現代人的悲喜感都受到電子媒體的操縱。他們在東京演出的作品《伊拉克的形象》,描述兩位女性以電子郵件交談,空襲來時通訊系統故障,眾多影像重疊,穿插似幻似真的新聞片段,反映著諸多歷史仇怨,呈現一齣超現實的悲喜劇。導演以阿拉伯的音樂節奏和多媒體畫面傳達被戰火蹂躣的心靈感受。E-Amari是研究布萊希特(Brecht)與阿拉伯戲劇創作關係的學者,我們不要忘記布萊希特當年深受中國京劇影響,可見得藝術形式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融匯。此次參加東京演出的日本劇團有於一九八四年組成的「流山兒」事務所(編按)。他們曾在世界廿幾個都市巡迴演出,一直偏好詮釋日本戲劇鬼才寺山修司的作品,並以人體模仿木偶的形式表演。其他還有OM-2和「吸血蟲組合」劇團;前者非常前衛,每年舉行Mental Shocking Collection的同類劇團戲劇節,後者常以生理與生物的符號創作,來指涉社會階級的矛盾。
文字|駱竟才 日本「亞洲相遇亞洲」演劇節執行委員
編按:該團曾在二○○二年十月間,由導演流山兒祥領銜來台於台北青少年育樂中心演出寺山修司作品《玩偶之家》。
「亞洲遇見亞洲」的策展思考
駱竟才(日本「亞洲相遇亞洲」演劇節執行委員)
「亞洲相遇亞洲」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舉辦,其中目標不僅在於交流演出,更希望共同尋找出創新舞台表演的可能性;透過座談討論和跨文化合作表演,研探屬於當代亞洲人的劇場藝術。我們的傳統都是寶藏,可以提煉出嶄新的戲劇智慧。六、七○年代肢體劇場的開山祖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與知名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等人都跑過中國、峇里島與印度等地以研究舞台表演的身體語言。與西方戲劇傳統大異其趣的是,亞洲的戲劇傳統在於必須透過特定的社會文化意涵與符號來觀賞特定區域的表演,直觀感受抽象的信息;但是西方表演則講求真實自然(naturalistic)的佈景、場景(proxemics)和服裝等等,賦予故事情節完整的時空,以便角色發展性格。
期待結合社會脈動
去年夏天,我們邀請了一些來自東南亞的年輕劇場工作者來東京進行工作坊和合作演出,稱之為「轉碼」(Code Switching)。那次實驗的嘗試是把亞洲社會中既有的舞台身體符號,互相移花接木地混合來,雖然效果不算成功,但我們有意繼續這樣的實驗。
筆者本來是香港民眾劇社的一員,八○年代初開始長居東京,當時接觸到的日本戲劇界正經歷著「後激進化」(post-radicatism)的轉換期,日本創作逐漸不像過去六、七○年代對社會時代那般地關切。在無法找到抱持共識的夥伴團體下,筆者埋首於比較文化的學術研究與國際時事的採訪工作裡,直到六年前,開始策劃「亞洲相遇亞洲」,才又回到劇場。
亞洲劇團的作品主題,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與當代社會的脈動結合。筆者去年與菲律賓的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劇團成員合作過,他們的作品具有鮮明的諷刺和激勵觀眾的色彩,對日本觀眾而言相當新鮮。
開放與中亞國家合作機會
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合演作品,多半是以日本作品和導演為主,加上來自亞洲、甚至歐洲的演員。我們的策展目的務求對等地達到相互對照的融合(inter-contextual syntheris),這必須以彼此了解的文化背景為基礎。目前東南亞國家彼此的交通還算緊密,然而我們的鄰邦卻不一定有即時合作的條件;比如筆者一直希望能到斯里蘭卡。因為內戰,斯里蘭卡的劇團多年難以公演,中斷了他們實驗戲劇的發展;唯有靠鄰邦同行的互相鼓勵和支持,才能彼此探求亞洲藝術的當代性。筆者也走訪過伊朗的戲劇環境,深感開放與遠方亞洲各國接觸和合作機會的重要;伊朗正處於政教合一的政權開始崩潰的關鍵時刻,他們的實驗劇場演出充滿了那些可貴的情懷,若有更多同行能以交流經驗作為支援,更臻其美。
數月前,筆者走訪過越南河內市,因為首都之故,聚集了不少國立演藝、電影與舞蹈學院。在河內年初舉辦的第一次國際實驗戲劇節裡,我遇見一群越南國內唯一的前衛藝術家。他們雖然唸過蘇聯式的五年制學院,卻在官方體制之外,全憑自己摸索發展當代藝術。正如柏林圍牆崩塌後,西方的專業工會人士都會越境到東歐援助同行;我們在鄰邦尚有很多事可以做。亞洲其他國家如台灣,其實也具有鼓吹當代文化發展的條件和優越的文化地位,希望台灣的藝術行政者能從「亞洲遇見亞洲」找到一些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