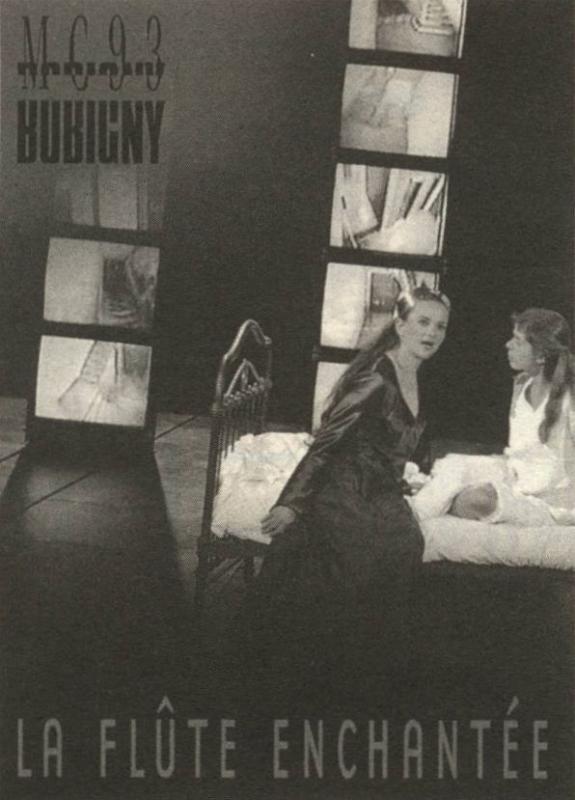因為蒂艾寫《爸爸得吃飯》時,並未考慮到表演層面,所以此劇形式違反傳統,其中既無舞台指示,亦無時間及特殊意圖,反而有一種從容灑脫;她以輕巧的方式來指涉事物──或者不指涉一切。在內容方面,除了惹內(Genet)與戈爾德思的劇作之外(譬如前者的《黑人》和後者的《黑人與狗的爭鬥》),這齣戲以非常大膽的方式來討論種族歧視,這在當代歐洲戲劇中極為罕見。
我認為導演搬演太多「定目劇」了。一個導演如果在六齣莎士比亞或契訶夫或馬希沃或布萊希特的戲劇中搬演一齣當今的劇作,便自以為壯烈。一百或兩百歲的作者不可能說今天的故事,我們總是以為可以找到相當的東西﹔但是不,我不相信麗塞特與阿爾勒蓋的愛情故事是當代的(註1)。現在,愛情以別樣的方式被訴說,因此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作者今天動手寫十八世紀時僕人與伯爵夫人在城堡裡的故事,人們會怎麼說?──我是第一個仰慕契訶夫、莎士比亞與馬希沃,並努力從中吸取教訓的人。然而,即使我們的時代沒有這等素質的作者,我認為與其上演十齣莎劇,寧可演出一齣有缺陷的當代劇作。
莫札特有價值,我們繼續聆聽他的音樂,這沒問題;儘管如此,還有更多的人聽比莉.哈樂黛或馬文.蓋或麥可.傑克森,這個更好。聰明人不會把他們拿來相提並論,而說當今不再有莫札特,並覺得靈魂樂可鄙。
沒有人──尤其是導演──有權說沒有作者,當然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一方面沒有人搬演他們的作品,而能在好條件下被拿來演出更被視為聞所未聞的運氣,這還算是枝微末節的問題。如果我們一點都不要求他們,不盡量汲取他們所作中最好的部分,你要作者怎麼變好?。當代的作者和當代的導演一樣重要。
~~戈爾德思 (註2)
法國非洲裔女作家瑪莉.蒂艾(Marie NDiaye )在眾所矚目下,以劇作《爸爸得吃飯》(Papa doit manger,2003),成為聲譽卓著的莫里哀之家──國立法蘭西劇院(La Comédie-Française)──成立三百廿三年來第一位進入其保留劇目的在世女性劇作家。此劇從今年二月下旬到六月下旬止,在金碧輝煌的黎希留廳(Salle Richelieu)舉行世界首演,由安德烈.恩格爾(André Engel)執導,筆觸細膩的劇本與出色的舞台演出令觀者有口皆碑,劇評亦一致讚許,明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將重新上演。
異乎尋常的成熟風格
蒂艾與小說家丈夫及三個小孩住在遠離巴黎塵囂的法國西南部鄉村裡,經營著村裡的舊咖啡館──也是間電影院。對於此劇的成功,她帶著安靜與神祕的喜悅,表達她的驚訝:「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故事。我在想為什麼法國人現在搬演《爸爸得吃飯》﹖為什麼演這個劇本?」(註3)
生於一九六七年的蒂艾,父親是塞內加爾人,母親是法國人(註4),當母親與突然消失的父親離異時,她還未滿足歲。她跟隨著當教師的母親度過童年,遷徙於法國外省各地及巴黎郊區 ──「那些沒有人會注意和沒錢生活在巴黎的人定居的地方」(註5),《爸爸得吃飯》的故事充滿了作者的自傳色彩。她在巴黎索邦大學學習語言學,並獲得法蘭西學院的公費,到羅馬的梅第西斯別墅當了一年的寄宿生。十八歲時,「子夜」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篇小說《關於富裕的未來》(Quant au riche avenir ,1985),其異乎尋常的成熟風格普獲讚賞。兩年之後,在小說《古典喜劇》Comédie classique裡,她一個句子就寫了一百頁;接下來的五本小說,複雜度不斷增加,越來越直接地對抗世界無法接受的奇特古怪,其中的最後一篇《粉紅色鯉魚》Rosie Carpe 榮獲二○○一年法國著名的費明娜文學獎(prix Fémina)。
五年前,蒂艾對小說感到厭煩,開始嘗試其他寫作形式,應法國文化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之邀創作了第一篇劇本《伊爾達》Hilda,去年由導演貝立耶-加西亞(Frédéric Bélier-Garcia)在工作室劇場(Théâtre de l'Atelier)搬上舞台。《爸爸得吃飯》是她的第二篇劇本,作者自稱「寫了一篇以對話為形式的小說」,原題為《不理智的愛》Un amour déraisonnable,一九九八年在法國文化廣播電台頻道被朗讀。去年國立法蘭西劇院新任行政總監伯洲內(Marcel Bozonnet)邀請導演恩格爾首演一齣當代作品,恩格爾正好聽見此劇的重播,進而發生興趣,爾後蒂艾開始修改劇本,她認為廣播劇版本「有太多冗句」,便將它壓縮,保留角色與場景,改劇名為《爸爸得吃飯》。她說﹕「我花了一年的時間讀劇本,才學到這點:如果有一件無法忍受的事,便是饒舌,用許多話來說平常的事。小說可以滔滔不絕地運載它們,但劇本不行。我的工作在於大量簡化,而不陷入莊嚴呆板、充滿累贅意義的句子中。小說可以離題、閒逛、迷一點路,但劇本不行,因為它一點都不像真實生活。在劇場裡真實生活是膚淺又惡劣的,你不覺得嗎?」
大膽討論種族歧視
長久以來,蒂艾自認為過於無知而不願談論戲劇。如今她接受在自己的作品題上「戲劇」二字,但始終認為寫作舞台指示不屬於她的工作範疇。她也開始到劇場看戲,而且樂在其中。如今這位劇作家閱讀的劇本幾乎和小說一樣多,契訶夫、易卜生、戈爾德思與拉高斯(Lagarce)的劇作皆在她無止境的家庭藏書之列。
因為蒂艾寫《爸爸得吃飯》時,並未考慮到表演層面,所以此劇形式違反傳統,其中既無舞台指示,亦無時間及特殊意圖,反而有一種從容灑脫;她以輕巧的方式來指涉事物──或者不指涉一切。在內容方面,除了惹內(Genet)與戈爾德思的劇作之外(譬如前者的《黑人》和後者的《黑人與狗的爭鬥》),這齣戲以非常大膽的方式來討論種族歧視,這在當代歐洲戲劇中極為罕見。
本劇共分為十一景,開場時,十年前無緣無故拋棄白人妻子和兩個女兒的黑人爸爸突然浪子回頭返家,輕敲庫賀貝瓦(Courbevoie)低租金住房(HLM)的房門,向開門的女兒米娜(Mina)說﹕「是我,我的鳥兒。是我。爸爸回來了。」(註6)爸爸來自非洲,他說﹕「爸爸的皮膚黑到人類膚色最黑的程度,無與倫比、閃閃發光,使得我深色的眼睛好像褪了色一般。孩子,從現在起,妳得知道:我皮膚完全且蠻橫的顏色,使我比像妳那無光澤的皮膚強。」(11)他身著嶄新的服裝,口袋裝滿了鈔票,向女兒遞上手裡的禮物:「在戴高樂機場的免稅商店買的果醬。」(21)並笑著說﹕「我驕傲、快樂、富裕地回來了,如此驕傲,如此快樂,如此有錢。」(12)爸爸要求家人接待、承認並疼愛他,聲稱要給予他的家另一個生活,將它搬離貧民區。事實上,爸爸是個騙子。他是個窮光蛋,從未旅行過,從未離開過庫賀貝瓦,漂亮的服裝是向人借的,許下的承諾全是空話,現在正與另一個女人同居,倆人有一個不久便夭折的嬰兒。
不顧雙親與姑母們的勸阻,只是個小理髮師的媽媽本能地向回返的爸爸回應她的熱情,她說:「為他所受的苦使我終生與他結合。」(55)她把全部積蓄悉數給予爸爸,帶領孩子跟隨他去,當謊言揭穿時,她以預藏的刀子毀了爸爸發光的容顏,之後正式離婚,和任職中學文學教師的同居人澤爾納(Zelner)結婚。廿年後,長大成家的米娜拒絕付給爸爸贍養費,但……爸爸得吃飯。最後一景裡,被毀容的老流浪漢爸爸,在電梯門口與正趕往參加丈夫火葬的媽媽重逢,向她表露情感:「我不曾好過,不曾忠誠過。我的皮膚是奇妙的黑色,但對某些人來說,是種侮辱,而且不能接受。即使它沒虧待我,我也從未感謝過法國。然而,我在這裡,活生生的,對妳有著特別的溫柔。對我來說,我不是只結了一次婚嗎?」(94-95)媽媽急著離開,但歷盡滄桑之後,仍感情無法抑遏地說道:「我在服喪,但……我對你永遠都有……是的……有一股無法解釋的愛。」(95)本劇即結束於這番無關理性、道德,而直接出於本能的愛情告白中。
人物殘酷、逾越常態
《爸爸得吃飯》裡的人物殘酷,逾越常態,介於真實與惡夢、日常與歷史、家庭神話與政治神話之間。全劇探討拋棄與愛情,社會階級與種族,法國與非洲的關係(註7)。爸爸說﹕「十到十五年前,女兒,我為了報仇而來到法國。我在憤怒、挫折、軟弱與奴役的感覺中來到這裡,對我自己說﹕我報復所有抑制的狂怒、痛苦與這種難以形容的恥辱。全法國要償還──我要它收回說過的話。」(62~63)因此他離開了白人妻子,以體現其報復行動。
屬於白人布爾喬亞階級的澤爾納對於爸爸的情緒則極為矛盾:「我認為我們沒有權利怨恨他。所有違背他的怨恨,我覺得,從政治角度上都該被譴責。……沒有所謂的黑人,只有傷口,我覺得。只有悲歌,只有可恥的奴役。……我該向他說,現在他對我而言,是一個真實又完美的人物。我該向他說,我恨他、蔑視他到最高點。」(65~67)至於保守的克萊蒙絲姑母向媽媽說:「妳女兒的膚色滿淺的,她們真是好運。大家都這麼想,我可沒說什麼。」(56) 則充分表現了白人的優越感與霸權。
蒂艾用她幽默且清醒的聲音向我們低聲訴說危險、痛苦的盤繞,其驚人的語言不但詩意、風雅,而且濃密、溫柔又銳利,以簡短的敘事結構支撐著這個當代悲劇蘊含的可能奧秘(註8)。導演恩格爾避開自然主義的詮釋,強調劇本的曖昧與複雜(註9)。他與長期合作的佈景設計師希埃提(Nicky Rieti)參考了哈潑(Edward Hopper)的圖畫,以風格化、繪畫的方式構思了庫賀貝瓦低租金住房二樓的世界,同時也顧及爸爸這個角色,透過佈景發揮其敏捷及虛張聲勢的精湛技巧。
非洲爸爸由名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旗下非洲演員杉加黑(Bakary Sangaré)飾演,這是他在成為法蘭西劇院第一位領固定薪酬的黑人演員(pensionnaire)下初試啼聲之作。他細細品味作者筆下的台詞,扮演了一個迷人、奇特、充滿威嚴的騙子爸爸。法國的黑人演員經常埋怨他們的角色很少(註10),劇中這位厚顏無恥的爸爸彷彿是為杉加黑量身訂作的角色,其他演員的表現也相得益彰。
有人抨擊劇作裡的黑人角色過於兇惡,蒂艾解釋道:「這只是一個人。我無須為黑人塑造一個善良、和藹的形象,這是一個『完全的人』,無須描繪人們所期待的黑人形象,這不合情理。爸爸只代表爸爸而已。」法國過去殖民非洲時極盡剝削與掠奪之能事,現在卻坐視其被愛滋病折磨,《爸爸得吃飯》恰為二者關係的寓言。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註﹕
1.在法國十八世紀名劇作家馬希沃(Marivaux)的代表作《愛情機緣遊戲》( 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1730 )裡,女僕麗塞特(Lisette)與男僕阿爾勒蓋(Arlequin)相戀。
2. Bernard-Marie Koltès, " Un hangar,à l'ouest ", l'annexe de Roberto Zucco , Minuit, Paris, 1990, pp. 124-125.
3. Jean-Louis Perrier, " La maison de Molière réveillée par Marie NDiaye ", Le Monde , le 22 février 2003.
4. " Papa doit manger ", Programme de la Comédie-Française, Saison 2002-2003.
5. Michèle Venard, " Marie NDiaye -《Hilda》", Théâtres, n。1, janv. / févr. 2002, p.48.
6. Marie NDiaye, Papa doit manger , Editions de Minuit, 2003, p.9. 後續的劇本引言直接以括號註明原始出處的頁數。
7. René Solis, " Artifices à 《Papa》- un beau texte de Marie NDiaye à la Comédie Française", Libération, le 1er mars 2003.
8. Fabienne Pascaud, " T'es plus dans l'coup, papa", Télérama, n。2773, du 8 au 14 mars 2003.
9. Propos recueillis par Fabienne Darge, " Entretien avec André Angel, metteur en scène de 《Papa doit manger》", Le Monde , le 22 février 2003.
10. Propos recueillis par Jean-Luc Eyguesier, " Entretien avec Issach De Bankolé ", Magazine littéraire, n。395, numéro spécial : “ Bernard-Marie Koltès “, février 2001,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