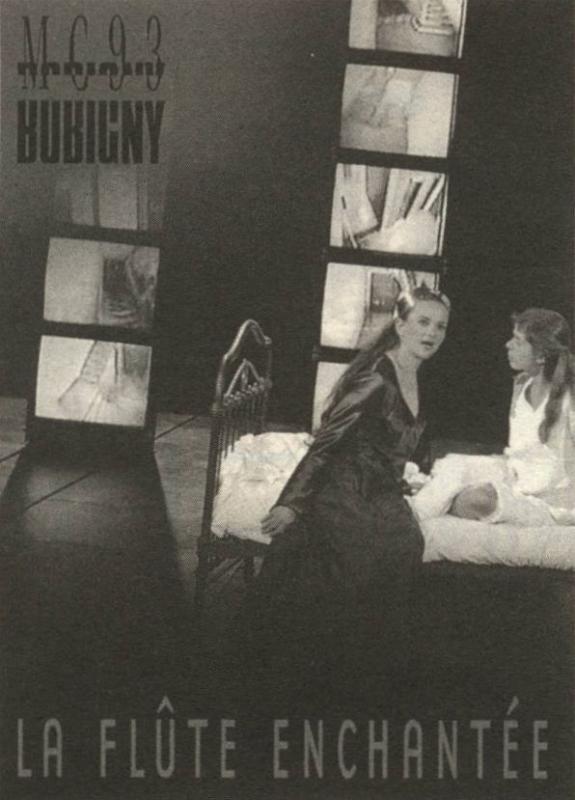觀賞胡塞爾的舞台作品,不免使人聯想亞陶畢生所追求的一種獨立於言語之外的具體、物質化舞台表演語彙,一種先行訴諸觀衆五官的舞台語言,熔音樂、舞蹈、戲劇與多媒體為一爐,表演意象強而有力,演員精力迸射,全場演出爆發驚人的能量。
「對我而言,文學的文本出奇地重要。文本由現實的凝聚與濃縮架構而成,爲一種可觸摸的現實。這是一種應該爆發的能量,而非劇場的根基。文本既非一種刺激,亦非一種靈感,這是一個搭檔……對於文本,我比任何人都還要忠實,因爲我視文本爲涵意的總和,可是表達的狀況是我創造的,根據我個人藝術意識進展的階段。」
──T. Kantor(註1)
千禧年四月,當巴黎劇場受春假悠閒氣氛之感染而顯得有點動力不足時,來自比利時名不見經傳的「烏托邦」劇團(Compagnie Utopia),在北郊的「熱納維利爾劇院」(Théâtre de Gennevilliers)帶來創團的三齣力作──《安葬死者/拯救生者》(改編自契訶夫之名劇《普拉托諾夫》)、《侯貝多.如戈》(戈爾德思著)以及《歐洲人》(豪爾德.貝克著),這三齣戲不僅演得熱烈異常且意蘊豐富,更重要的是活力四射,讓觀衆看得血脈賁張,內心澎湃激動,終場彷彿經歷一場淨化的儀式,身心舒暢無比。這類型高熱量的文學劇場近來在法國甚少得見,這也就難怪巴黎的劇評家會大加推薦,而現場觀衆不管同不同意導演的詮釋觀點,劇終也不得不爲演員熱情奔放的一流演技忘情地鼓掌。
導演阿梅爾.胡塞爾(Armel Roussel)可以想像的,是個年輕的小伙子。他由於不滿法國劇埸側重文學詮釋的傳統而跑到比利時求發展,今年才三十出頭。可是就舞台表演語彙之掌握以及劇本分析的能力而言,胡塞爾的表現完全不輸成名的大導演;那種完全駕馭舞台演出因而顯得胸有成竹的氣勢,是剛出道的導演所少有的。這點想必是巴黎劇評家對他另眼相看的主因。
胡塞爾導起戲來絕不墨守成規以外,更是個能用大腦思考的導演。他所挑的三齣劇本無一不是現代經典之作,而且契訶夫是廿世紀下半葉歐陸劇場的最愛,戈爾德思爲近十年來最熱門的法國劇作家。面對這兩位廣受歡迎的作家,後起的導演首先必須面臨的難題是如何突破前人之作。而貝克的名聲在歐陸或許不如前二者響亮,不過他的劇作側重歷史深度之際並同時觀照當代世局,絕非容易處理的劇本。
創團之始即敢挑戰受歡迎、高難度的現代經典,並勇於提出新詮,更能以戲劇表演特有的媒介先行訴諸觀衆的感官,藉以與一般閱讀劇本之知性活動作區別,胡塞爾不僅能讀更能導。爲了淋漓盡致地表達個人讀劇的觀感,他不惜改編、濃縮劇本,並擅用多媒體,極力刺激演員用身體直接表達他們對劇中人的各種幻想,他的舞台演出因此總是瀕臨瘋狂的邊緣,爆破力驚人。
以契訶夫之作爲例,衆人皆知,契訶夫的劇作向來被視爲日常人生的寫照,乍看之下無聊、消極,角色缺乏生命的動力。《普拉托諾夫》爲作者十九歲時的處女作,從胡塞爾的視角觀之,本劇透露的是少年契訶夫滿腔改革熱情受阻,以至於對人生幻滅的劇烈過程。主角普拉托諾夫雖有奮鬥的想望,一股壓不下去的慾望卻在他體内蠢蠢欲動使他日夜難安,可是周圍的環境卻處處掣肘,讓他經常感到無奈與無力。
這兩股相互對抗的勢力造成劇情猛烈動盪的活力與張力,胡塞爾由此點切入劇情,濃縮、改編、甚至於改寫台詞,大量借助馬戲、音樂與舞蹈,將主角本能的衝動、慾望以及狂放的性幻想一一呈現於觀衆眼前,其他角色亦皆爲求生的慾望所逼,個個顯得激昂與瘋狂,全場演出迸射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的生猛精力,與一般契劇缺乏活力的演出情境大異其趣。
胡塞爾更在舞台上公然爲契訶夫的演出傳統致哀:導演在舞台右前方供著一張作者遺照,前面點了一根白蠟燭。看似破壞偶像的(iconoclastic)顚覆性演出,其表演邏輯實際上是出奇地緊密,環環相扣,高潮迭起,讓人看了還想再看。
然而胡塞爾絕非便宜行事的導演,更非一位隨意竄改作者的心血結晶以滿足自己創作慾的導演。他所導的《侯貝多.如戈》,僅在表演的場次順序上小作更動,其餘不僅完全按照原文一字不易地演出,且在表演的過程中處處突出劇文的絕對重要性,結果依然震撼人心。
凸出劇文的絶對重要性
侯貝多.如戈爲一無動機殺人狂,戈爾德思採戲劇表現主義編排場景的手段,以十五個主角歇腳的人生旅站,鋪排主角越獄、弑母、逃亡、「強暴」少女(一名「小女生」)、暗殺警探、劫持人質(公園中的一名「太太」)、濫殺無辜、被捕、以及最後從監獄屋頂墜樓喪生的人生行程,劇情支線交待兩個家庭──「小女生」以及「太太」兩家人──解體的過程。本劇雖以眞人眞事爲本,劇情初看在於暴露現代都會的暴力問題,實則藉由種種象徵譬喻,探究當代人生的困境。戈爾德思並於劇中大量旁徵博引,特別是古波斯太陽神密特拉(Mithra)的崇拜儀式,全劇因而遠遠超出社會寫實劇的規制。
於深刻的主題之外,戈爾德思劇作之所以能在作者謝世後的數年間迅速成爲歐陸劇場的常演劇目,乃在於他獨出機抒的文風,這是一種宛如街頭巷語但其實典雅有致的古典語言,個人色彩濃烈。
胡塞爾即以戈爾德思的劇文作爲全場演出的重頭戲,因此他幾乎從頭到尾皆讓演員面對觀衆直抒胸臆。如此一來,劇中人的言談困境首先得以暴露無遺;他們表面上看來有問必答,交往密切,實則各說各話,一種基於無法溝通而衍生的孤寂感瀰漫全場演出。孤單、寂寞、溝通困難是戈爾德思戲劇的基調。
更重要的是,由於正面表演,戈爾德思文字稠密的對白得以充分展現其絕對重要性。誠如法國當代另一重量級的劇作家維納韋爾(M.Vinaver)所言:於戈爾德思的字句之間,形式與內容合而爲一,各式情感、念頭、轉瞬即逝的衝動、以及大可擴及宇宙的主題採獨特的方式發展,故事、人物、時空全由對白的字裡行間透露(註2)。
以戈爾德思的劇文爲主,胡塞爾扣緊劇文的神話、幻想與寓言層面發展表演的意象,透過主角人物的活力與能量,探討現代社會的問題與人生困境。
一個處處有牆的世界
出乎所有觀衆的意料之外,全戲以第六景〈地下鐵車站〉開場。事實上,觀衆仍在陸續進場之際,一名挺個大圓肚子、裝扮成一位老先生的演員(V. Minne飾)已在台上走來走去,並好奇地張望現場的觀衆。
由巴索爾斯(M. V. Bassols)設計的舞台,其前景正中爲一道巨大的鐵格柵欄所擋。視演出需要,這道柵欄可分左右兩邊拉開以空出舞台中央的區位,但此時柵欄仍位於舞台左右兩側的前方位置,並未全然消失不見。因此於演出過程裡,觀衆等於是透過鐵格柵欄看戲。這道鐵柵欄具體點出禁錮世界的主要表演論述:正如男主角墜樓前所言,我們居住的世界是一個牆外有牆、處處碰到阻礙的世界(註3)。
柵欄之後的舞台全空,只有四部閉路電視分置台上地面四個角落,另有兩部電視懸吊於舞台視框之外左、右兩側高處。此外,舞台的最後方爲一片落地的投影大銀幕所圍。閉路電視與投影螢幕的設置皆在於建構一個媒體社會的表演意象。
正戲開演,觀衆才知台上的「老先生」是第六景中那位半夜在彷彿迷宮般的地下鐵車站迷路的老頭,他腳步慢半拍,一不留神被柵欄擋住出口:「嘩啦一聲,我這會兒就在世界以外,在這個不是時候的時候,在這種奇怪的光線下面」(189)。此時從暗地裡冒出來的殺人通緝要犯如戈(E. Castex飾)身材壯碩,面無表情,卻諷刺地被心慌的老頭視爲救星。兩人接著在看似於夜半的地下車站交心,實則各自面對觀衆自我表述:老先生自此領悟到:「年青人,每個人都有可能出軌」,「隨時隨地」(189),而殺父弑母的如戈則希望自己「變得和玻璃一樣透明」,「別人的眼光穿透你的身體看到你身後站的人,好像你人不在那裡似的」(188)。他渴望變成「一節安安靜靜穿過田野的火車,什麼都沒辦法讓車子出軌」(189)。
立於高大的鐵柵欄之後等著第一班地鐵進站,老先生與如戈實爲人生道上的迷途者,而白天的正常世界已明白將二人隔除在外。以這場迷途/出軌之戲開場,導演開門見山地指出全劇的主題所在。
媒體、影像與社會
〈地下鐵車站〉一景過後接著上演的才是原劇的開場戲〈越獄〉,其處理手法亦頗出人意料。因爲本場戲裡於深夜時分巡邏的兩名獄警從頭到尾都未在陰暗的舞台上露面,觀衆是從舞台兩側高懸的閉路電視看到這兩名獄警的嘴臉。且由於影音視訊經過電腦處理,角色的面貌已不復辨認,而只見影像的五官動作被誇張處理,演員的聲音同時變得失眞、滑稽,配上粉藍的色調,造成一種有如卡通的喜劇效果,這與此時由於陰暗而顯得危機重重的舞台氣氛成一強烈的對比。
這兩名獄警於夜半巡邏無聊至極的時分,因爲忘情地辯論人到底是用耳朵或者是用念頭聽到外面的動靜,而眼睜睜地看著由於謀殺生父罪嫌遭到囚禁的如戈從容地逃離監獄。這場開場戲原就是於緊張時刻流露荒謬的況味,尤其是當獄警乙說起:「人家跟我說殺人的本能是安頓在屌上頭」,而他已趁監視犯人洗澡之便,仔細觀察過六百個以上的屌,結論是這六百個「有大的、小的、有細的、有非常小的、有圓的、有尖的、有超大的,可是從這中間得不出半點結論」(169)。
胡塞爾以只具輪廓、快節奏、機械的閉路影像處理本場戲不僅讓人耳目一新,且契合戲劇狀況。嶄新的表演手段從戲一開演即能吸引所有觀衆的注意力,進而激發觀衆於未及逆料的表演狀況裡更專注於欣賞演出的過程。在此同時,閉路電視的影像雖節奏明快,畢竟變化有限,觀衆不一會兒即轉而注意聆聽比機械化影像更有意思的對白,因此等於是同時強調劇文的重要性,而未產生喧賓奪主的缺點,十分難得。
在後續的戲裡,胡塞爾更三度於背景大螢幕上播放黑白錄影影像。首先是第四景〈便衣警探的憂鬱〉,一名警探向妓院的老鴇抱怨自己連日來莫名的苦悶。他出門後,如戈尾隨其後。緊接著,背景螢幕播放一名嚇壞的妓女正面向著觀衆(老鴇)描述如戈刺殺警探的過程:「他(如戈)跟在探長的後面走,探長好像陷入深思裡;他跟在探長後面走活像探長的影子一樣;然後影子又像中午的太陽越縮越小,他就越走越靠近探長彎曲的背後,接下來很快地,他從衣服的口袋裡掏出一把刀子插進那個可憐的探長背上。探長停下來。他沒有回身。他輕輕地搖頭晃腦,好像他的沈思剛剛才找到解答似的。然後他全身搖晃,倒在地上」(184)。
稍後第九景〈大利拉〉更全景透過錄影演出:如戈的小情人「小女生」,如同舊約聖經中出賣大力士參孫的大利拉,在警局作證指認如戈,後者的身分因而曝光,立時成爲全國追緝的要犯。胡塞爾以小女生臉部被警察威脅修理的特寫鏡頭直指暴力之存在,而且小女生的臉部成爲影像焦點所在,更能將觀衆的注意力聚焦於戈爾德思亦莊亦諧的劇文上(註4)。
第十二景〈火車站〉以火車奔駛於鐵軌上的影像意示這場戲的背景,遭到通緝的如戈在這場戲裡瀕臨崩潰的邊緣,來來往往的乘客在他眼裡全是殺手的化身。「看這些瘋子。瞧他們不懷好意的樣子。這些人都是殺手……他們的腦袋只要收到一個最小的信號就會大開殺戒」(226)。這是全戲唯一以實景錄影交待劇情發生所在的場景,作用在於凸顯開場戲裡提及之人生軌道的表演論述,而且放大的火車奔馳影像生動地塑造本場戲裡心靈幻象的空間。
以上利用錄影影像烘襯精練的劇文,或強調重要的表演意象,同時也點出了媒體、影像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是其他執導本劇的導演不免大加發揮之處(註5),胡塞爾則未直接觸及,而是旁敲側擊。例如四部置於舞台地面上的閉路電視,於全場演出中固定播出彩色切分成廿四小格之分割畫面,色彩亮麗,但畫面轉換甚緩,畫面的內容(大自然與昆蟲的生態)與演出無直接關係,卻無時無刻不在,胡塞爾似以此暗示存在於現代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媒體與影像。
另一方面,胡塞爾引用不少媒體或刻板人物形象:第十景中兒子遭如戈劫持的「太太」(F. Marcq飾)仿瑪麗蓮夢露的造型亮相;「小女生」(S. Delcart飾)胖嘟嘟的臉龐與圓圓的身材宛如一個長大的洋娃娃;頭戴一頂呢帽、身著一襲黑色風衣,本戲中的警探吻合電影私家偵探的刻板形象;將自己妹妹「小女生」賣到妓院的「哥哥」(K. Barras飾)打扮如色情雜誌裡的人妖;「姊姊」(A. Delatour飾)一襲黑色皮衣下穿的是妓女的行頭;上文已述在地下鐵車站迷路的「老先生」與小丑相距不遠,等等。舞台上這些眼熟的身影,明白地點出現代生活環境中各式媒體影像充塞的景況。事實上,眞實社會裡的主角──義大利的Roberto Succo──正是我們媒體化社會的犠牲品(註6)。
發揚肉身劇場的震撼力
在邁向導演的路上,胡塞爾深受原籍伊朗的美國導演雷查.阿布多(Reza Abdoh)影響。簡言之,阿布多的劇場深入挖掘肉身軀體的表演潛力與張力,他的演員常在台上公然穿脫,演員熱切的身體,比起台詞,更能表達角色内在的驅力與騷動。阿布多喜挑戰常人對軀體、性別、扮裝與慾望的既定概念,因此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在他的作品中司空見慣。胡塞爾深受啓發,也大力刺激自己年輕的演員與台詞建立一種肉身的關係,盡情開發自己對台詞的各式幻想。而年輕的演員爲狂熱的情緒與慾望所激發往往不惜自我暴露,大膽赤身露體表達最深層的內在騷動(註7)。
於《侯貝多.如戈》一戲中,兩場裸戲均處理得劇力萬鈞。其一是居全劇正中的樞紐場景〈就在臨死之前〉:苦悶的如戈在一家酒吧借酒裝瘋,他和酒吧裡的保鏢大打出手,最後累極,於黎明曙光裡沈入夢鄕,人雖未死,但已距死期不遠。
這場關鍵戲最難處理的部分,莫過於開場如戈引雨果長詩《世紀傳奇》第十二章第六節愛琴海上羅德島上巨大太陽神石像的吶喊。在筆者看過的其他演出中,這段引言往往是喃喃道出,宛如夢囈,雨果原詩的氣勢與力道完全喪失殆盡。
在胡塞爾的演出中,如戈全裸先行出場獨自立於台上,偉岸、孤立,背景銀幕整面刷藍,一股煙霧緩緩地從舞台兩翼滲出,逐漸瀰漫全景,他正面對著觀衆怒喊:「就是因此我被塑造成運動員。/今日你的震怒成全了我。/喔大海,我站在神聖的底座上無比巨大/你洶湧的波濤無法侵蝕我的雙腳。/赤裸、堅強,前額沈入濃霧深淵」(195)。
如此具震撼力的處理手法不僅充分展現巨大石像張口吶喊的驚人力量,且強勁地點出全劇太陽神的重要指涉。接著,保鏢與妓女方才陸續登場,他們在絕望的心態下大跳勁舞。全裸的如戈與周遭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的確像是旁人稱他之「瘋子」,他甚至對著不通的電話說話:「我要走了。我得馬上上路……我得走了因爲我快死了。反正,誰也不關心誰。沒有的事!男人需要女人而且女人也需要男人。不過說到愛情,男女之間沒有愛情……我相信沒什麼好說了,沒有什麼可說的……反正,一年、百年,都是一樣的;遲早每個人都會死,每個人的結局都一樣……」(198—99)。此景中裸裎現身的如戈,更能突出主角於生命危機時分自我剖白的情境。
結局〈侯貝多逐日〉,全體演員全裸演出。這場高潮戲原應只見如戈一人於日正當中逃到監獄的屋頂上,其他人犯只聞其聲,未見人影,突然之間刮起一陣暴風,如戈最後於正午「彷彿原子彈爆炸一樣耀眼的末世景象中」墜樓(240),全劇終。
胡塞爾則反其道而行。他讓代表囚犯的四名演員裸身分別爬上四部閉路電視的軌道桿上,直視前方,分別道出劇中囚犯眼看主角爬上監獄屋頂的驚險過程,演員全身的肌肉由於用力因而全面繃緊,危急萬分的情勢眼看一觸即發。此時的如戈則相反地,赤身留在地面上,直至尾聲方才在現場觀衆伸出手扶住身的狀態下,跨上中央觀衆席的椅背上,踏著逐漸往上升高的椅背出場。這也就是說,如戈並未在舞台上摔下,而是相反地,逐漸爬高,最後消失於最高之暗處,「昇天」的象徵意味顯而易見(註8)。全體演員赤裸裸的演出強化了結局撼人的力量。
無法逃離的夢魘世界
採表現主義編劇的《侯貝多.如戈》於寫實的大背景中,不時浮現視角扭曲的夢魘情景。胡塞爾則透過選角表達另一種心靈夢魘的觀感。他用六名演員扮演劇中廿多名角色,其中除了如戈一角由固定的演員擔綱外,其他演員必須一人飾演數角,因此如戈看來彷彿隨時隨地都碰到同樣的人。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他的母親與他稍後在公園中遇見的一位太太即由同一名女演員出任,飾演小女生的演員稍後又化身爲一名妓女。而他在地下鐵車站碰到的老頭,拿掉圓滾滾的肚子,便成了他在公園裡劫持的小孩(註9)。這種情形,從小女生的觀點視之,更是令人心驚:她的哥哥維持人妖的裝扮,同時扮演妓院的保鏢;她的姊姊採一貫的歇斯底里表演路線,同時出任老鴇,最後是她花錢買小女生下海。小女生因此看來永遠逃不出這個肉慾橫流的世界。
觀賞胡塞爾高能量的舞台作品,不免使人聯想亞陶(A. Artaud)畢生所追求的一種獨立於言語之外的具體、物質化舞台表演語彙,這是一種先行訴諸觀衆五官的舞台語言,熔音樂、舞蹈、戲劇與多媒體爲一爐,表演意象強而有力,演員精力迸射,全場演出爆發驚人的能量,而且意蘊豐富,絲毫不讓人覺得導演譁衆取寵。在此同時,胡塞爾又能兼顧劇文的重要性,甚至於《侯貝多.如戈》一戲中,特別凸出劇文舉足輕重的地位,殊爲不易。
註:
l.Le théâtre de la mort, T. Kantor, éd. D. Bablet, Lausanne, L'Age d'Homme, 1977, p.20.
2.M. Vinaver, "Sur Koltès", Alternatives theatrals, no. 35-36, février, 1994, p.10。另請參閱拙作〈不同凡響的戲劇世界〉,《戈爾德思劇作選》,桂冠出版社,1997,頁262-66。
3.引文見拙譯著《戈爾德思劇作選》,桂冠出版社,1997,頁237。以下出自本劇的引文皆直接於文中註明頁數。
4.例如:
探長:「你知道他叫什麼?你一定知道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小女生:「我知道」。
探長:「說」。
小女生:「我知道,而且很清楚」。
探長:「小女孩,你在開我們的玩笑。你想挨耳光嗎?」
小女生:「我不想挨耳光子。我知道他叫什麼,只是一下子說不出來」。
探長:「就像這樣子說,你說不出來?」。
小女生:「名字就出來了,已經到舌尖上了」。
探長:「舌尖,到舌尖上。你找耳光打。」(204)
5.詳見拙作〈暴力、媒體與戲劇〉,《表演藝術》,第六十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頁18-25。
6.Roberto Succo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義大利北邊的Trevise城落網,翌日所有的媒體與記者皆聞風趕至,正巧目睹Succo利用犯人外出散步的時機,趁獄警不注意的當下,爬到牢獄的屋頂上對著媒體記者大聲喊話,並拾起屋瓦砸壞地上的汽車,且開始寬衣解帶。底下站的「觀衆」群起嘩然,Succo受到鼓舞,將身體吊掛在電纜上來回擺盪,最後手一鬆,人從八公尺高的屋頂摔下,不過只受了一點輕傷。三個月後,他在獄中用塑膠袋悶住頭部自殺死亡,詳見拙作〈瘋狂殺手或神話英雄?(上)〉,《當代》,一九九八年六月,頁76-78。
7.胡塞爾引叔本華之言自我表白:「性關係在人的世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性關係是所有行動隱而未現的中心,卻到處遭到遮掩。性本能是所有戰爭的原因以及和平的目標;它是一切嚴肅行動的基礎,一切玩笑的目標,一切風趣話永不枯竭的泉源,所有影射的關鍵,所有無聲符號、所有未表白的提議以及所有偷偷摸摸的視線的解釋,是年輕人每天的希冀而且通常也是老人的渴望,下流者成日為此頑念所纏,而端正之心靈亦無時不思及此」,引文見Dossier de Presse, Compagnie Utopia,2000.
8.按密特拉崇拜儀式之觀點視之,主角肉體雖亡,但靈魂將得到永生。有關戈爾德思是否將一殺人要犯神話為英雄的爭執,詳見拙作〈瘋狂殺手或神話英雄?(上)〉,頁84—88。
9.這個「老孩子」符合劇文所提及之小孩比實際年齡大許多的情形(209)。
文字|楊莉莉 清華大學外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