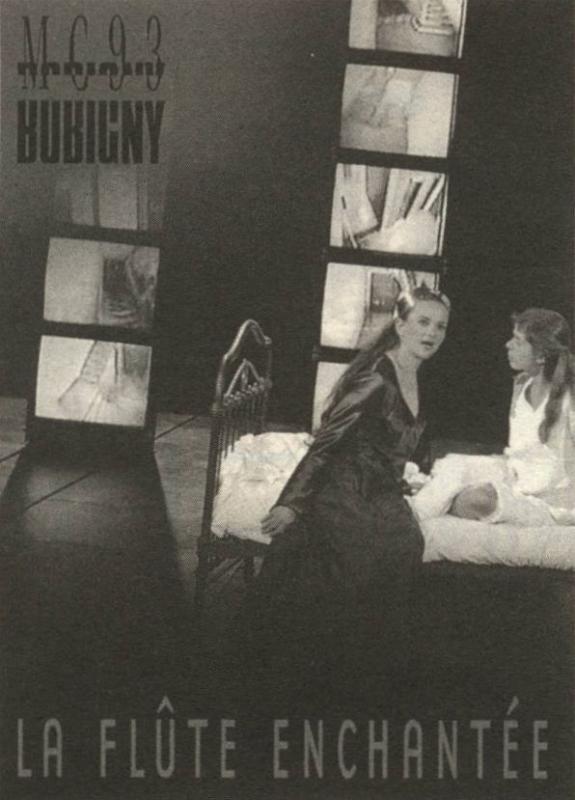陽光劇團團長兼導演莫努虛金的戲劇既非虛構的故事,也不是劇場和現實的並列,而是現實的戲劇化。《最後的驛站(奧德賽)》是她數月來風塵僕僕,從桑軋特到澳洲,與難民會面的成果。從二○○一和二○○二年間收集到的上百件真實敘事──個人奧德賽──構成本劇的內容。
睽違巴黎劇壇三年餘之後,享譽國際、重量級的法國陽光劇團(Théâtre du Soleil)終於在今年四月初推出最新大戲《最後的驛站(奧德賽)》Le Dernier Caravansérail (Odyssées)(註1)。
以近期令西方各國焦頭爛額的「難民」時事為主題,重拾該團自《黃金時代》(L'Âge d'or, 1975)後束之高閣的「集體創作」(création collective)(註2)方式,《最後的驛站(奧德賽)》帶給戲迷一個深具人道主義內涵的藝術饗宴。這齣戲贏得如潮佳評,至六月底的場次早已售罄,七月在亞維儂戲劇節演出,預訂九月到羅馬巡迴演出,十月中起回巴黎東郊老家「子彈庫」(Cartoucherie)重演,明年一月將到澳洲公演,明年五月則到德國魯爾藝術節(Rhurtriennale)演出。澳洲離台灣不遠,國家劇院有邀請他們屆時來台演出的計畫,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現實的戲劇化呈現
《最後的驛站(奧德賽)》是巴黎這幾個月來第三齣獻給難民的重要戲劇(註3)。一是去年十月於山崗國家劇院演出的《史基納》Skinner,出自法國「日常生活戲劇」(註4)創始劇作家之一的德易曲(Michel Deutsch),便是一個描寫被人蛇集團遺留在邊境地帶的偷渡客的故事;接著是去年十二月,在MC93劇場,知名美國導演瑟拉爾斯(Peter Sellars)在上古希臘悲劇作家優里皮底斯(Euripides, 480B.C.─ 406B.C.)作品《赫拉克列斯的孩子們》The Children of Herakles演出的第一部分,舉行一系列全世界流亡者的見證座談,在表演後的第三部分,則播放以難民為主題的紀錄片與劇情片。從美學觀點來看,陽光劇團團長兼導演莫努虛金(Ariane Mnouchkine)採取一個幾乎相反的藝術手段。她的戲劇既非虛構的故事,也不是劇場和現實的並列,而是現實的戲劇化。《最後的驛站(奧德賽)》是她數月來風塵僕僕,從桑軋特(註5)到澳洲,與難民會面的成果。從二○○一和二○○二年間收集到的上百件真實敘事──個人奧德賽──構成本劇的內容。
曾私下造訪台灣數次的莫努虛金,素以理想主義者的形象著稱。一九九五年,她以絕食抗議南斯拉夫內戰的屠殺(註6);翌年,她在「子彈庫」收容無居留證的人民,並在劇場的屋楣上升起法國的三色國旗。二○○一年初夏,她親自到桑軋特難民營會見難民,難民營當局介紹庫德族詩人、演員格拉尼(Sarkaw Gorany)擔任她的翻譯員。格拉尼原本也是桑軋特的難民,從此加入陽光劇團,在《最後的驛站(奧德賽)》中演出。後來,莫努虛金再度返回桑軋特,由懂波斯文的陽光劇團伊朗裔女演員貝艾絲逖(Shaghayegh Beheshti)陪同為她翻譯,用錄音機錄下難民口述的悲慘故事。二○○一年十二月,當陽光劇團在澳洲巡迴公演《堤上的鼓手》(Tambours sur la Digue,1999)時,莫努虛金在報章上讀到一艘挪威船「坦帕號」(La Tampa)因為在海上收留了難民,澳洲當局反對這艘船靠岸,而這些船上的人員將被關在離這兒幾千公里遠的迷你小島上。
進入難民營聽故事
莫努虛金與貝艾絲逖被允許進入一個位於雪梨的難民營,營區圍繞著有刺鐵絲網,由一名私人警衛看守,裡面監禁著數百名中國人、北韓人、伊朗人和庫德人……等,她們在這裡錄下上百小時的訪談。莫努虛金因此得知難民營當局如何非法地驅逐個人至印尼的無數小島,並在靠岸時將船弄破,使人無法返回。接下來,她們來到紐西蘭,「坦帕號」在澳洲水域救起的阿富汗青少年被收容於此處,這些十到十六歲的男生或是孤兒,或是因為父母不願他們參加塔利班的軍隊而放逐異鄉,以求得到較好的待遇,可以適齡就學(註7)。
然後,莫努虛金與貝艾絲逖拜訪了羅柏克(Lombok),一個鄰近巴里島的小島。兩百四十名阿富汗人經由人蛇集團安排先偷渡至印尼,接着乘小船到澳洲。他們被澳洲警方帶到羅柏克隔離,等待澳洲政府審查他們的案件,澳洲政府提供兩千元給所有願意返回阿富汗的人,不願意的人則被封鎖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沒錢、沒工作、沒任何出路,焦灼地等待另一個國際當局來釐清他們的情況。她們特別到羅柏克的一個印尼宿舍,告知一名婦女她的丈夫在澳洲難民營裡的消息。莫努虛金告訴難民們自己不是記者,不能為他們做什麼,而是一個做劇場的人,想說他們的故事。阿富汗沒有劇場,難民不知劇場為何物;但慢慢地,他們開啟話匣子,要求陽光劇團代他們向他人訴說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家庭的故事。大多數人向她們解釋從前是多麼美好;而如今年輕人只認識戰爭,因為沒有未來而離開家鄉。這些故事非常簡單,譬如在旅途中,別人給他們一瓶水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敘事逐步構成一首史詩。最後,莫努虛金與貝艾絲逖一齊設法救出澳洲難民營中的兩個人,這兩個人目前皆被收容於陽光劇團。
集體創作憑直覺
莫努虛金將這些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與庫德族難民的訪問錄音攜回「子彈庫」,交給與她長期合作的編劇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但劇作家放棄寫一齣受見證影響的劇本,於是莫努虛金集合旗下演員進行「集體創作」。從去年九月開始,演員們以偷渡者、移民及戰爭的其他犧牲者等人物為出發點即興創作,導演要求他們任憑形象及感覺穿透他們。「同情」(非「憐憫」)成為工作的格言,包涵了「分享」之意,難民敘事和即興表演的關係也似乎是直接、立即的。為了保留「創作自由」,導演不讓演員聽任何難民的證言,之後,訪問錄音才印證了演員們的直覺。如此,《最後的驛站(奧德賽)》圍繞著莫努虛金集體建構,導演自稱她的角色不過是「讓有創造性的演員表達」而已。陽光劇團總共收集了三百八十九個成功的即興創作,但最後只選擇六十幾個構成演出(註8)。這齣劇共動用了三十五名演員,其中有十二名新進演員,說二十二種語言(註9),他們同時也參與佈景與舞台裝置的建造。
《最後的驛站(奧德賽)》總題為「殘酷的河流」,由十九篇敘事組成。上半場分為十景:〈擺渡〉、〈桑軋特〉、〈阿富汗的愛情(鳥篇)〉、〈陰暗的夜晚〉、〈留下來的人〉、〈德黑蘭的夏夜〉、〈向火車進攻〉、〈阿富汗的愛情(星夜篇)〉、〈在路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耶)〉、〈海岸防禦線〉,下半場分為九景:〈世界的新娘〉、〈事情發生的那一夜〉、〈海岸防禦線上的交鋒〉、〈阿富汗的愛情(完結篇)〉、〈非洲的某處〉、〈狂風暴雨的夜晚〉、〈法國小海灘〉、〈工作與鬥爭〉、〈喀布爾。解放〉。這些在舞台上重建的日常生活斷片和小故事,描繪了難民在自己國家所承受的政治、經濟或宗教方面的慣常苦難,與野蠻、希望與絕望、在尋求政治庇護國家的破碎夢想與人道轉瞬即逝的裂片。
難民掙扎動人顯影
開場點題的〈擺渡〉,場景位於吉爾吉斯共和國(Kirghizistan)和哈薩克共和國(Kazakhstan)邊境間洶湧澎湃的河流上,在人蛇的掌控下,人們競相搭乘在暴風雨裡搖晃顛簸的小吊籃,要到河的那一端;河流是一片翻騰、發出劈啪聲、鼓起又落下的廣大布匹,場面浩大,立即把觀眾捲入這齣盛大的戲劇中。在〈阿富汗的愛情〉三部曲裡,一對情侶因為犯下相愛的罪而遭到長滿落腮鬍的塔利班殺害。而重複出現的非法穿越鐵絲網一景,堪稱其中戲劇張力最強的段落之一,在桑軋特,每一夜,驚恐且氣喘吁吁的偷渡客們,在他們高價付費的保加利亞籍人蛇的命令下,鑽過鐵絲網的洞口躲進壕溝裡,等待一列駛向英國的火車。火車要不是不來,就是開得太快,令人來不及攀登,有人還因此斷了一條腿。難民營的夜警發現偷渡客,把他們帶回。而人蛇集團之間發生爭執,被射殺的人蛇屍體攀掛在鐵絲網上,他口袋裡的手機響起,傳出小兒子獻給父親的歌聲……此外,在每一景之間插入的優美信件或詩文,投映在舞台底部的銀幕上,並以充滿情感的聲音讀出,使我們更能夠體會難民內心掙扎的痛苦。
場景的剪接、節奏、舞台內部空間的框架切割,勒梅特赫(Jean-Jacques Lemêtre)融合各民族樂風的劇場配樂原聲帶,及如同電影中「畫外」(hors-champ)的高明運用(註 10)──僅用一個軀體或動作的出場即勾勒出故事的梗概,令《最後的驛站(奧德賽)》帶有電影的況味。莫努虛金具驚人形象感和風格化的導演才華又達到另一個新高峰(我們別忘了她也是電影導演)。劇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巧思是:在張掛灰色布帘、光禿禿的舞台上,所有劇中角色和佈景皆棲置於附小輪的板子上,由其他演員推出場並操縱其滑動,角色足不落地,在移動的平台上保持不穩定的平衡,象徵著難民失根漂流的悲情命運;再者,美輪美奐的佈景與服飾,演員卓越的肢體語言,在在令人目不暇給。
繼《背信的城市或復仇女神的甦醒》(La Ville parjure ou le Réveil des Erynies,1994)、《突然就是不眠之夜》(Et soudain des nuits d'éveil, 1997─1998)與《堤上的鼓手》之後,以運用東方傳統劇場技巧聞名的陽光劇團再度拾起詩意的武器,向這個無視社會邊緣者的世界,提出責任的問題。他們不斷變化風格的戲劇匯聚了三個典範:法國重要劇場導演維拉(Jean Vilar, 1912─1971) 提倡的「人民劇場」(théâtre populaire)、布萊希特主張的「政治劇場」(théâtre politique)和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下的「節慶劇場」(Théâtre festif)(註11)。該團明年將邁入第四十年的劇場生涯,與其先前尚古的作品迥異,《最後的驛站(奧德賽)》的主題全然現代,它取材自棘手的時事,鋪展了一幅描繪流亡者的巨幅畫面,令觀眾走出劇場後,除了享盡聲色之美外,亦平添不少感時憂世之思。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註﹕
1. 《奧德賽》L' Odyssée原是上古希臘詩人荷馬(Homère)的史詩傑作,詩中主題有關特洛伊戰爭後,國王奧德修斯(Odysseus)歷經重重磨難和考驗始得返回故國綺瑟加的故事,引伸為充滿驚險的旅行或經歷。
2.一九六○與七○年代起西方劇場創作者發起的創作方式,非由單一個人(劇作家或導演)署名,而是由從事戲劇活動的團隊共同構思的表演。劇本經常在彩排時即興表演後確定,再由每個參加者提出修正。編劇工作循工作期間發展,只以一系列「試誤」參與整體構思。一切歷史、社會學與動作的探索為故事的定稿所必須,譬如陽光劇團早期傑作《一七八九》(1970─1971)和《一七八三》(1972─1973)。有時會發生演員以純粹身體和實驗的角色研究方法開始,根據他能找出的動作來創作他那一部分的故事。某些時候,在劇團工作中,會需要有人協調即興創作素材的,編劇與導演的工作於是變成必要。這是一種綜合與集中、不必然強迫要指名選擇一個人來承擔導演的職務,不過它促使劇團在風格與敘事上集中草稿,趨向集體的執導。這種工作方法現在常見於研究劇場中。(Patrice Pavis, Dictionnaire du Théâtre , Dunod, Paris, 1996, p.74)
3. René Solis, " Les voix de l'exil de Kaboul à Sangatte", Libération, le 15 avril 2003.
4. 請參閱拙作〈日常經驗為戰場,語言為武器──法國當代劇作家維納韋爾(Michel Vinaver)〉,《表演藝術》,第一一八期,2002年10月,頁44 ~45。
5. 桑軋特(Sangatte),法國北方鄰近英法海底隧道的難民收容中心,難民來此的目的在於儘可能停留短時間,以穿越英吉利海峽,非法偷渡至英國,因為他們懂得英語及族群成員的影響,而且英國政府給予難民優惠的待遇。(Programme de " Le Dernier Caravansérail( Odyssées)", Théâtre du Soleil, Paris, mai 2003)
6. Pierre Notte, " Les Voyages d'Ariane ", Revue Théâtres, n°8, avril / mai 2003,p.13.
7. Catherine Bédarida, " Profil: Les improvisations douloureuses de l'interprète Shaghayegh Beheshti ", Le Monde, le 1 avril 2003.
8. Catherine Bédarida, " Le Théâtre du Soleil porte la voix des réfugiés", Le Monde, le 1 avril 2003.
9. Jean-Louis Perrier, " À la Cartoucherie, les flux et les reflux de la misère et des hommes ", Le Monde, le 16 janivier 2003.
10. Fabienne Darge, " À la Cartoucherie de Vincennes, tableaux de la misère des chercheurs d'asile", Le Monde , le 24 avril 2003.
11. Jean-Jacques Roubine, Introduction aux grandes théories du théâtre , Dunond, Paris, 1998, 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