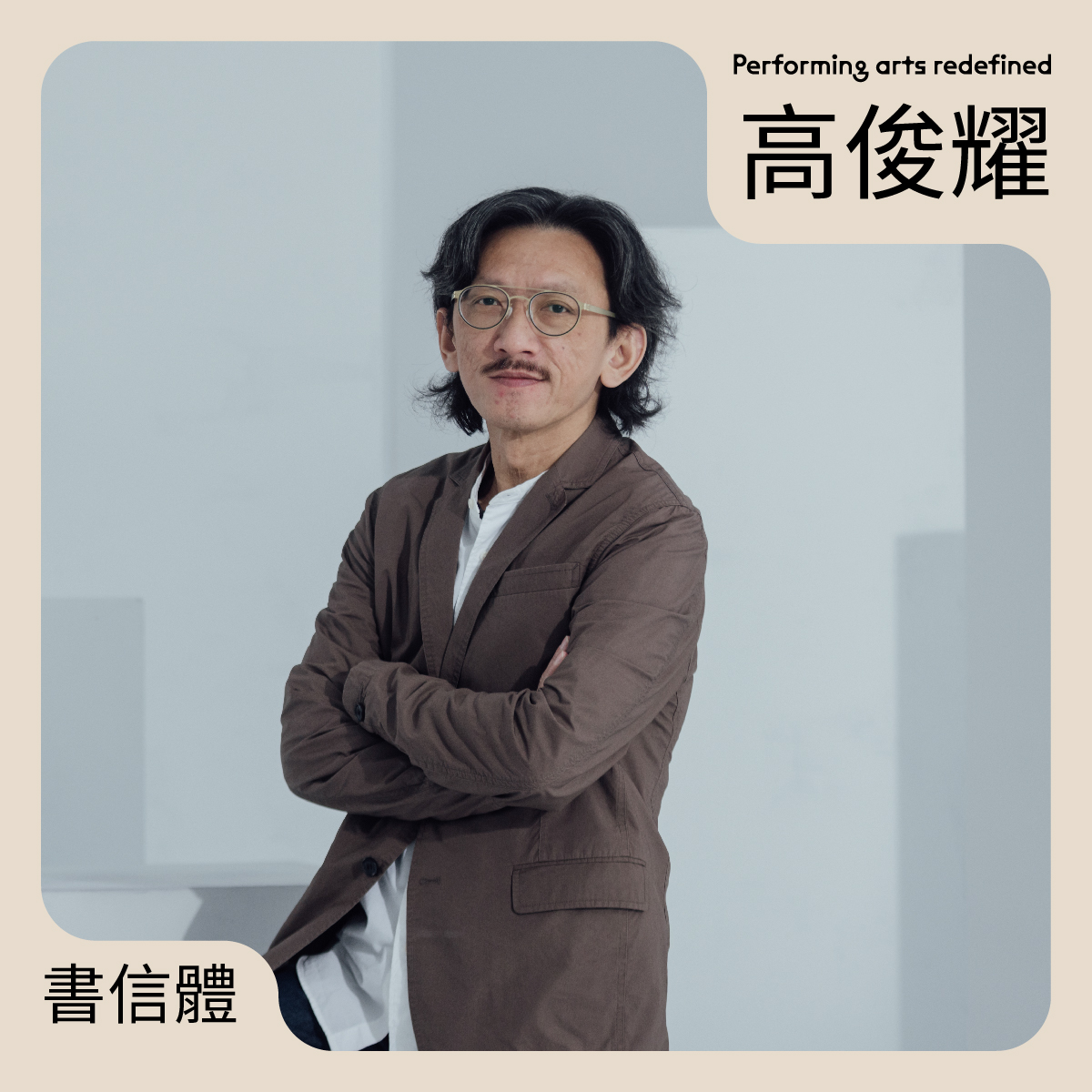YC,
年前回老家雙溪大年,老媽和大姐因年後要搬去吉隆坡居住,大掃除之際,該丟的丟、要留的留、能送的送,辛勞地奔波著、困難地抉擇著。2004年8月我出國留學時,就留了一大批書籍、物件和資料在姐姐家,想說過年過節回來時就清理,結果一擱就10來年,每次都跟自己說,再等一年吧,如果真的沒有再使用,就會放掉,如此自我說服了這些年。現在終於無法迴避長年堆積的舊物,要把眼下10來箱整理成兩箱帶走。於是第一步要把捨不得的書籍送走,恰好剛認識了一位在當地經營二手書的朋友,心想也太巧,偏偏在這時刻,就意味著書找到了主人,我得聆聽書的決定。再來就是一些工作資料,抉擇的方式簡單而蠻橫,捧在手上,有畫面的就保留,想不起的就丟棄,然後默默提醒自己,不喜不悲不嗔不怨,乍看以為在修行。最後就是一大堆剪報,最久遠的至少20餘年,油墨味沾黏在塵埃中,有些紙質幾近脆化,新聞或已不新,事件未必就此過去。該怎麼辦呢?我打了幾個噴嚏,偷偷撿拾了一些放進箱子,其餘的,一併回收。捫心瞭然,回收的,不只是舊物。
幾個小時後,心裡鬱悶得很,就往家附近走走。不遠處傳來咚咚鏜鏜的鑼鼓聲響,尋聲而至,來在關帝爺廟口前,果然有潮州戲在上演。還記得我跟你提過嗎?小時候,電視還不普及,潮州戲就是民間最要緊的娛樂。每逢節慶,黃昏5點就有許多人搬著凳子來占位,凳子一擺下,你就可以離開忙別的事,等7點開演再回來。大家頗有默契,都懂看戲倫理,你的凳子放著,沒有人會去挪動。那時候我就是負責幫婆婆和媽媽搬凳子的小傢伙。7點開演前人潮就聚集了,許多流動攤販也忙著招呼人客,炒粿條、雲吞麵、叻沙、紅豆冰、煎蕊、冰淇淋等,小小的我心底一樂,天底下有什麼比邊看邊吃、邊吃邊看,更逍遙的事?!
潮州戲,又稱潮劇,是用潮州方言載歌載舞的地方戲曲,流行於廣東、福建一帶。早期華人移民到馬來西亞時,通常會根據原籍地或自身方言來群聚或結社,甚至決定了所從事的行業。過去有「華社三寶」之稱,指的是中文教育、華文報章和華人社團。後者,就是按照地緣籍貫成立的會館,通常會運用廟宇、祠堂等公共空間來舉辦活動,聯繫鄉情也同時凝聚族群認同。我爸媽小小年紀就從廣東潮陽過來,一別就是五六十載。潮州戲敲鑼打鼓,口音薈萃了一個群體的精神樣貌,相信也慰藉了台下不少看倌們的心情。
話說回來,我來到廟口前,只見戲台前方停了好幾輛車,有幾隻野狗在覓食,就我一個觀眾望著台上演員唱念做打。幾個跑龍套的演得很馬虎,眼睛半睜不開,比手畫腳,完全不甩樂師的拍子。小生和旦角疏離地對戲,酷似悶熱的氣候,懶洋洋地演出著。或許是我看得十分專注,突然,小生一眼瞥見了我,眼神一揚,「咦,有人看戲?」興許是職業道德所致,他動作頃刻俐落爽淨,和他對戲的旦角見狀,也不敢唬弄,精神一提,嗓子拔地嘹亮,樂師們樂了,跟著起勁,音樂生猛起來,只剩下幾個跑龍套的,左顧右盼,在想發生了什麼事。
有幾個小孩搬了凳子過來,野狗識趣地讓了道,好幾個老人家攜伴走來,坐下,人群開始聚集。車主匆忙趕來,一邊跟大家說抱歉,一邊小心翼翼地把車開走,讓出了更大的空間。我索性爬到台口右側平台處,隔著樂師們的板子,就近觀看。啊!小時候自己不也這樣,好幾個小朋友因為個子矮小,坐在台下被人頭遮擋,看不到戲,就毫無顧忌地爬到台口兩側,彷彿是為自己而設的貴賓席,直到管事的廟祝瞅見,拿了把雞毛撢子來趕人。印象中,我也被彈了幾下。有幾個流動攤販推了攤子過來,叫嚷著,場面一時喧嘩起來,吃的喝的看的樂的,這下輪到我有些驚呆,彷彿兒時戲班榮景霎時重現。
一個跑龍套的順著走圓場靠了過來,「喂,這裡不能坐人,下去。」我不甘願地跳了下來,驚擾了一旁歇涼的野狗,一瞧,人群早已散去,空寂的平地就自己一人。我回頭看,台上兀自演得熱絡,大夥兒紛紛飆戲。我無法就此轉身,便繼續站著看戲,戲需要觀眾,觀眾也渴望著戲。小生熾熱的目光掃視過來,嘴角微揚,「啊,你還在!」……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