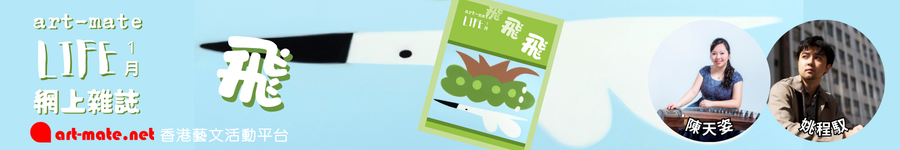果陀劇場《解憂雜貨店》
2025/8/29 19:30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
從東野圭吾的小說,到日本電影、中國電影,再到如今的舞台劇版本,《解憂雜貨店》一路跨越媒介。電影多半依靠鏡頭與剪接推進情節,而舞台劇則以「空間語言」來完成時空的流轉。如何讓寄信者與回信者的聲音不再只是文本上的呼應,而能同時呈現在觀眾眼前,正是此次舞台劇最具魅力的地方。
劇情整體承襲原著的核心:關於家業與夢想的兩難,情感與自我實踐的掙扎,以及人如何在回首過往時安放遺憾。舞台版完整保留體育選手的故事線,讓「夢想與情感陪伴」的矛盾更貼近當代語境。這一支線並未出現在中日電影版本,卻在劇場中突顯,或許呼應了現代對「個人成就與他人關係」的敏感議題。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片段,則來自一位多年後回覆來信的角色——他以善意隱去真相,不只是為了安慰他人,更像是對自己過往的和解。這使故事從單純的選擇辯證,延展為關於「善意如何彌合遺憾」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