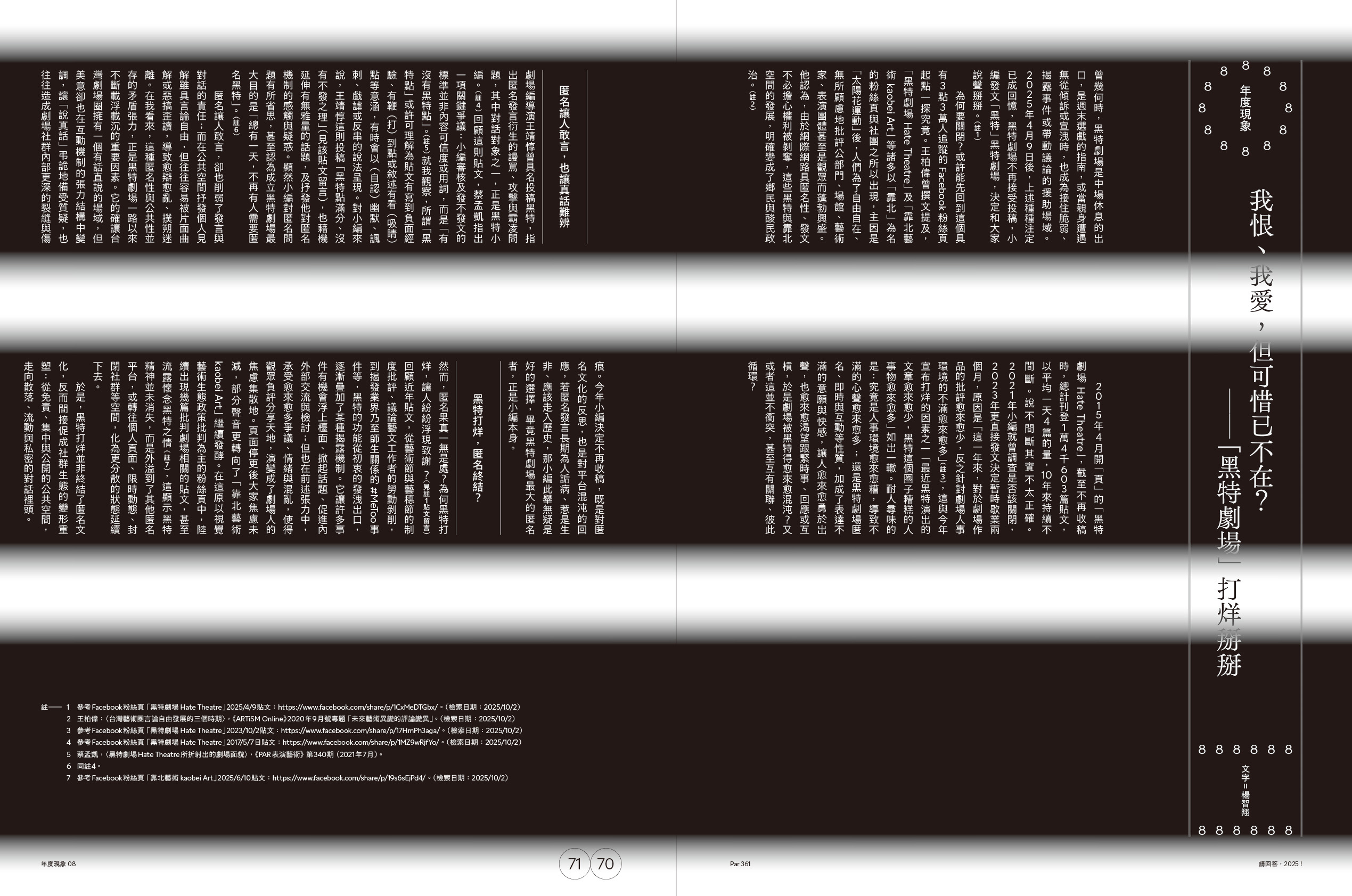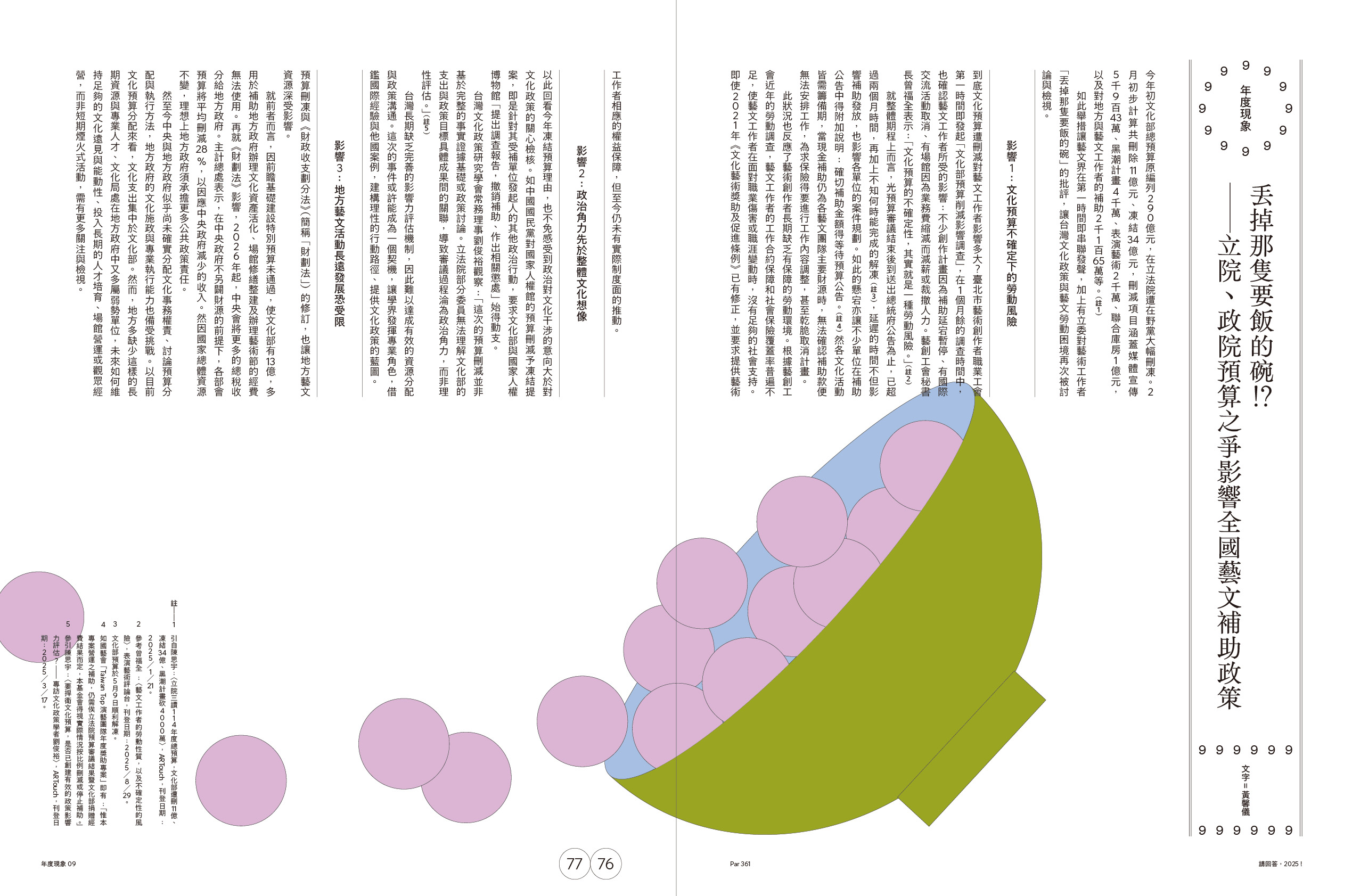張軍 永恆,是珍惜跟觀眾見面的美好相遇 (下)
Q:演《春江花月夜》時,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借鑑了多少傳統程式?創新部分主要體現在哪裡? 對於《春江花月夜》這樣的新戲,在塑造人物上,我大約會不自覺地先找到行當的歸類,畢竟這是我身上幾十年積累下來的下意識,而且我跟隨蔡正仁老師、岳美緹老師兩位恩師學戲,巾生、官生、窮生、雉尾生都學過。張若虛這個人物,我比較把他定位為小官生,飛揚一點的時候,會再更靠向巾生一些。聲音、身形、舞蹈動作,都是從傳統程式來的,這樣創作的時候有一個基本的依託,也是一種對傳統的再運用。 至於創新,我覺得是感知張若虛對於時間的思考。他永遠停留在27歲,但是和辛夷的三次見面,辛夷分別是16歲、26歲和66歲。這部分的創新,其實在傳統舞台上也有可借鑑的,比如說杜麗娘就是生生死死,超越生死,張若虛也是生生死死,超越生死。這種內心的、深度的,對於生命的、時間的感受感知感應,我覺得這是創新的部分。雖然這部戲是古典的題材,服裝也是古典的,總體呈現還是規規矩矩的,但內心在體驗這些非常深度的哲思時,我覺得是一種全新的探索和呈現。 Q:傳統文化與現代流行,小眾與大眾是否合流或是分流?當您專注固有藝術成就,對於創新與創作有什麼看法? 我一直覺得傳統文化和現代流行文化,小眾與大眾,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 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崑曲主宰中華民族的集體審美達兩百年之久,在那時,崑曲其實也是流行藝術、流行文化。隨著我們的推廣和創作,崑曲觀眾正在大幅度的增長。我說不上到底有多少崑曲的觀眾,但我經歷過崑曲的窘迫階段。1990年代中期左右,當我畢業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看崑曲,一個劇場只有幾十個人是常有的現象,但是經過了這20、30年的努力,好的崑曲演出都是一票難求。無可置疑,崑曲肯定是小眾藝術,這跟它的藝術質地和本質有關,但小眾也可以擁有大量的觀眾,看似對立的觀念其實並沒有那麼絕對。 就像在這些年間,我一直在創作的音樂形式,叫「水磨新調」,就是崑曲水磨調的新演繹方式。從錄音棚製作開始,一直走到了萬人演唱會,走到像小巨蛋這樣的場合,像周杰倫、蔡依林一樣地做崑曲搖滾音樂會,這種嘗試非常受到大家追捧,讓這樣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