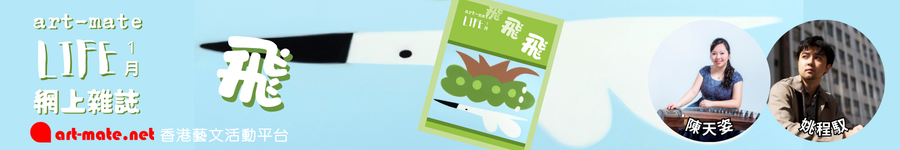第一次知道吉赛儿.韦安(Gisèle Vienne)是在法国演员阿黛儿.艾奈尔(Adèle Haenel)2023年的一封挞伐法国影视圈纵容权势性侵犯的公开信里读到的。
阿黛儿在最后一段写到:「自2019年以来,我一直与吉赛尔.韦安的戏剧与编舞合作中追求我的艺术作品。她是一位艺术家,创作了我见过最强大的作品之一。面对电影业树立的不屑、空洞、和残酷的运作原则,她让意义、作品和美不断地发挥作用,如同一盏明灯,让我对艺术强大的力量保持信仰。」
当时我没有去细究在这严肃的政治宣言里,占据一整个段落的艺术家究竟是何方神圣,因为我对这篇文本的表演性深深著迷,准备开启一系列「退出宣言」的实践创作。阿黛儿的公开信正好迎接当时台湾的#Metoo浪潮,「取消、退出」是我抓取出的核心。接著我在空总C-LAB开设了几场工作坊,带领参与者写下自己要退出、取消的身分与处境,并拍摄录像宣读,签署宣言等行动,最后阶段展演得到的一种回馈是:退出然后呢?
我总不小心被这句反问给惹怒。「然后呢」完全戳刺到#Metoo运动最深层的无力感,许多案例发现往往到最后退出的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又或许,更让我痛苦的是关于艺术无用的无解辩证。后来我认清「宣言」是一种感性的政治革命,其中所碰触的「压迫」没有所谓的本体,因为压迫是一种关系。
这个后来就是现在,读到阿黛儿公开信的一年后,我在柏林亲临了吉赛儿.韦安的展览:「This Causes Consciousness to Fracture-A Puppet Play」,回国后的隔天立刻在国家剧院看了她的舞作《群浪》。神秘的共时性,让我在最短时间见证了阿黛儿所言,并让那所谓强大的艺术力量的源头也穿越过我。
在柏林驻村期间,我看了超过20档展览,吉赛儿的人偶展绝对是体感深刻经验的前三名。一进展间,我就被高坐在展台上驼著背的长发女孩吓到。当你顺著动线经过她时,会有些不好意思但依然忍不住想弯腰看清楚她的脸。你知道她是个偶,你可以称她娃娃,可是很想开口问她叫什么名字?此刻已进入序场,别忘了这是一出「木偶剧」:A Puppet Play。
接著映入眼前的画面,是数座承装一具具青少年偶的长型玻璃方块。你很快就能抓取到青春逝去的简单隐喻,正在发育体型的偶,挂著苍白的面容、空洞的凝视,有时沾满了血迹或泪痕。脸颊上的妆,有些眼线、一些唇膏——尽管衣著符合青年潮流,但那些毫无生气、半透明且虚假完美的存在,正散发出一种在遥远记忆里熟悉过的「不安」。当你绕过一座又一座,像瞻仰遗容般细看他们的脸、服装、躺卧的姿态,你开始看见冻结的扭捏躁动,听见隐藏著幽灵般的声音、压抑的哭声,或是在寂静中出现的幻听低语——如同压抑暴力的回声,缠绕著一段天真、纯洁透亮的神话。
专精偶戏的吉赛儿,理解「操控」的技术可以赋予生命。我认为这是启动她倾向关注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内部的主要动能。钻析她的作品,很常看到暴力这个关键字,但更精准地说,她是在拆解社会环境与客体的暴力关系,譬如我们是如何被训练不去听╱看什么?我们为何又如何去改变自己的身体与姿态?如果我们是一座座偶,她在拆解的就是那些能移动我们关节的手。
吉赛儿在访谈中提到,儿时她认为偶是唯一的方法,能让她透过解离和创造内心世界去应对女孩身体经验的贬低——其中包含思考、想像,以及在身体外的各种创意策略。 在另一间展间,错置站立的人偶与观赏的青少年混为一个画面,你几乎无法立刻分辨谁是偶谁是人。那一刻我拿起手机记录下这诡异荒谬的画面,仔细思索吉赛儿如何透过改变观众的期望值,去打破、重建观众与艺术的关系:她用编舞家的思维实践了一出「沉静、静止的戏」,邀请观众以表演的期望来体验展览,甚至成为展品的一部分。对她而言,沉默和静止定义了各种经验,而这些经验实际上从未真正沉默或静止。因为沉默并不存在,就像静止也不存在。无法聆听沉默和静止的语言和运动,削弱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感知定义了什么能被听见和看见,从而影响了我们所有的行为,这些行为又不断结构社会。
吉赛儿的艺术包含剧场、偶戏、舞蹈、电影、雕塑、摄影、音乐等,舞作《群浪》对我来说便是涵盖这一切的实践成果。在一次的访谈中,吉赛儿将跨界创作这件事比喻成翻译,必须重新去检视所有的概念与细节,同时计算要把「人」放在何种脆弱的位置,让他们不断去检视自己的相信与期待。在观赏《群浪》时,某一瞬间我脑中冒出一个声音:到底是台上的舞者吸了大麻,还是台下的我?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绝顶艺术家的「制幻术」——制造一个足以与现实并置的世界,让观者在过程进行一场私密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