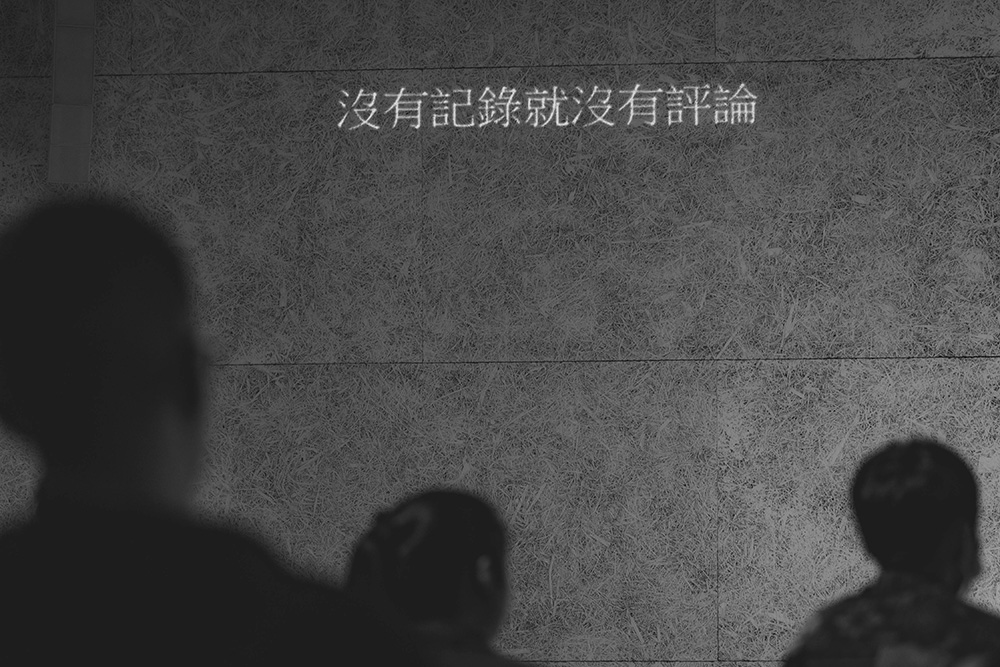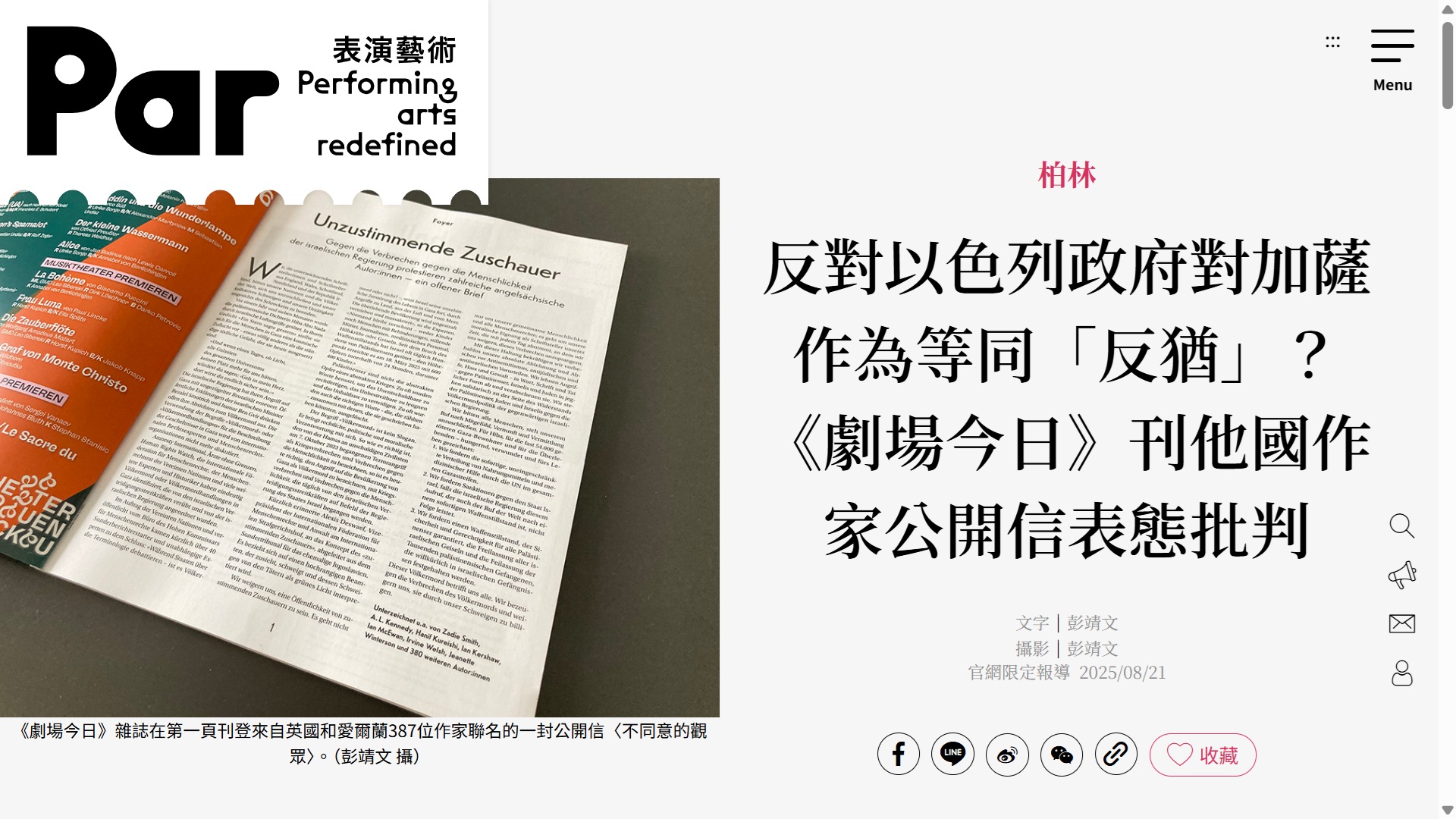年前,国民党团要求文化部停止「转型正义」工作,并以「扭曲国家对重要历史人物纪念的意义」等理由删除、减列与冻结文化部预算。其他如文宣费全数删除,黑潮计划共砍4,000万,公视则因台籍战俘的历史剧《听海涌》遭指涉扭曲史实,补助预算砍2,300万、冻结25%。一时间,文化人与导演拿补助是政治酬庸、为特定意识形态宣传等说法甚嚣尘上,「要饭说」更让艺文圈为之哗然。
作为曾经制作不止一个白色恐怖历史剧场作品,并曾获得相关政府补助经费的剧场导演,我认为现在是个适当时机正面回应这样的质疑:国家是否应该补助并推动「转型正义」文化活动?不仅是立委与网红对此有所抨击,表演艺术圈近年亦有相关质疑。剧评人王墨林近期在《PAR表演艺术》官网的文章中指称,时下白恐戏在执行当局「转型正义」政策的宣导下,将历史事件当成一种消费的政治(注1)。类似的观点,剧评人郭亮廷在去年亦有撰文提及(注2)。这些评论预设了一个立场:创作者只要接受了和国家转型正义工程有关的补助,作品就不证自明地服膺官方史观,或沦为国家政令宣传。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在这些再现白色恐怖历史的作品中,许多被认为是「史观」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是「美学」的问题。处理白色恐怖历史的剧场、影剧创作者,在大多数层面与一般创作者并无二致,创作与叙事的取舍若有任何标准,那必然是关乎创作者在实践什么样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