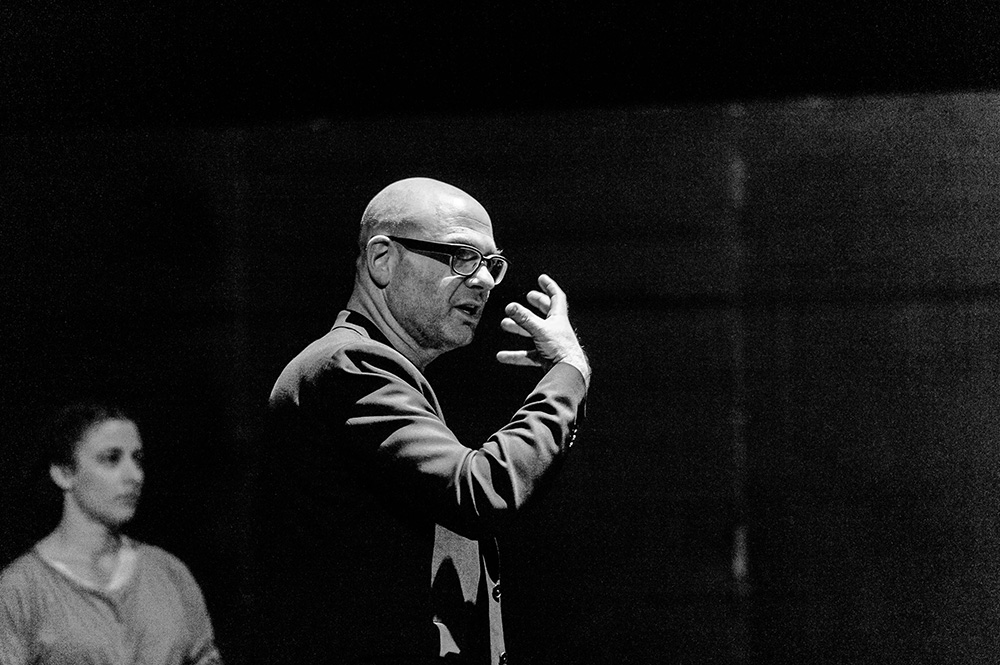Q:你的作品常被形容为「马戏剧场」(circus-theatre),融合多重艺术语汇。你认为这是当代马戏的趋势吗?
A:对我而言,多重语汇是必要的。某些主题以语言表达更具力量,但有时杂技动作与技巧才是我们与观众之间最强的桥梁,是传递情感与思想的方式。
我总是从主题出发,再寻找最合适的表达形式。马戏艺术、技艺与平衡永远是基础。
就像《奔跑者》,人们或许会问:这是剧场、舞蹈,还是马戏?对我来说,标签和分类并无意义。
Q:夜店马戏团几乎是捷克当代马戏的代名词,你如何看待当代马戏与传统马戏的关系?
A:20世纪初,捷克曾拥有欧洲最大之一的马戏团,不仅为娱乐,其目的也有教育性——让人们能见到平时无法看到的动物。那时没有网路,也没有动物园。传统马戏的魅力在于氛围、大帐篷与圆形舞台,但如今少有作品处理戏剧性、叙事性或结构创新。
传统马戏无法适应时代,也无法找到新的出路。有人争论是否应在舞台上使用动物,但若从那角度看,所有涉及动物的运动也都该结束。
对我而言,马戏艺术是多元而缤纷的——从最商业化的太阳剧团,到最实验的表演;从公共空间、画廊,到教育性、科学性、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创作。传统马戏无法涵盖这样的广度。

Q:你如何形容捷克当代马戏的特质?它目前面临哪些机会与挑战?
A: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创作自己认为重要的主题。作品建立在强大的戏剧传统之上,结合舞台设计、音乐、服装、灯光与音效等创意元素。
捷克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学校,因此难以培养新艺术家与下一代。我们自学成才,花了多年才达到受过专业训练者的杂技水准。如今观众已无法分辨谁是自学、谁是学院出身。捷克当代马戏仍深受剧场影响,强调叙事与主题深度。
Q:布拉格旧屠宰场区的 Jatka 78 是你们的基地,这个空间如何影响团队的发展?
A:拥有这个空间让我们获得自由。我们亲手翻修——成员、团队、朋友,甚至观众都参与其中。剧场内设有画廊、大排练厅、小舞台、训练场、教育中心、餐厅、物理治疗室、服装工坊,还有制作、行销与技术团队的工作空间。我们同时经营第2个场地,名为 Azyl78 的大帐篷。
自有空间让我们能制作其他剧院无法容纳的计划。我们能在舞台上完整排练1个月,使用全套舞台、灯光、音效与服装。这在其他剧院几乎不可能。
我们也能给年轻世代提供舞台、驻村计划,并接待国际团队。「拥有自己的家」带来巨大自由,但同时也带来责任。
这个场地也让我们得以实现筹备5年的专案,由阿喀郎.汗(Akram Khan )执导,预定于 2027 年 10 月在布拉格首演。
虽然这地方原本是屠宰场,但在这11年间,我们举办了多场「为亡兽的弥撒」(Mše za duše mrtvých zvířat),那是一种大型文化行动与和解的庆典。

Q:《奔跑者》在形式与内容上完美融合,作品的创作过程为何?
A:主题永远是核心。《奔跑者》谈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关于生命,关于时间无法重来。人生就像跑步机在运转:当生命从指间溜走,意味著什么?当我们跌倒、遇见他人、追逐某物时,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孩童般的游戏精神,什么又是危险?
这些是我们起初问自己的问题。当找到答案后,我们思考如何将它们化为舞台语言。《奔跑者》就是这个过程的成果。

Q:《奔跑者》中有多处极高难度的技术片段,特别是结合跑步机与大环的段落,能否分享其中的技术挑战?
A:若表演者没有经过数月适应跑步机,他们绝不可能完成现在的动作。距离首演仅10天时,我们才从速度5调升至10——那是巨大的差距。同样在首演前10天,我们第一次在跑步机上放入多个前所未有的物件与材质。
这正是我心目中的马戏:整场演出发生在一条移动中的跑步机上,就像有人在弹跳床上。只有具备技术、经验与技巧的人,才能在舞台上真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