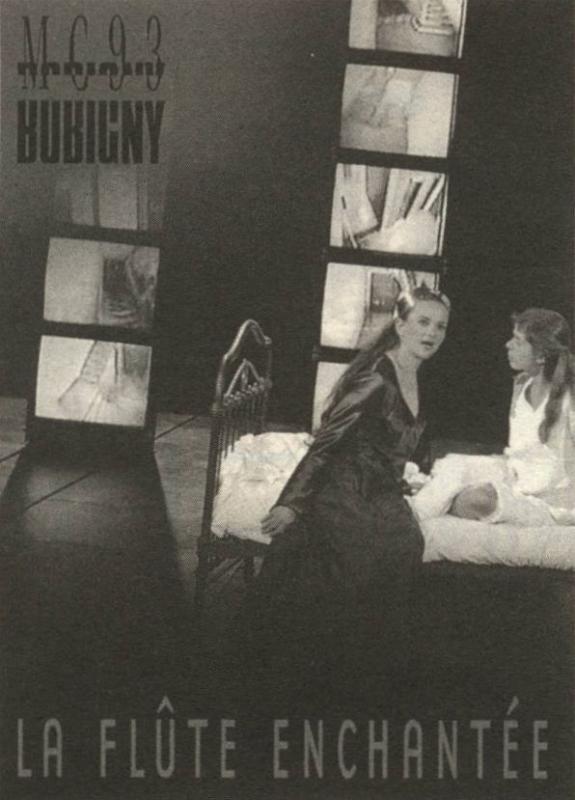納許在亞陶的作品裡找到總結這齣舞劇主題的一句話:「事關能夠糾纏一個作家意識的所有問題﹕生活、戲劇、習俗、宗教、詩、永恆。」這部創作勾勒了一盤形而上學的線索遊戲,譬如﹕活潑的與無生氣的,嚴肅的與滑稽可笑的,偶然的與需要的。總而言之,《穹蒼不再》儘管晦澀難懂,但在漂亮佈景與細緻燈光的映襯下,仍舊展現了一系列奇特、美麗的場景,令人目不暇給。
前年攜《夜無眠》Les Veilleurs訪台演出的法國匈牙利裔編舞家喬瑟夫‧納許(Josef Nadj),馳名國際,是法國當代舞壇前途似錦的創作者。他的舞蹈作品令人思及重量級波蘭戲劇導演康托(Tadeusz Kantor,1915-1990)的「死亡劇場」,兩者在角色方面略微近似(註1)。自從一九八七年以取材自出生村莊回憶的首部作品《北京鴨》Canard Pékinois成功地進駐法國舞壇開始,納許創作不輟,迄今已與巴黎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合製了十二齣作品。去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五日他又在此推出新作《穹蒼不再》Il n'y a plus de firmament。
這齣作品源於納許在畫家巴勒杜斯(Balthus,1908-2001)去世前不久拜訪其在瑞士住所的回憶,當他向主人辭行之際,老畫家對他殷勤叮嚀:「不要忘記我的朋友亞陶(Antonin Artaud, 1896-1948)。」納許返家後,馬上重讀了長年被關進精神病院,身心受盡折磨的法國詩人亞陶的作品全集。原來,在一九三五年時,巴勒杜斯曾為《頌西公爵》Les Cenci設計佈景,此劇乃亞陶唯一的劇本,也是「殘酷劇場股份有限公司」唯一的製作(註1)。而亞陶亦曾在超現實主義者面前為巴勒杜斯的繪畫辯護(註2)。此外,《穹蒼不再》是一九三二年亞陶應作曲家艾德加‧瓦黑茲(Edgard Varese)要求,為了一齣歌劇而寫的未完成文本,其內容與納許舞作內容毫無關係。
紀念一段不渝的友誼
此外,納許在紐約遇見了強‧巴比雷(Jean Babilée),這位年屆八十歲的知名舞者兼編舞家,於一九四六年穿着性感的單背帶工作服,首演了一齣名列法國舞蹈傳奇的芭蕾《少男與死亡》Jeune homme et la Mort,這齣法國重要編舞家候朗‧培堤(Roland Petit)的傑作,採用了法國才子作家考克多(Jean Cocteau)的舞劇主題(註3)。在巴勒杜斯逝世當天,納許與巴比雷碰巧談及畫家和他的作品,因此納許決定在巴勒杜斯的圖畫和亞陶的詩篇之間編織謎般的線條,創作一部作品獻給巴勒杜斯、亞陶與他們始終不渝的友誼。納許說:「從此刻起,我再拜訪里爾克(Rilke)、莊子、日本、意大利、愛爾蘭。我像蜘蛛一樣把這些空間聯繫起來,構成一個表演在其中誕生的迷宮。」(註4)
《穹蒼不再》開場時,巴比雷背對觀眾坐在椅子上,把玩著一把刀子,凝視、觀察,然後丟棄它,接著伸出手指在空中潦草地畫圖。此時,日本演員兼導演Yoshi Oïda──大師級戲劇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的旗下愛將──身著黑色長大衣,頭戴黑帽,從舞台底部的門進場,自懷中掏出白色布偶放在空了的椅子上,又從門內消失。這兩個人面對面,相互串通,分開,又夾帶一塊長木板重新出現。後來,他們一同分享佈滿釘子的圓形大麵包,戴上面具演出幻想的戲劇。劇末,兩人肩並肩坐在木板搭成的長椅上,全神貫注於他們沉默的對談中。這兩個皆已上了七十歲年紀的舞者和演員,猶如忙碌的默啞丑角,穿過雜耍演員的世界,陷入荒謬儀式的錯綜複雜中。
如蛇靈動 如貓輕巧
然而,吸引所有觀眾目光焦點的仍是在舞劇中,由馬戲雜技演員╱舞者們神乎其技的兩個表演段落。如鳥兒般棲息在門形高架上、守候已久的一名男子突然翻身,似蛇般沿竿滑下,被緩慢、無盡的墜落暈眩淹沒,然後再輕捷地爬上,回到原位。還有在羅西尼(Rossini)歌劇《塞維亞的理髮師》Le Barbier de Séville序曲中出場的四名舞者,一邊從舞台前方右側推出一個大櫥子且將其上下左右翻轉方向,一邊在大櫥子四邊及其門洞間舞動「重力╱抵銷重力」的芭蕾舞(註5)。此外,受中國傳統舞蹈訓練出身的中國女舞者金莉,除了以輕靈如貓的動作,跳著腰身柔軟的印度舞以及剛毅俐落的中國武術動作之外,她與巴比雷的雙人舞,在莊重之中點綴著小丑似的鬼臉,亦頗為逗趣。
納許在亞陶的作品裡找到總結這齣舞劇主題的一句話:「事關能夠糾纏一個作家意識的所有問題﹕生活、戲劇、習俗、宗教、詩、永恆。」(註6)這部創作勾勒了一盤形而上學的線索遊戲,譬如﹕活潑的與無生氣的,嚴肅的與滑稽可笑的,偶然的與需要的。總而言之,《穹蒼不再》儘管晦澀難懂,但在漂亮佈景與細緻燈光的映襯下,仍舊展現了一系列奇特、美麗的場景,令人目不暇給。
文字|蘇真穎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註﹕
1. Marcelle Michel et Isabelle Ginot, La Danse au XXe siècle, Bordas, Paris, 1995, p. 193 & p. 242.
2. Mathilde La Bardonnie, " De Balthus à Artaud, Nadj dans le bonheur ", Libération, 7 novembre 2003.
3. Sarah Clair, " Jean Babilée ou la danse buissonnière " , Van Dieren Editeur, Paris, 1995, pp. 56-60.
4. Irene Filiberti,"Josef Nadj : Il n'y a plus de firmament", Dossier de presse, 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 2003-2004.
5. Dominique Frétard, " Le rêve oriental de Josef Nadj se perd dans l'hommage aux maîtres " , Le Monde, 10 novembre 2003.
6. Gwénola David, " Une pièce sibylline, radieuse", Dossier de presse, Théâtre de la ville-Paris, 2003-2004.
向亞陶和巴勒杜斯的友情致敬
專訪喬瑟夫‧納許談新作《穹蒼不再》
關心亞陶生平與作品的意念及願望使我想要創作一齣舞劇。我尋找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應,並探討友情﹕一個生者與另一個不在的人、一個死去朋友的關係,當他們的生命分離時,如何保持遠距離的友誼。舞蹈的中心主題因此出現﹕兩個世界力求互相靠近,兩個經歷不同生命歷程的人的感受。
──喬瑟夫‧納許
訪問整理﹕蘇真穎(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法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巴黎市立劇院正在演出您的最新創作《穹蒼不再》,我覺得它是一部非常優美的作品,請問這齣舞作的構思從何而來?
這部創作是一連串機緣的成果。它與我之前事先決定研讀如卡夫卡、波赫士(Borges)等作家的創作,或獻給我最喜愛的文學作者的舞劇相較之下頗為不同。它的不同首先是與編輯米歇勒‧阿赫襄博(Michel Archimbaud)的會面,我們很喜歡討論藝術。當我們提及巴勒杜斯(Balthus),剛好他認識他,甚至在編輯一本關於他的書。我問他是否可以介紹我去他家畫室,因為我喜歡在畫家的畫室攝影。他幫我引介,帶我到巴勒杜斯在瑞士的家,而我就在畫室給他拍照。
我們討論,東拉西扯。他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是編舞家、做劇場的人。突然,他開始談起他的朋友亞陶(Antonin Artaud)。我發現他變得容光煥發,而關於亞陶的回憶令他心煩意亂。離開時他再一次對我說﹕「亞陶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幾個月後,我再回到他家去拍照。我們繼續討論。他重新和我說到亞陶,好似他要把「應多注意亞陶」這個想法傳到或貼到我的腦中。就這樣,關心亞陶生平與作品的意念及願望使我想要創作一齣舞劇。我尋找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應,並探討友情﹕一個生者與另一個不在的人、一個死去朋友的關係,當他們的生命分離時,如何保持遠距離的友誼。舞蹈的中心主題因此出現﹕兩個世界力求互相靠近,兩個經歷不同生命歷程的人的感受。
畫出來的靈思
巴勒杜斯也說到在他們相識時期發生的一樁事件。他說亞陶摔了一跤,他從樓梯上跌下來頭部受到強烈撞擊。巴勒杜斯微笑著說﹕「就是在這一跤後,他寫了他的宣言《殘酷劇場》。」對我而言,亞陶跌倒的意象變得十分強烈,於是變成這齣舞劇的中心主題之一﹕如何在涉及亞陶的事實之外表現跌倒、人的墜落。主題﹕跌落的隱喻。我以棲息在中國桅杆上的雜技演員來實現這個主題﹕他墜落,慢慢地從譬如門之類的結構降落(這個結構印在宣傳海報上),然後慢慢地跌落、攀升、摔跤。在找到這個主題後,我嘗試在巴勒杜斯的繪畫中找尋可以在舞蹈裡發揮的小主題。在他的畫室裡,有一本畫冊偶然地打開到某一頁,畫中有一扇窗,窗前有一張桌子,桌上有一把刀。我把出自巴勒杜斯繪畫裡作為神話裡犧牲象徵的刀引入舞蹈中。接著,我又在《道路》La rue畫中看見一個肩上扛著木板的人物穿越馬路,一個遮住臉的謎樣人物。我取木板當作主題並以此結束表演﹕他們到達,放下木板,兩個人坐在木板上凝視兩個巨人──兩個出自亞陶日記的人偶。他夢想有一天能夠將十公尺高的兩個龐大人偶搬上舞台,卻從未實現這個夢想。
現在,我已經有了四個主題,接下來我找第五個作為我排演工作的基礎與開端。當我造訪巴勒杜斯家時,就在進門之前,我發現在擦鞋墊上畫著一匹馬。我打開門看見一幅畫,不是巴勒杜斯的畫,只是隨便一個畫馬的畫家。當我在巴勒杜斯家的浴室望著外面的庭院時,我看見一匹活生生的駿馬出現在眼前,轉圈,然後消失。懷著馬的影像回家後我繼續閱讀亞陶,然後不期然看見一個句子﹕「我,亞陶,始終想身為一匹馬,而不是一個人。」啊!就這樣,我必須找到一個結合兩人的馬的圖像。在舞作中,我構想一幅不斷從牆上掉落的馬的圖畫,以模仿「亞陶─馬」的墜落,然後他發現畫的背面有一匹長翅膀的馬,再將它掛回牆上,畫不再掉落。有了這些基礎主題後,我便自由地從閱讀亞陶的作品中汲取思想,開始發展段落。
留存當下的感動
您要在這齣舞作裡表達什麼?
又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因為對我而言,舞作本身,如何以一系列的形象構成,便是其訊息。我不要以話語表現,說這個代表這個,每齣舞作對我而言都源於內在創作的需要,也就是說,在美學計畫之外,我不要證實什麼。每齣作品總是留下我現階段的感受,以及我在生命此刻易受感動的事物。當我編這齣舞作時,亞陶和巴勒杜斯的世界向我呼喊,他們表現的事物給我深刻的影響,這個作品便是我對他們的世界所做的見證、反省與回答。
請談談這齣舞作的創作過程?
創作過程像平常一樣。我含含糊糊地向我的舞團解釋題材,我們要處理什麼,是怎麼一回事。關鍵總是在於一系列的即興創作。我已經勾勒初步的雛型、題材、方向與情境,向我的舞者解釋﹕「我希望你們往這些尚無細節、我還沒有等待明確形式出現的方向思索。」我等待能量顯現,等待許多其他需要時間的事情。即興創作是使這些成分變得顯著的最佳方式。他們開始練習,我觀察他們,如果需要的話,嘗試給予資訊,使他們接近我已發現的。首先是感覺,隨着動作、情境和反應出現,我開始讓舞者知道哪些是準確、符合我的期望的。然後我們開始默記。我以形象編舞並逐漸地確定呈現主題的某種編劇法與決定段落。同時我們進行許多變化,而我則在一定的時刻決定順序與細節。最後我們練習節奏、細節、細節的均等,舞作便產生了。
演員Yoshi Oïda說的幾句話──也是這齣舞作裡唯一的幾句話語──令人費解。這些話的意思是什麼?這種語言存在嗎?在您的上一齣作品《哲學家們》Les Philosophes裡面,也有幾句不可理解的話。歸根結柢,話語在您的「動作與形象的劇場」裡扮演什麼角色?
這是亞陶作品的一段具體原文,亞陶詩篇裡不可理解的詞、他的語言遊戲。他寫作、找到。這些是亞陶偶爾以發明想像的語言自娛時新發明的詞。他僅僅以詞的音色寫作,編寫詩篇。這是我在亞陶的敘事裡找到的一段詩。確切地說,他引用這些詩句。此外,話語在我的作品裡扮演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但也是一塊我不忽略的領域。我首先以動作與形象表現。之後,如果需要,我與我的舞者╱演員也以聲音來表現。人以說話、唱歌來表達,他有從自身發出聲音的能力。話語是一個可能性,卻不是唯一的。這是為什麼我們有時使用所有人皆無法理解的語言,譬如:在《哲學家們》裡,爸爸的角色在開場時說蘇美爾語,一種已被遺忘、消失的語言。或許有許多事物皆消失在人的記憶關係裡。
您的作品跨越數種不同的舞台藝術﹕舞蹈、啞劇與馬戲,請問表演者們來自什麼領域?
各種領域。在這齣舞作中非常明顯,因為混合了一個老舞者強‧巴比雷與一個年輕中國舞者金莉,演員Yoshi Oïda以及馬戲雜技演員。對我而言,這是個理想的混合體。我自己的團則是由演員和舞者組成。
這齣舞作含有許多東方元素,譬如中國皮影、中國武術、印度舞、中國風味的舞台佈景、日本演員與中國舞者……等。在您的創作裡,東方佔有何種地位?
答﹕的確,我試圖透過巴勒杜斯來接近東方。巴勒杜斯曾和日本妻子在日本生活,而亞陶讚賞答里島舞劇。對我而言,重要的是多年來沉浸於東方哲學、智慧及補全西方世界的東方傳統。更何況對我的原籍是重要的,我們匈牙利人不是起源於歐洲,而是來自東邊很遠的地方。為了感到自己的完整性,我當然同時需要西方和東方文化作為精神食糧。
深思的劇場
您的舞作呈現一種荒謬的詩學,是否與中歐被戰爭蹂躪的荒謬現實有關?
是的,甚至它來自更遠的地方。我們看見國家、歷史的狀況明顯地在藝術的各個領域,特別是文學,孕育出一種坦白注視的風格,指出人類狀態的艱澀與怪誕。
您從文學、哲學、繪畫及時事等汲取創作的靈感泉源。舞蹈的理智化和劇場化賦予您的表演深度。您認為這是西方當代舞蹈的有利發展方向嗎?
不,我不認為。這真的取決於創作者,他們想要放什麼在作品中,和他們如何感覺。我嘗試透過表演來轉化我的思想、自己生活中的不安、對什麼易受感動、人類狀況、人的全部敏感性,不只是現在的,也有過去的。我只是嘗試連接然後將它的複雜性呈現在舞台上,因此有一部分對人生與哲理的思考。然而,劇場對我來說是一個交流和儀式發生的地方,並非僅僅是一場空話,而是能深刻思考的地方。所以我力圖捍衛包含所有這些組成部分的表演。
請問您在編舞方面有沒有師傅或弟子﹖
沒有。
未來的計畫﹖
始終是創作新的舞蹈作品。
主題為何?
下一個舞作的主題是二十世紀初法國作家黑蒙‧胡塞爾(Raymond Roussel)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他寫作了有關胡塞爾與人類瘋狂的研究作品。
延伸閱讀:
http://www.josefnad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