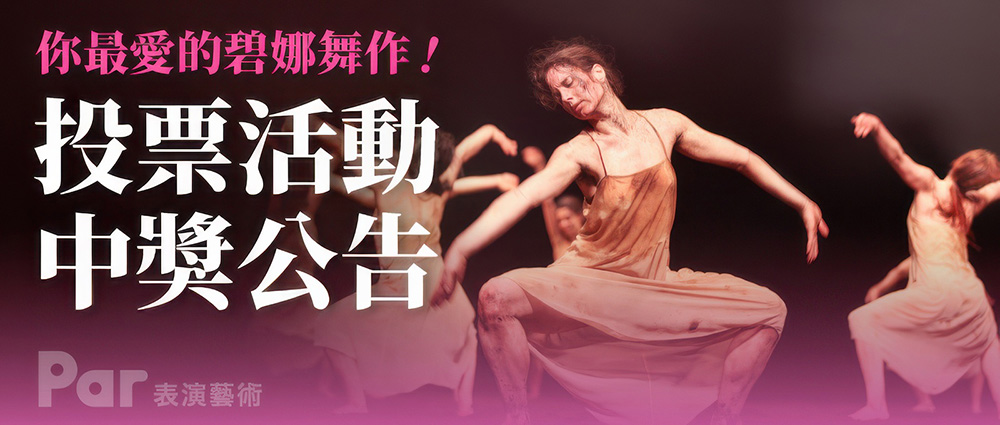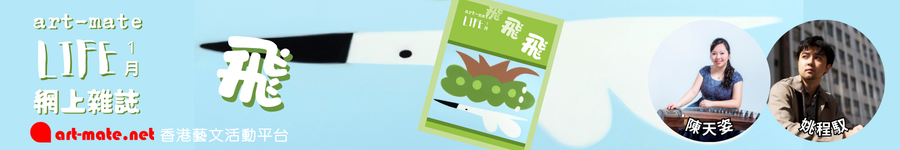1967年6月25日,披頭四(the Beattles)在人類透過4支衛星破天荒同步能讓4億人收看直播的特別節目「Our World」中高唱〈All You Need is Love〉,時值第3次以阿戰爭。1985年7月13日,皇后樂團(Queen)在英國人為衣索比亞饑荒募款的拯救生命演唱會(Live Aid)現身。當皇后樂團的〈Bohemian Rhapsody〉大唱「媽媽!⋯⋯有時候我真希望我從來沒有被生出來!」之時,他們的風采甚至一度掩蓋了巴布.狄倫(Bob Dylan)與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光芒。
以上的人類共同記憶都非常的北方,而且男方。 彷彿北方的男人們是愛與正義的代表,拯救著落後、饑餓、野蠻的南方。令人悲傷的是,演唱會愈辦愈多,當時的非洲卻似乎愈來愈窮。或許作為全體人類的一分子,我們更應該想起的是1970年因為沒去成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而寫了〈Woodstock〉這首歌的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可惜人們總愛說她是男版巴布.狄倫),或是巴布.馬利(Bob Marley)在1978年讓互鬥許久的兩個政黨兼黑幫的頭「表演」出握手言和的One Love Peace音樂會。
甚至,我們應該再往南方一點,來到巴西,遇見 Bossa Nova 的起源。如今一般人以為是在頭等艙、爵士酒吧或熱帶島嶼假日飯店上放送的懶洋洋歌曲,其實在1950年代末期是極具革命性的音樂運動。表面上聽起來舒緩放鬆,簡直像任何廉價的情歌。但其實不論就樂理層次或文化層次,它都無比稀有與珍貴,尤其在那萌發的時刻。
去正式、反文化──Bossa 掀起的巴西音樂文化革命
樂理上,若仔細研究 Bossa 當中和弦的變換,以及人聲與伴奏相互交錯的切分音,會發現那蘊藏著非常複雜的結構。文化上,Bossa 的系譜廣袤而精深:19世紀末形成的森巴、非裔美國人的爵士樂及搖滾樂、巴西東北部 Bahia 地區在地化的加勒比海化非洲音樂,全部都可以在 Bossa 中找到棲身之地。差別在於 Bossa 將原本這些「可跳舞的巴西音樂」,變成了「必須專注聆聽」的音樂。
還有一個重點,使得 Bossa 成為一種革命,那就是除了這些「傳統音樂」之外,在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正式音樂」領域中,一直到 Bossa 在50年代末期出現之前,聲樂那種飽滿圓潤的唱法,才被視為是「會唱歌」的腔調。與此相對,Bossa 掀起的巴西音樂文化革命,卻是極度清新,簡直為世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音樂類型。非洲的樂鼓和阿哥哥(Agogô)的節奏放慢10倍、森巴節奏變成獨奏吉他,而詞曲樂者在腦海中想著海洋、船隻與青春肉體,用一種剛起床不久的嗓音來唱歌。管絃樂伴奏再見,腹式呼吸飽滿唱腔掰掰。就讓我們輕輕吟唱,甚至走音都好。就是要那麼地「去正式」。就是要那麼地「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