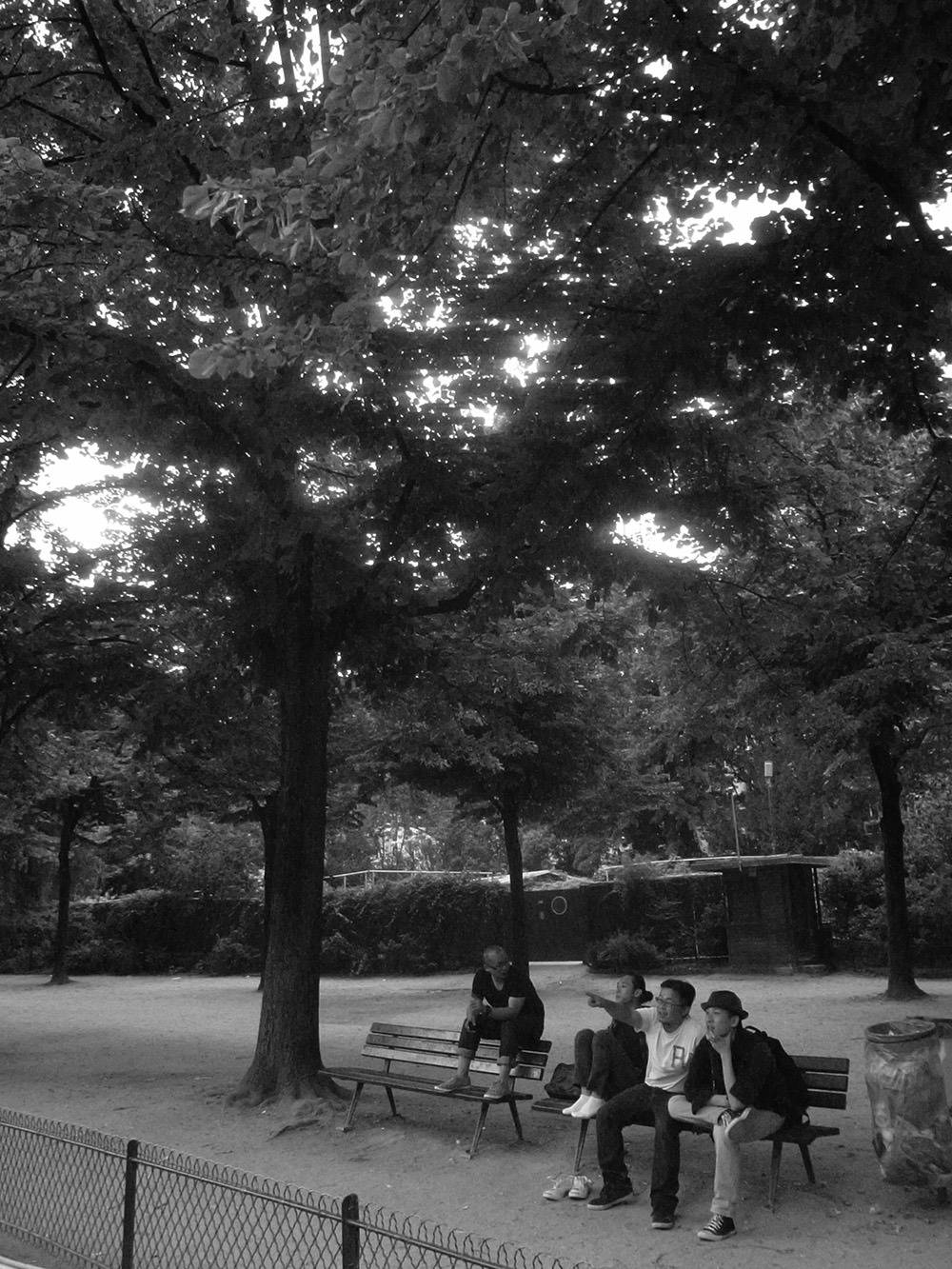黑潮:賴純純回顧展
2025 3/1~5/25
臺北市立美術館
我們多少都看過賴純純的公共藝術,她的作品遍及台灣各處,包括機場、台北和高雄捷運站、國道服務區、醫院、銀行、學校等,流動性的造形和鮮麗的色彩為其標誌,無論基材是壓克力玻璃或是金屬,色彩就像舞動的精靈,在她的注視下一一落了地,化為千姿百態的形體。早在1970年代學習期間,受到指導老師廖繼春啟發,賴純純便已領略到以色彩作為表現主體的可能,以此建構出想像空間。
現於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黑潮:賴純純回顧展」,由張晴文擔綱策展,梳理這位台灣當代藝術先鋒近半世紀來的階段性代表作,從大學畢業製作的油畫《陽明黃昏》(1975),到1980年代以抽象為表現形式,從畫布延伸至雕塑,再擴及空間裝置的創作,1990年代悠遊於東西方媒材、自然物與工業材料之間的變化與創造,賦予物件存在的意義。儘管每個階段性風格有所差異,惟色彩和空間的探索始終是她藝術思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