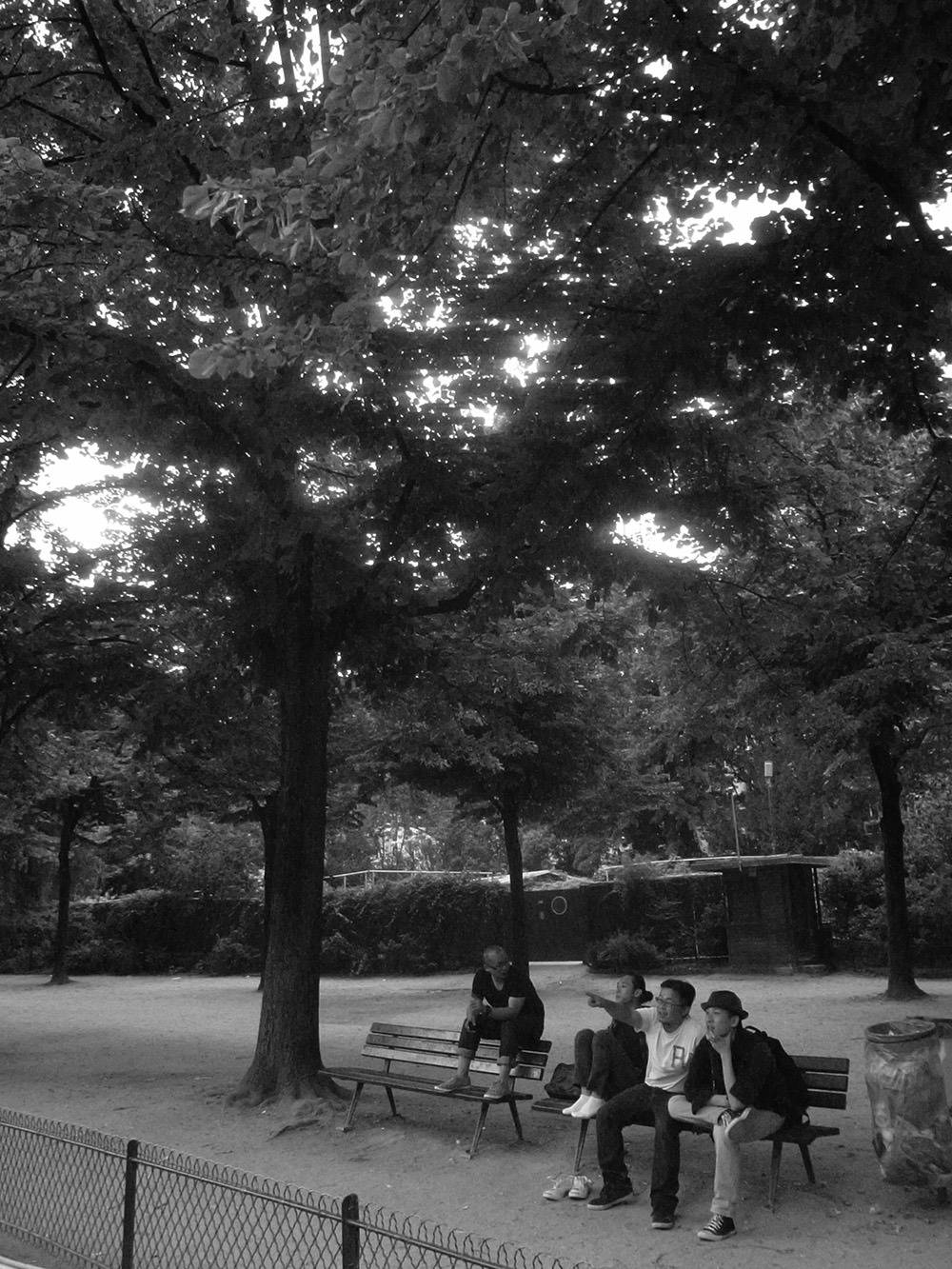張曉雄「青春祭」
2025/4/12~5/24
台北 双方藝廊
大約20來年前就聽說張曉雄在1990年代初期,在北京辦了中國第一次的男體攝影展,寫進了中國攝影史,在他的攝影展「青春祭」終於可以一睹這批1990年至1995年間的攝影作品。張曉雄是捕捉光線與動作的高手,他的攝影與其傳奇生命經驗密不可分,我試著從攝影起心動念的角度來切入。
因為南北越分裂舉家遷往柬埔寨,張曉雄在此出生度過童年,卻在12歲時,紅色高棉推翻施亞努國王,在混亂屠殺局勢下逃往南越,輾轉被母親送往中國杭州避亂,家族四散,唯一一本家庭相簿,保存了中南半島的童年記憶,因為對遺忘的恐懼,啟發了他日後以攝影來保留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