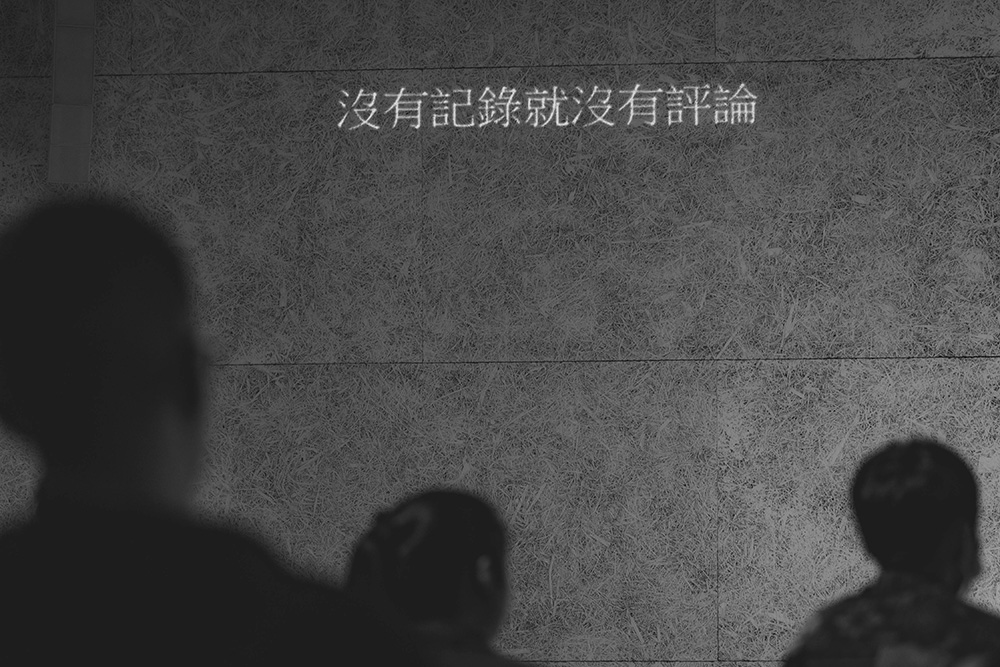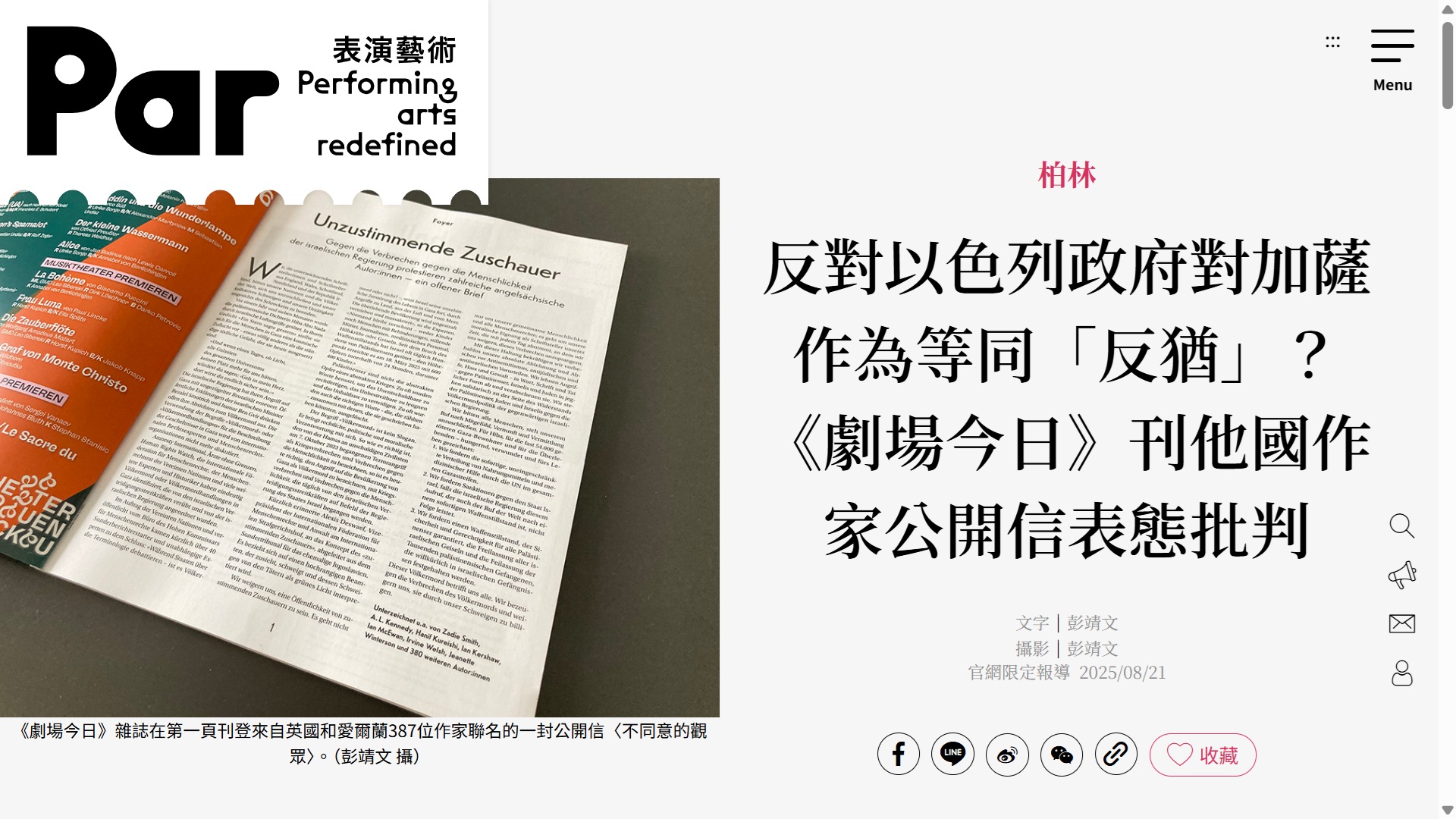超歌舞伎Powered by IOWN《今昔饗宴千本櫻 萬博版》
2025/5/25 台北 中華電信綜合活動中心
2025年5月25日於中華電信綜合活動中心上演的超歌舞伎 Powered by IOWN《今昔饗宴千本櫻 萬博版》,不僅是一場表演藝術的創新實驗,更是一項融合傳統與未來、跨文化與跨技術的多重嘗試。
從沉浸式螢幕設計到AR虛擬偶像初音未來的參與,從九天民俗技藝團的實體加入,到NTT與中華電信合作的全光網路技術(IOWN),本演出不僅重新定義「現場演出」的條件,也為當代跨國劇場文化的未來打開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