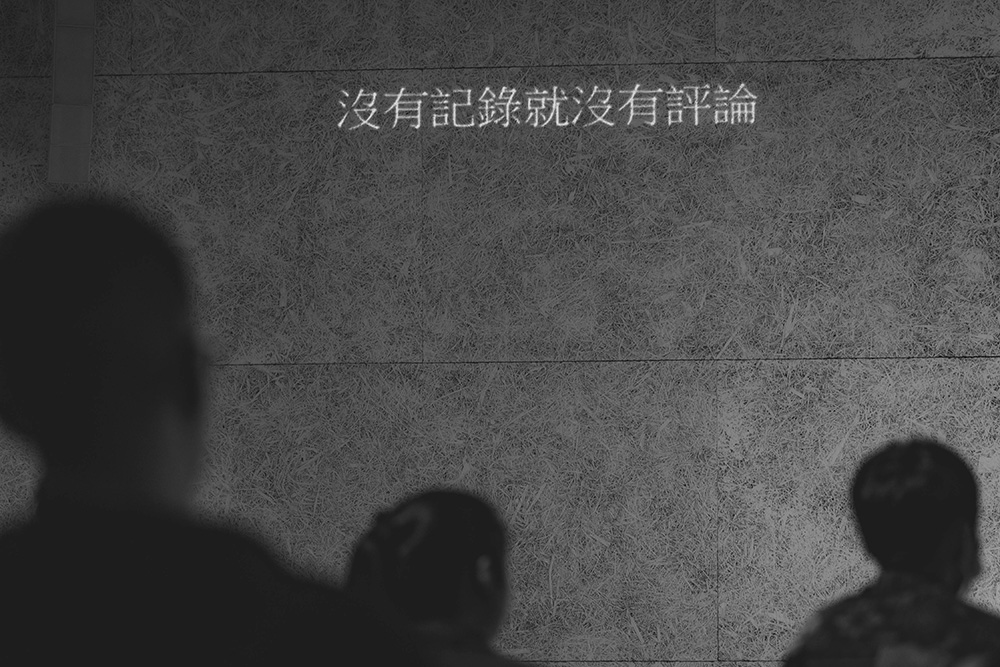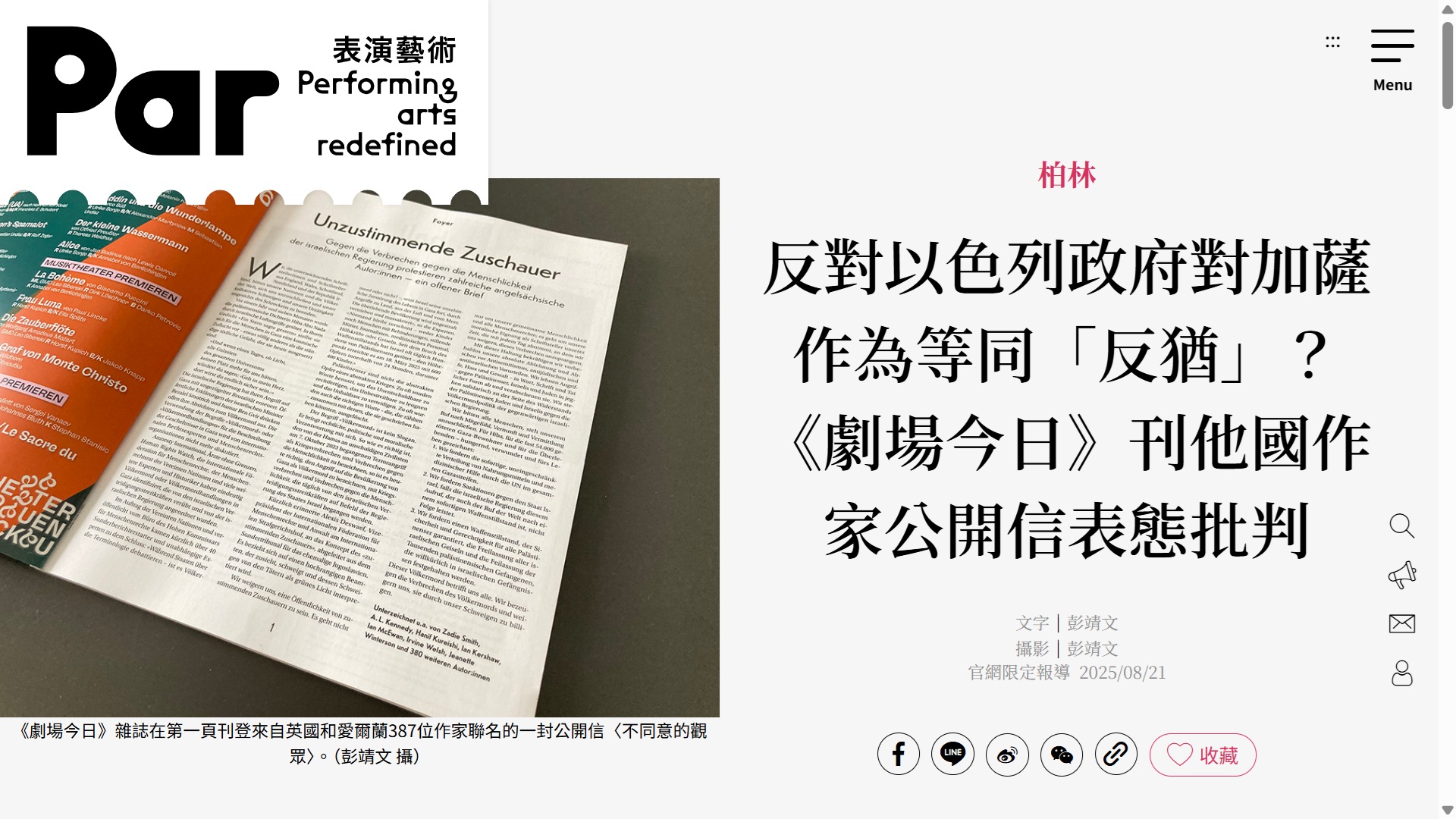VTuber作為數位表演形式已逐漸為世界觀眾所認知,演出內容亦益發多樣化。其中,Cover以女團hololive的偶像化路線,將VTuber打造為虛擬偶像,更成功從日本走向全球市場。hololive曾於去年5月,在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舉辦大型粉絲見面會。成員透過遠距連線參與活動,精心設計表演,包括演唱中文歌曲和即時互動。虛擬角色與觀眾現地交流,成功縮短了虛擬與現實的距離。筆者曾撰文討論,不再贅述。(註1)
2025年1月18日,hololive再次來台,先於下午舉辦hololive meet(筆者未能參與,本文不論),晚上則是hololive STAGE World Tour '24 Soar!。後者海外巡演計畫自2024年8月開始,途經美國、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加開台北場作為最後一站(圖1)。海外巡演採3D動態捕捉演出,成員歌舞唱跳整整90分鐘。演唱內容多為成員的原創曲,同時加入關聯本地的表演。台北場裡,hololive EN Hakos Baelz和ID Kobo Kanaeruo合唱王心凌的《愛你》,複刻原MV舞蹈,喚起眾多台灣人的回憶。以前沒機會去日本現地參與hololive演唱會的觀眾,能在這次巡演裡即時體驗虛擬偶像的舞台演出水準。
從產業面來說,台北站可看作是Cover測試台灣場館設備配合品質的一次嘗試。Cover會下什麼判斷不知道,可至少觀眾這塊應該體感上瑕不掩瑜。VTuber的演唱會有什麼特殊文化意義,值得表演藝術認識?後文將從跨次元、利他與在地全球化的角度,視這次演出為社會學式的文化事件,討論VTuber值得關注的緣由。
跨次元:表演實踐的審美邏輯與獨特性
「跨次元」指的是VTuber本身即為連結多重次元的表演實踐。
VTuber源起出自三次元人類追求二次元形象的實驗,並於相關影像科技的提升下,獲得能與真人動作能力相比擬的表演效果。但是,這段過程至今在硬體設備可負擔範圍內還未達完美。台北場採用通例的正面三片式螢幕,中間大螢幕為主舞台,以固定鏡位呈現演出者全身;左右較小的螢幕專則特寫表演者,讓觀眾能看清演者神情(圖2)。有趣的是,出於可視角的限制,中間螢幕超出一定角度觀看時,會失去大半立體感。換言之,如筆者坐在靠走道側,正對右螢幕的話,中間螢幕裡的VTuber看起來基本上為「平面」動畫。技術的限制值得上升至概念探討。

重點在於,參與觀眾的觀看興致沒有受到太多影響。VTuber因為存在於跨次元的光譜,為動畫、表演者的綜合體。它與粉絲的關係建構和認知極為複雜(註2),讓VTuber表演的容錯率與情感代入的空間相當大。如果說進入網路時代,虛擬與真實界線愈來愈模糊;VTuber形成的文化實踐,代表了人類的認知可以同步整合多重時空的曖昧不明。換言之,VTuber所在的時空次元為何,本身已是見仁見智的光譜。VTuber在螢幕上是立體或扁平;極端點說,是否為即時遠端連線演出,又或者為預錄,都不影響它引發觀眾情感的能力。
因此,VTuber就算3D化,仍然具備不同三次元的審美邏輯。真人的肉身形象有著難以複製的特異性,打個比方:筆者不會想像、打扮成真人女偶像,因為性別差異,於自己難以跨越;但是cos成支持的VTuber偶像,有機會倒想嘗試。亦是在此邏輯上,不分性別年齡,VTuber粉絲自在地打扮成自己的「推」。乃至於VTuber的衍生形象,如遊戲中的角色扮演造型,也可以是粉絲致敬的樣態(圖3、4)。種種實踐都會遞迴給VTuber,強化其獨特性,乃至催生出有別於三次元真人的不可替代之情感經濟。

利他:粉絲自製物品的無償交流
有這層情感價值,才能理解粉絲裡會出現各種無償的應援活動的理由:「利他」關係明顯存在於VTuber的產業生態裡。除了Cosplay,場外可見粉絲群自主提供偶像週邊,組合而成的交流祭壇。更有為數不少的粉絲自製小卡、小物,在全場分享給觀眾,無關對方支持的VTuber是誰(圖5、6)。亦有粉絲透過網路串連募款,集資製作花籃。在虛實難辨的大詐騙時代,很難說這類給予陌生人的善意和信任容易做到。

無償在此情境成為一種無國界的溝通方式,hololive則是各地人流的共同語言。人們願意花錢到現地商業活動無償付出,是因為能得到更多無形情感回饋。
hololive除了以偶像IP聞名產業外,其「箱推」(註3)文化亦是各方傾慕的營運特質。意即觀眾雖然有各自最支持的偶像,與此同時,hololive整體亦為受眾愛屋及烏的應援對象。原本真人偶像經營重視的各式數字,在虛擬偶像身上雖然仍存在,可是在Cover沒有成為檯面上的評比標準。互助互惠是hololive的共同默契,後疫情數年期間,使其箱推感益發穩固,成為全球粉絲對此企業的信賴基礎。演出者以身作則促進粉絲間的良性循環,替線下現實活動帶來難以忽視的人流(圖7)。VTuber作為新興娛樂產業朝不保夕的變動性,更促使hololive粉絲積極以行動為自己的「推」留下記錄。

在地全球化:核心策略中的文化流動與關係建構
VTuber成為次文化生態的一種後,各國都出現自己的VTuber實踐。然而,像Cover這般將自家VTuber推廣至海外各地,並廣獲群眾參與的產業案例卻極為稀少。延續去年holo meet的分析論點,加上今年巡演狀態,可以說「在地全球化」是hololive的核心戰略。
日本次文化批評曾有「無臭性」一詞,意指創作不帶特定文化色彩,以助作品跨國流通。其實,此概念已過時。在hololive裡,日本二次元文化變成其核心。就算是EN、ID的成員,多是一定程度上熟悉日本動漫遊戲文化的表演者,能在直播中運用相關文化元素。至於hololive的VTuber形象設計,多以符合觀眾熟悉的日本二次元美感為主。簡言之,日本VTuber成為其二次元文化的匯聚點,Cover以此文化資本開拓海外市場。
隨著日本二次元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hololive的日本化本位搭配上因地制宜、積極結合異文化的表演設計,為其帶來眾多全球交流的動態可能性。例如,台北場裡,角卷綿芽和AZKi的MC時段,她們以台語向觀眾問好,亦談及台灣食物及101;成員亦多少在台上學習、使用了華語單字。
當然,如此「套近」的操作能以很商業的角度來批評,看其為人人都能做的表面工夫。然而,回到VTuber以直播為本職的活動內容而言,hololive確實直接面對世界各地觀眾,透過翻譯持續和不同語言文化的支持者交流。粉絲也在此基礎上,積極主動學習日文、英文。VTuber台北場的MC幾乎都日、英文為主,沒有翻譯,亦未見有人不滿。有此前提,她們展現對現地語言、文化的了解意願,才能正向視為與受眾的好客互動。
所謂「在地全球化」緣此不只是抽象的文化流動,亦是具體的關係建構。hololive VTuber海外巡演的現場實踐,讓她們與支持者的跨次元連結更為緊密。VTuber仍是次文化,但它自身與社群的開放性與多樣化正快速傳播世界,供給粉絲無可取代的另類現實。
註:
- 王楷閎:〈虛擬與真實,並非二選一的選擇:Holo Meet Taipei:數位時代的偶像活動〉,《PAR表演藝術》官網限定報導,2024/06/18。
- 筆者曾有論文討論。參見王威智:〈展演VTuber:編織現實與虛構的同伴物種〉,《中外文學》53卷3期(2024年9月),頁213-252。
- 「箱推」是日本偶像文化中的術語,指支持整個偶像團體(如 hololive)所有成員的粉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