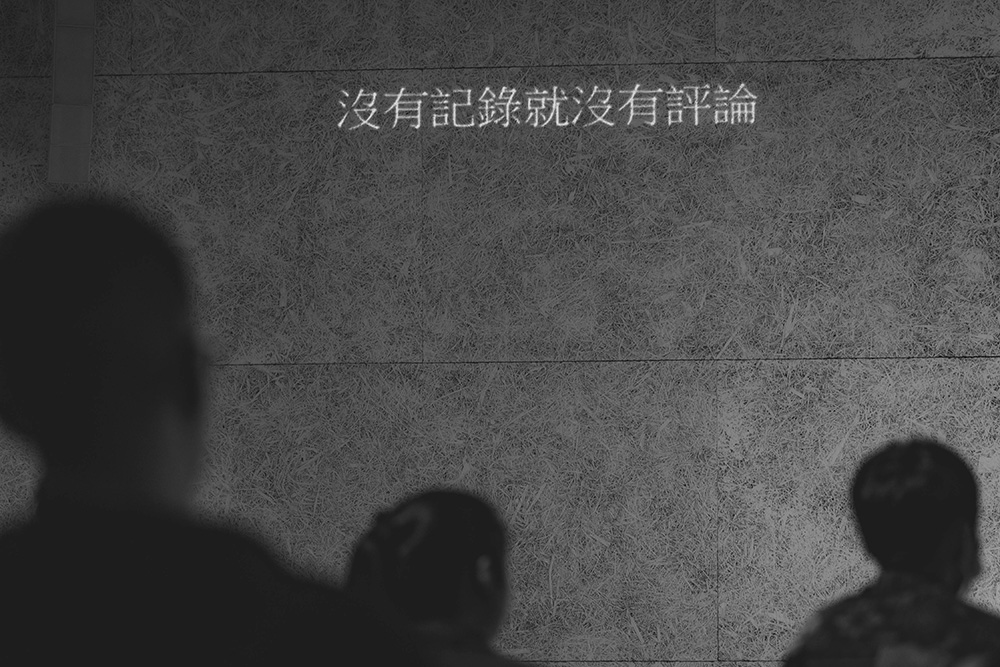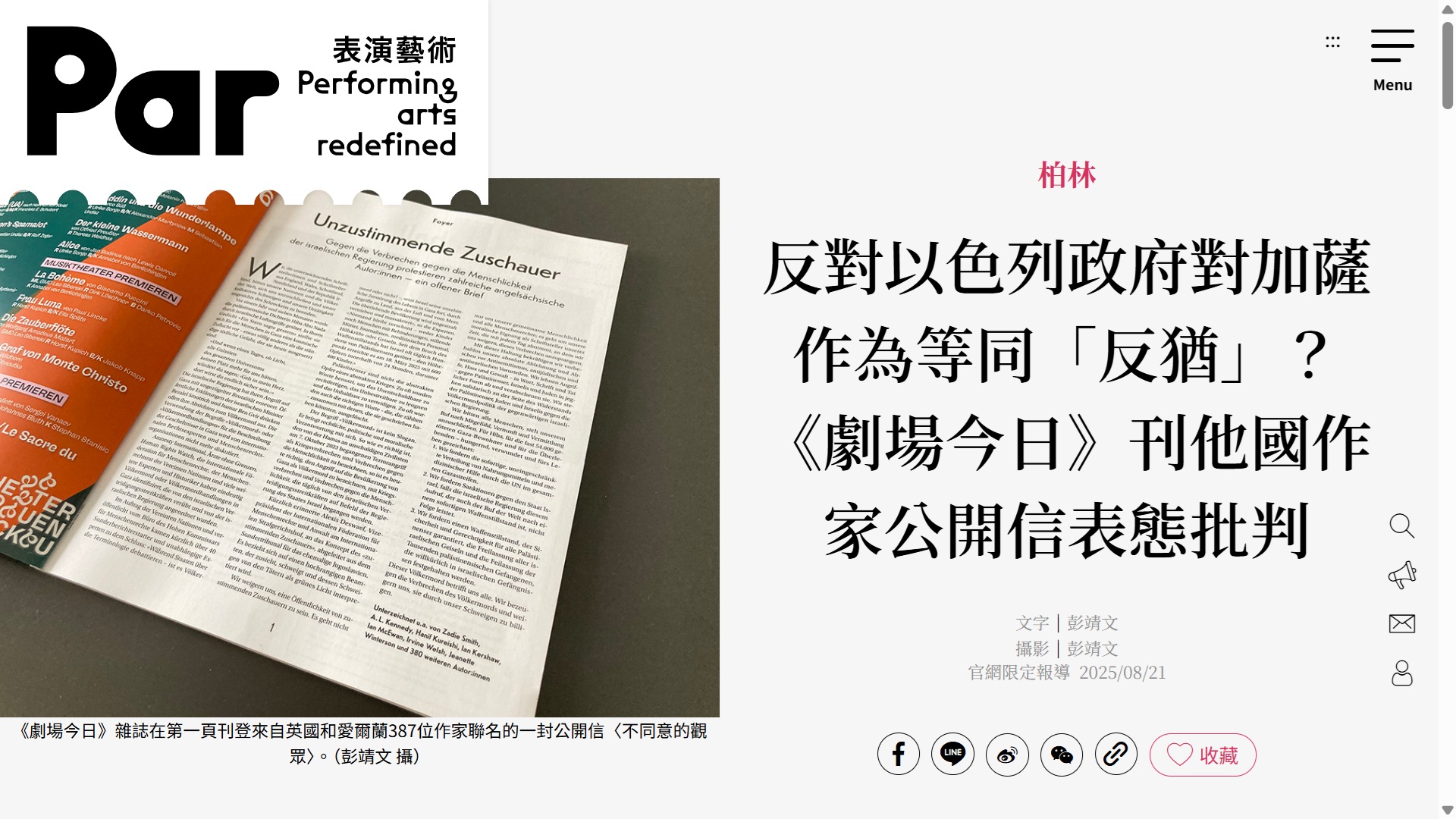年前,國民黨團要求文化部停止「轉型正義」工作,並以「扭曲國家對重要歷史人物紀念的意義」等理由刪除、減列與凍結文化部預算。其他如文宣費全數刪除,黑潮計畫共砍4,000萬,公視則因台籍戰俘的歷史劇《聽海湧》遭指涉扭曲史實,補助預算砍2,300萬、凍結25%。一時間,文化人與導演拿補助是政治酬庸、為特定意識形態宣傳等說法甚囂塵上,「要飯說」更讓藝文圈為之譁然。
作為曾經製作不止一個白色恐怖歷史劇場作品,並曾獲得相關政府補助經費的劇場導演,我認為現在是個適當時機正面回應這樣的質疑:國家是否應該補助並推動「轉型正義」文化活動?不僅是立委與網紅對此有所抨擊,表演藝術圈近年亦有相關質疑。劇評人王墨林近期在《PAR表演藝術》官網的文章中指稱,時下白恐戲在執行當局「轉型正義」政策的宣導下,將歷史事件當成一種消費的政治(註1)。類似的觀點,劇評人郭亮廷在去年亦有撰文提及(註2)。這些評論預設了一個立場:創作者只要接受了和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有關的補助,作品就不證自明地服膺官方史觀,或淪為國家政令宣傳。
首先需要回應的是,在這些再現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品中,許多被認為是「史觀」的問題,實際上往往是「美學」的問題。處理白色恐怖歷史的劇場、影劇創作者,在大多數層面與一般創作者並無二致,創作與敘事的取捨若有任何標準,那必然是關乎創作者在實踐什麼樣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