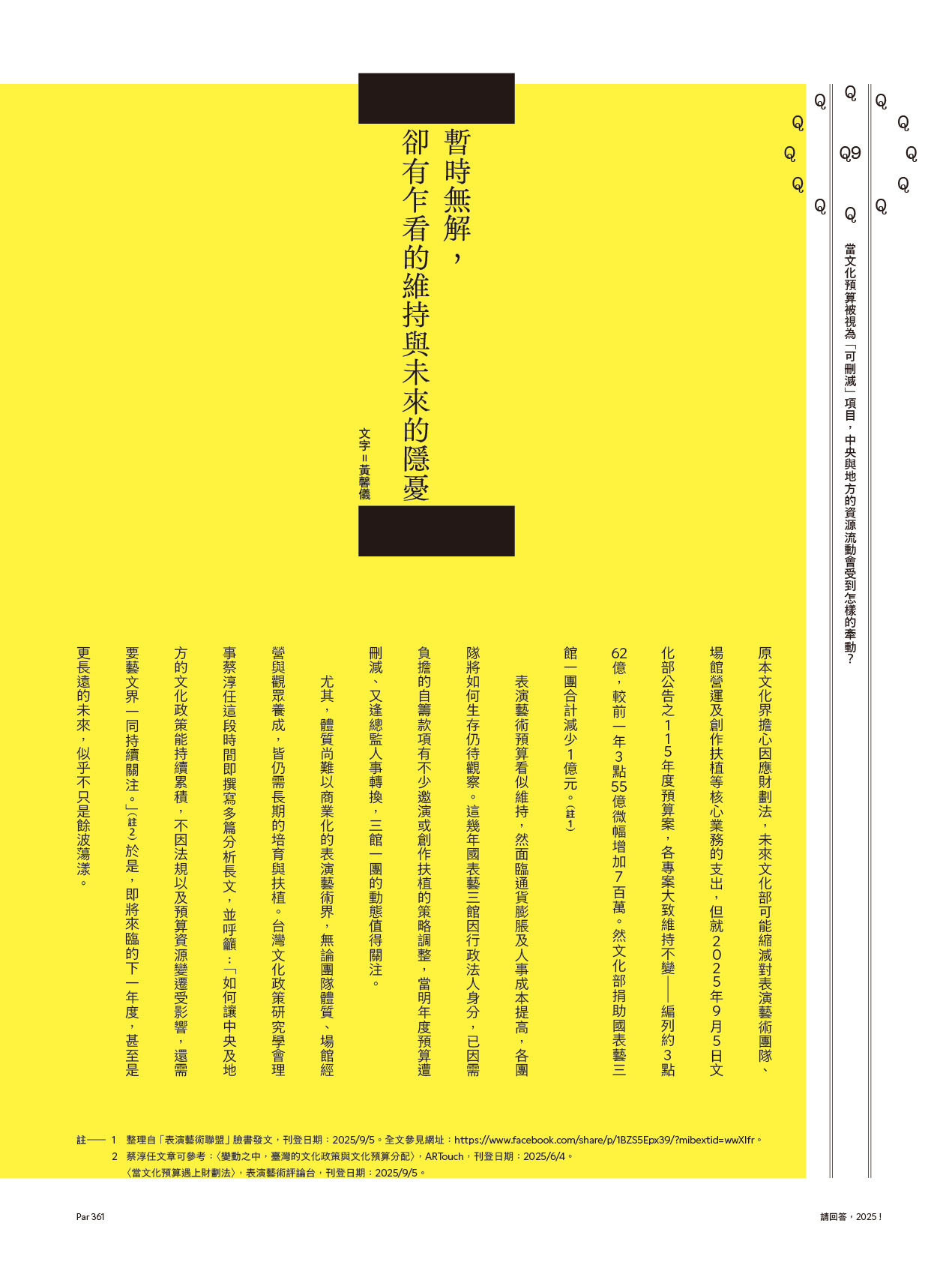國光劇團《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青春版
2025/6/7 14:30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王熙鳳被視為《紅樓夢》中極具權力與手腕的女性角色,因此觀眾在閱讀文本時,往往容易以「陰險狠毒」、「心狠手辣」的標籤去框定她的形象。那麼,如果觀眾帶著這樣的第一印象走進劇場,青春版的王熙鳳是否也會被固著在某種「程式化」的想像中,而失去改變的可能?
打破標籤的王熙鳳?
在青春版演出中,王熙鳳的情緒轉變打破了這樣的預設。當她面對情感背叛時,並未失控地怒罵,而是冷靜地謀劃。她以寬容大度的姿態重塑自我形象,讓眾人誤以為她為了家庭、為了丈夫,成了一位體貼夫君、賢慧的夫人。但這樣的善意只是表象,她真正的心思則是緊密布局、步步為營:從放任街坊鄰居知曉風聲,到用藥使尤二姐失去孩子,再到最後設局讓秋桐借刀殺人,每一步都是為了保留權力所做出的自我保衛。
或許放在今日的道德觀來看,她的手段令人質疑;但在那樣的時代背景裡,王熙鳳的選擇無疑是女性以理性與謀略,去應對體制的一種方式。這樣的角色演繹,讓我們看到的她並不只是「機關算盡」,而是一個能感受到愛與憤怒、傷與狠的活人。
這次青春版所呈現的,是一個重新被詮釋過的王熙鳳。正如魏海敏認為「在現在這個時代,推著他去傳授下一代的王熙鳳,不是魏海敏。」(註)當戲曲角色若僅以傳統方式複製,就容易流於形式;而當代演員重新進入角色、注入自身經驗,便有可能讓「她」再次活過,成為既經典又貼近當代的王熙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