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 巴黎
共體時艱或捨本逐末? 法國表演藝術界面臨撙節窘境
2月底,法國政府投下震撼彈,宣布年度總預算必須縮減共100億歐元,以彌補經濟負成長帶來的虧損。儘管文化部只占刪節總額的2.4%(註1),卻造成表演藝術界前所未有的壓力。 中央的撙節勒令 對剛走馬上任的文化部長哈希妲.達狄(Rachida Dati)來說,這波大幅度的撙節政策無疑是重大挫敗。原本大家期望她透過良好的政商關係,為文化產業爭取更多資金,但沒想到卻得面對開源節流的難題。削減預算案似乎只是總統、行政首長與經濟部長的決議,這突顯了政府權力的集中化,部會首長根本沒有協商空間。更令人擔心的是,這次修正預算似乎只是首波海嘯,6月內閣還得面臨另一次財政整頓。 此波衝擊下,受創最深的莫過於2個承先啟後的文化產業古蹟維護和創作補助(註2)。達狄聲明,她會動用文化部的預備金補償三分之二的虧空,並運用轉移法令,挪用其他計畫的補助費用。她也表示不會刪減地方場館補助,以維護她推動的鄉村文化平權政策。然而,由國家直接資助、監督的藝術機構卻面臨空前的財務危機。
-
 國際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國際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直面時代的當下 勇敢的藝術實踐
2024布拉格Bazaar藝術節今年是布拉格本地藝術節Bazaar Festival 的10周年紀念,於3月15日至25日舉行。這次的主題聚焦在「勇敢的藝術實踐」(Courageous Practice),集結中歐和東歐各地的藝術家,呈現多元形式的作品,包含實驗舞蹈、跨領域混合媒材演出。每個作品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創作方式,尤其著重藝術作為與社會互動的媒介。藝術節單元包括主要節目,和駐村作品呈現(Saturday Bazaar),以及講座、工作坊、讀書會、野餐等活動。除了作為展演平台,也開展交流的空間,讓不同社群可以匯流。觀眾和藝術家可以分享身體力行的創作、思考,和生活方式。 10年前第一屆的Bazaar藝術節是源自歐盟協會和歌德協會共同資助的藝術節「Idendity. Move!」,包含13個西歐和中歐國家參與其中,在不同城市同時有演出發生,主要為舞蹈和肢體劇場作品,探討身分認同的主題,得到相當不錯的觀眾回饋。當時布拉格的Alfred ve dvoře劇院作為參展單位舉辦了第一屆 Bazaar藝術節。Bazaar是市集的意思,以熱鬧的市集作為概念,打破舞台和觀眾之間的分隔,任何人都可以買賣交換點子,由多個小型演出組成,結構較為彈性和流動。藝術總監Ewan McLaren希望可以繼續發展這個形式的藝術節,於是正式開始了Bazaar藝術節,以布拉格為基地,聚焦在中歐和東歐相關脈絡的主題。 訪問Ewan和製作人Barbora Comer 時,他們提到Bazaar藝術節的精神是不以完整的作品為最後目標,旨在呈現創作的過程和藝術作為回應政治、環境和社會議題的表達媒介,邀請觀眾進入討論和評論的空間,希望在藝術節之後仍然延續社會參與。今年的主題「勇敢的藝術實踐」在定義上尤其開放,囊括女性主義、烏俄戰爭的網路現象、人和物與現實的關係等等,在策展上呈現各種挑戰既有價值或揭露社會問題的作品。
-
 生活 藝@書
生活 藝@書《城市如何文化》 誌記香港目前階段性的發展和變化
在反送中運動與世界疫情趨烈的當口,茹國烈(編按)出走香港。他以客觀靈敏的眼光,透過遊歷歐亞主要城市所寫下來的體會與觀察,即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待「香港」這座城市。他有意無意地,讓自己針對每座城市的寫作,保持著一種理性與平衡的距離;不為批判也不是診斷,更不是莽撞和衝動的推崇,整體而言,本書相當有條理地歸納了這些重要城市的多層次社會發展,並且他以BEAM的「文化光譜」觀點(註),提供他認為當代城市需要這些人類生產的「動能」,作為建構文化事物與生存的基本要件。 作為一本誌記香港階段性發展的「情書」,茹國烈從質性概念出發進而量化的分析,能讓讀者更深入理解香港各區域「地區行政架構」的發展和構成。他採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供的「文化專題指標」,對照「文化光譜」的類別,標誌香港各行政區域的「文化密度指標」,以及不同區域之間彼此的差距。例如油尖旺區、中西區與灣仔區,是香港文化密度指標總數最高的3個區。油尖旺區作為都市的中心之一,便與遠離中心的元朗區,分數差距超過10倍。 從規劃都會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本相當具有理念的文化政策建言書。身在台灣,此時讀到本書的「香港篇」,真是混亂時局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然而,香港都會化的本質,除了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背景,還有特殊的政治性、地理性,甚至冷戰後地緣政治角力下的權力象徵,這讓香港構成的內涵顯得極為複雜。相反地,「文化光譜」折射下所顯示的城市理念,便又是那麼地珍貴且難得。我相信作者試圖提醒我們的是,每座城市均有它特殊的發展體質,或說根據時間和歷史所形成的「文化光譜」,絕非能以一個標準作為普遍性的價值衡量或政策做法。「文化光譜」所強調的都會主體性,不是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打造的平等或不平等;作者不強調(或許也不認為)都會文化建設與意識形態和權力介入相關,他循循善誘地說明我們可以從「文化光譜」看到更多具體的城市文化理念,而那正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關於西九文化區的經營,本書作者著力甚深,竟選擇在落成完工之後離開,顯然是更珍視自己看待人事物的客觀距離與眼光。他針對戲棚相關的交際社群,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在建設初期便刻意為戲棚區打造更多可以容納市場交易的空間。這種由上而下的機構空間規劃,值得我們思考
-
人物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演員
王肇陽 表演,是我衍生出來的東西
「這裡讓我非常自在,可以放鬆地聊、自然地說出我想說的事情,有些場合我不行,會顧慮很多,在這裡不會。」王肇陽坐在中和華新街的清真雲南小吃店裡,邊啜飲著奶茶邊說。一向喜歡小吃與路邊攤的他,2023年結束馬來西亞與台灣合製的《同棲時間》吉隆坡演出後,仍著迷於那裡的食物風味與生活節奏。 王肇陽,彰化人,37歲天蠍座A型,母語台語,INFJ提倡者(編按)。自我介紹時會把職業定義為「自由演員」,不是劇場、影像,或是任何其他特定類型的表演者。「自由」聽來無邊無際,但認識他的人就知道,這兩個字若發生在他身上,那就必然代表著深思熟慮後的選擇。細數他的表演經歷,若從2011年退伍後第一檔正式售票演出《迷彩馬戲團》開始,王肇陽在表演領域的資歷已近14年。 追求有限度的自由,讓表演成為一件工作 現在的王肇陽,似乎少了一種憤怒感,像是在某些轉折後,來到職涯人生的另一種階段。 「最近幾年聽到有人說,表演其實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現在對我而言,好像比較是這樣子,是一種自我追求,純粹是我喜歡透過表演,得到一種很自由的感受。」他突然切換語速模式,興奮地分享從日本旅行放風回來的見聞,那是一間在樂迷之間很熱門的爵士俱樂部「Blue Note Tokyo」。講起這個難忘的夜晚,他慵懶的身體瞬間充滿能量。他與朋友是臨時起意的造訪,那晚的主要表演者是美國爵士鋼琴家Billi Childs,搭配3位不同國籍的樂手演出。這是王肇陽第一次到專門的場地欣賞純粹的爵士音樂表演,看完後激動得難以名狀,感動不已。爵士樂由樂手的個人風格出發,同時探索樂曲的各種可能性,在台上表演者彼此有基礎共識的狀態下,遊走在音樂的語境裡,與同台夥伴靠近或比拼,沒有過多的預設,卻處處是專業。 這般帶著規則卻同時擁有無限自由的演奏方式,喚醒王肇陽心底對於表演理想的圖像。「我坐在台下,默默覺得,能夠這樣跟自己視野、想法差不多的人一起演出,真的是好像在飛!這種機會真的太難得了,我好希望以後的合作都可以像這樣,這是身為表演者應該都很想追求的事情。」 能夠好好表述自己在職涯所追求的狀態,當然也曾經迷惘過,在這個產業誰沒有呢?剛入行不久,王肇陽便順利接到國際大型製作的巡演,有資源的劇組把每
-
 評論 回想與回響 Echo
評論 回想與回響 Echo虛擬與真實,並非二選一的選擇
Holo Meet Taipei:數位時代的偶像活動2024年5月11日,日本Cover株式會社旗下女性虛擬直播主(Virtual YouTuber)團體Hololive production,至台北流行音樂文化中心舉辦粉絲見面活動。參加成員按演出順序有Hololive En三期生Fuwamoco、Hololive ID三期生Kobo Kanaeru、Hololive Promise(EN二期生)Hakos Baelz與IRyS、Hololive En一期生Gawr Gura。活動細節台灣眾媒體均有報導,本文不再重述,而是針對此活動提出觀察與評價,討論為什麼值得我們注意? 遠距跨國商業模式:VTuber實體演出的重要性與優勢 Hololive已經在不少地方(美國、台灣、韓國等)舉辦過類似粉絲活動,足以證明以往大眾認為VTuber主要活動在虛擬網路世界的思考,事實上與發展現狀不完全符合。 以Hololive來說,粉絲實體見面會明顯為其全球性的戰略布局。為什麼實體重要?VTuber在網路上可以提供觀眾情感和娛樂的慰藉,但是廣義表演藝術最為迷人的「現場性」,仍然只能在特定而且有限的時空中發生,而VTuber作為一種數位表演亦難以跳脫這種渴求現場性的邏輯。舉辦各種規模的粉絲見面會和Live演出,因此不只是一種經濟考量,更是VTuber此一媒介自覺要與各種傳統真人表演藝術展開競爭的嘗試。 果真如此的話,VTuber有什麼優勢能與真人相比?從創作面來講,VTuber具有跨越時空限制的科技環境。是以技術上,這次Holo Meet Taipei的VTuber全在自己國家(日本、美國、印尼)遠距直播,而於台北的舞台上與眾人同樂。借助網路與相關直播設備,在VTuber的世界中,全球化是可見的實踐,創作者可以無視地域限制進行表演,相對節省眾多人力與設備移動成本。如此遠距跨國商業模式亦只有VTuber這樣二次元的媒體才能達成。 然而,進一步可以思考的是,這方面的直播或舞台技術當然不是Cover株式會社獨占,為什麼Hololive能在全球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觀眾為什麼願意花大錢去看虛擬偶像的表演?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實際演出來談。
-
 專欄 抵達終點左轉
專欄 抵達終點左轉為什麼要一個人站在_裡?
該說是「那裡」還是「這裡」,我愈來愈不確定了。 如果是那裡,我就在看是觀眾也好,寫字抒發也好,那代表了距離。如果是這裡,我是被看在演,或導,成了一個標靶(target)。這篇文章我想談單人表演,卻發現自己的定位都在暈眩。 一直對於渴望做solo的人,充滿好奇。成為標的或許是表演的某種必然,但成為舞台上唯一的標靶是另一回事。我曾以為的戲劇,是一種編織,人與人與事件與物的串動。我以為的戲劇不是源於一個議題亮點,除非那是創作者腦袋裡的靈光。再之後,以為成了作為。羞恥心一勺勺挖起來換,反應過來才發現那原來是消耗品。 第一次注意到的靈光,是《Fleabag》(譯作:倫敦生活、邋遢女郎)。我先看了影集,然後看回舞台劇錄影。英文台詞跟不上,捧著劇本追,前後看了不下十幾遍。我拿《Fleabag》影集當教材,每次都失敗學員跟不上台詞,搞不清楚角色之間暗潮洶湧,不懂要看什麼。儘管我都拿第一集用,第一季女主角開場就打破第四面牆,我談這被用爛的「形式」,如何從舞台過度到鏡頭,並在之後賦予格外的意義,建構男女主角的關係。更愛反覆共讀第二季的第一集,那整頓飯吃得驚心動魄我拆解鏡頭數,視線分析角色。以及演員如何講話但不停止動作。 因為太喜愛,所以教不好。我總是現場最興奮的那個,宛如主創Phoebe的狂粉。其實最想談的核心是「改編」,可是每次到了最後,看著被學員們被轟炸過的表情,我只能輕巧帶過。改編是商業技術,是編劇與導演的工作,不是原創。觀眾只能奢求對美好故事的經驗不會被取消就好,能二次享受是宇宙福氣。 近幾年IP化的浪潮不斷,我總是納悶這浪為何一直打在作者(尤其是文學小說)頭上?影視化是轉譯,原著夠好就有外譯擴充的潛力,若一開始就用中英交雜的晶晶體寫,再翻也依然語意不清。《Fleabag》的成功,讓我對「獨角戲」有了全新的好感與其說單人表演是充斥著演員技術展現的意圖,有沒有可能,更大的企圖是:他╱她真的好想談一件事? 於是「演員」這個職業集合,成了「人」。那這跟脫口秀又有什麼區別呢?我想起以前在英國學表演時,班上一位丹麥女同學的畢製獨角戲,就是在探求這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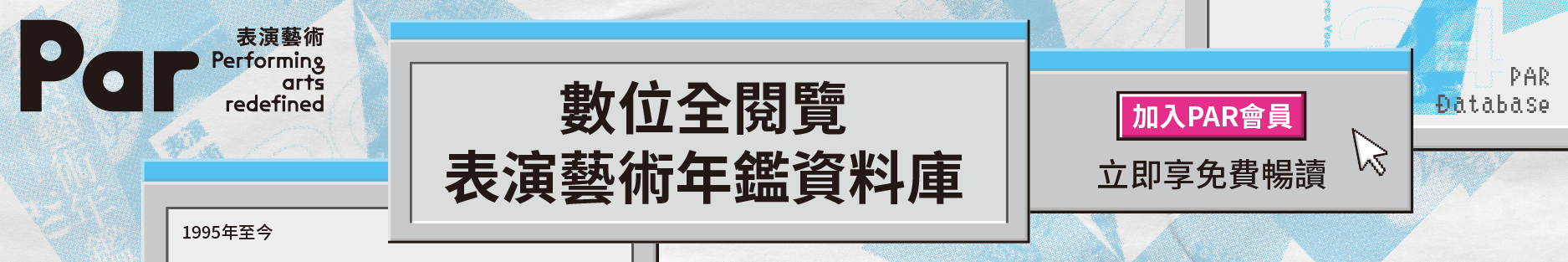
-
 國際 檳城
國際 檳城檳城兩劇團 揚威馬來西亞「戲炬獎」
來自檳城的兩個劇團揚威馬來西亞第19屆「戲炬獎」!由Noise Performance House製作的兒童劇《我的醜醜鴨》,以及剃刀實驗劇場製作的《我的末日青春小鳥》分別以11項和9項提名成為大熱門,最終獲得當晚頒發的14個獎項中的8個。《我的醜醜鴨》奪得最佳女主角、原創劇本、原創配樂和造型設計等4個獎項;《我的末日青春小鳥》則拿下最佳導演、舞台設計、平面設計和網路票選最受歡迎戲劇作品,同樣以4個獎項平分秋色。加上憑《謝師會》奪得最佳男主角的李奕翰同樣來自檳城,這回檳城劇場人可謂大豐收。
-
 人物 紀念大師 In Memoriam
人物 紀念大師 In Memoriam卓明,那「鑿光的人」——紀念Star
終究,現實是一場幻化的景象,相似一齣戲在舞台上的出現,在時間帶上某個時刻,跟現實中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相遇,與舞台上一個角色相見,有人是與自己連接了一生成為舞台的故事,或劇中一個角色讓自己進入孤獨無語的現實世界。我們面對當下其實看見的是一個未來,如同Star(註)長眠在這座山頭。 6月的陽光並不刺眼,放眼望去漫山一片蒼鬱,倒顯得梯田似的花葬區彌散著虛假的死亡氣息。是的,這片風景總是令人感到死亡的不在場,連Star的骨灰下葬於此看起來也不真實,更何况我們不僅找不到他「林啓星」(本名)的名字,更不知道如何丈量他的落葬之處。他76歲的一生就在這方寸之地的「無名之墓」劃下了句點。 在「林啓星」所謂的一生,我們自他20歲進入軍校即已相識開始,近乎50餘年間,或同棲於一屋,或分處異地,我們始終連繫不斷。50餘年前,Star與我因翻越軍校圍牆被逮住,雙雙送進禁閉室,講好就此退學離開,於是他費盡一番折騰終於回到平民身分,而我則因半夜聽到父親為我如此不才而痛心哭泣,心一軟又回到軍校。此事直至公祭後與他的南部學生翠香聊到故人往事時,才知在Star心中卻是我對他造成了一種傷害,他深深認為這是我對之間約定的背叛,而我也自此在軍隊苟且了14年。
-
 國際 新加坡
國際 新加坡各大藝術節5月啟動 跨領域╱跨媒介作品繽紛上陣
今年各大藝術節如期進行,濱海藝術中心的「另藝派」(Flipside)於5月31日至6月9日進行,一如往年,為觀眾呈現雜技、偶劇、喜劇、肢體表演,有的藉此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有的進行關於人與科技的狂想。 今年「另藝派」以物件劇場居多:來自泰國的《Ta Lent Show》以家居物件進行即興表演;來自法國的《Stars in Our Eyes》以日常物件進行兩齣短劇,激發觀眾的想像力,引領觀眾一下遨遊宇宙、一下進入機器服務人類的未來世界。物件劇場使得人與物之間的界線模糊,讓藝術者與觀眾得以「跨越」,發現表演的更多可能性。「跨越」讓想像力得以馳騁,對生活更加敏銳。 「新加坡國際藝術節」(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SIFA)也於5月17日至6月2日上演,今年的主題是「他們宣稱」,邀請觀眾為所有與自己抱持不同信仰與理念的群體敞開心房。與往年不同,今年的藝術節多了「Little SIFA」,即為適合親子共賞的戲劇節目,包括偶劇、戶外演出、製偶工作坊。另外,今年也增設了「明天、明天」系列,邀請新加坡各劇團呈現小品演出(work-in-progress)。
-
 國際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
國際 四界看表演 Stage Viewer形式凌駕人性、舞蹈切割劇場
波赫士.夏瑪茲「自由」顛覆碧娜.鮑許「大教堂」接任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總監近周年,法國編舞家波赫士.夏瑪茲(Boris Charmatz)終於交出首份成績單《自由大教堂》(Liberté Cathédrale)(編按)。在概念編舞的影響下,這個風靡全球長達半世紀的舞團是否仍延續碧娜.鮑許(Pina Bausch)細膩雋永、深入淺出、以人為本的舞蹈劇場脈絡?新任總監是否能透過抽象、解構、有機、實驗的創作美學,開展出經典舞團的當代風貌? 為了繼往開來,只能改弦易轍 很少有人會把教堂與自由聯想在一起。教堂,作為宗教集會的場所,意味著莊嚴的氛圍、神聖的信仰、充滿規範和約束的儀式,甚至是西方文明發展的基石。相對於夏瑪茲過去舞作著稱的狂縱不羈、標新立異、不拘一格,這些嚴肅的象徵完全背道而馳。對編舞家來說,結合這兩種迥異的概念,正反映出烏帕塔舞蹈劇場新舊交替的當下處境:「過去教堂曾把舞蹈譴責為罪惡,如今自由的風氣卻映照出這種局限。這個舞團承載著無數傑作的歷史重量,今日它該何去何從?我認為要重獲自由,唯有另闢蹊徑,讓革新反過來滋養曾經擁有的一切。」(註1)夏瑪茲認為,若要突顯鮑許歷久彌新的價值,必須超越以她為名的經典框架,嘗試別出心裁的創作方式。 對夏瑪茲而言,教堂不只象徵著宗教或文化的不朽價值,它的希臘詞源ekklsia本義是公民集會,突顯出當下、現場、聚集的意涵,如同劇場。他想匯集不同的體態,讓舞動的群體建構出一種「沒有教堂屏蔽的神聖集會」(une glise sans glise):「我來自一個無神論的共產家庭。共產黨並非宗教,但它是一種帶領人實踐理想的信仰,擴延至藝術、行動、公開言論等不同領域()我對教堂充滿各式各樣的質疑。但它也是一種關懷人性的靜心之所。這座建築並沒有特殊的實用性,但它有嚴格的規範,也宣揚著對他人的信任,就像是愛,需要有規則、信念、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絲瘋狂。」(註2)
-
 評論 戲劇
評論 戲劇從「沉浸式劇場」到「劇場裡的沉浸式」(上)
從臺中國家歌劇院兩部沉浸式展演製作談起需要寫在最前面的是,近年由大型場館或藝術節主導,並於專業劇場空間發生的「沉浸式」展演,大體可以分成:一、主打擴充實境(AR)或混合實境(MR)科技,以穿戴式裝置為載體打造數位化的沉浸式體驗;二、不倚賴前述設備,單純以空間調度、舞美設計及聲音影像達到沉浸效果的展演製作。本文主要討論之案例為《偵探學》(2022)及《Sucks in the Middle》(2024),其範疇屬後者。 沉浸式展演約莫在2015年前後逐步進入觀眾視野,這些展演大多採高單價、多場次、少人數的銷售策略,主打結合餐飲、互動遊戲、遊走式參與的複合式體驗。同時多以餐酒館、高級旅店、咖啡廳等非典型場地作為演出空間,既可讓觀眾身歷其境地感受整個作品,又能擺脫繁冗的劇場規範。同時,這些非典型空間所帶來的親密感、話題性、甚至是異業合作的潛力,都讓沉浸式展演近年在藝文市場占上一隅,成為表演藝術一個新形態(重點是有效)的營運模式。 近幾年,大型場館也開始試著打造獨家限定的沉浸式展演,從發生在劇場外建築空間(例如國家兩廳院《神不在的小鎮》、臺灣戲曲中心《和合夢》),到發生在劇場空間內,但不使用原有的舞台鏡框及觀眾席的沉浸式展演(如臺中國家歌劇院主辦,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偵探學》、《Sucks in the Middle》),雖然數量尚不算多,但演前演後也確實收穫了不少回響及討論。 從主事者和創作方的角度出發,這樣的製作趨勢或許反映了藝文場館對於節目的多元、場地的實驗及受眾的開拓,所展現的積極與實踐。但同時令人好奇的是, 一個從成形到成功都在劇場外的非典型展演空間裡的關鍵字,是為了什麼原因會讓我們試著把它放在劇場裡?而觀眾和創作者又希望從一個發生在劇場裡的沉浸式展演獲得什麼?
-
 評論 戲劇
評論 戲劇從「沉浸式劇場」到「劇場裡的沉浸式」(下)
從臺中國家歌劇院兩部沉浸式展演製作談起拆掉觀眾席,然後呢?沉浸式展演製作對劇場本位的意義 「打破鏡框」對於劇場來說早已不是新命題,如果單純討論觀演距離的試探或是場地結構的改裝,那其實還有更多、更久的作品應該被提到。表演工作坊的《如夢之夢》(2005)、當代傳奇劇場的《水滸108I上梁山》都曾對國家戲劇院加以改造,將表演區延伸到觀眾席內。但在「沉浸式」一詞定義成型的今日,《偵探學》、《Sucks in the Middle》所打破的不只是作品之外的鏡框,而是作品之內的第四面牆;也因此,所謂的「沉浸」才得以成立。 回到本文開頭的提問,當藝術家大費周章地讓觀眾席從劇場裡消失、將前後台空間打掉重練,把劇場費心改造成適合演出的結構,那使用「劇場空間」作為場地的用意是什麼?而就劇場本位出發,這樣的作品對劇場的意義又在哪裡? 這裡我想再拉進來一個作品,是與《Sucks in the Middle》同一週於臺中國家歌劇院小劇場演出的《感覺的邊界》。這是臺中國家歌劇院2024年新藝計畫甄選的兩件作品之一,由新興數位藝術團隊SYNZR(吳秉聖、邱俊霖、劉承杰)呈現。《感覺的邊界》是一個音像藝術作品,觀眾與表演者被數公尺高的數位屏幕和多聲道音響環繞,輔以劇場燈光設計及動態捕捉技術建構出奇幻的視聽體驗。 觀看《感覺的邊界》的過程,一定程度上也有某種沉浸式的效果,它同樣沒有明確的觀看區與觀看方向、觀演距離極近,同樣有種整個空間都被作品填滿的感覺。但它並沒有《偵探學》或《Sucks in the Middle》那般,將劇場空間改造成另一種場景的企圖,也沒有前述二者所具有的、類似限地創作(site-specific)的理念、為特定表演空間量身打造它的內容,這個作品在其他場所(暫且不論設備條件或是技術規模)同樣可以成立。 我想要特別指出的,是創作團隊在演後座談中的一句發言。當創作團隊被問到,如果這個作品在美術館或是其他多功能、非典型場地也能演出,「那麼劇場空間對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而創作團隊表示,相對於音像藝術過往以戶外空間或視覺藝術展場作為展演場地,劇場提供了相對專業、彈性、多元的技術條件及設備環境。更重要的,劇場本身是一個具獨立性的空間,可以避免作品受其他環境因素譬如聲音、光線(可能來自於場地外部環境,或是同


Noriyuki SAWA沢則行:偶師、戲偶與觀眾,是不可或缺的三角關係

邱安忱:想賦予戲偶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劉毓真:有偶陪伴,善待彼此的人生

楊輝:四海為家,用掌中戲偶交朋友

陳敬皓:搭起一般人與劇場的連結,讓偶戲走進日常
-
 生活 藝@書
生活 藝@書精進古典音樂的講座精華
《未解的問題:伯恩斯坦哈佛六講》 無止境的音樂思辨光從書名來看,這本書似乎與古典音樂難以構成聯想;但一看到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想必一定是關於音樂創作或樂團指揮的相關書籍吧?!待翻開內容又看到了許多譜例,相信許多讀者心中必定充滿詫異,這本書究竟在說什麼? 事實上,本書的標題《未解的問題》來自於伯恩斯坦1973年在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所進行的一系列講座名稱,其發想源自美國作曲家艾伍士(Charles Ives)在1908年所寫下的同名小品。艾伍士的這首曲子激發了伯恩斯坦的靈感,那就是「進入到20世紀後,音樂要往何處去?」,而伯恩斯坦在哈佛大學的系列講座便以此為名,以6場講座的規模為學生們闡述他的想法與理念。而本書就是這6場講座的演講內容,經過編輯們的潤筆挑篩精練而成。 雖然這已是近半世紀前的講座了,但伯恩斯坦精闢的觀點與見解放在身處於21世紀的當代仍歷久彌新。首先,他以跨學科的方式提供了一種分析音樂、解釋音樂歷史的新方法。在第一場講座中以柯普蘭的《鋼琴變奏曲》作為楔子,援引簡單的音樂主題向聽眾闡明音樂發展的各種可能,同樣的4個音可以成為巴赫《平均律鍵盤曲集》中的主題,也可以演變成拉威爾的《西班牙狂想曲》,甚至是烏德香卡舞團中的印度音樂。由此觀點出發,伯恩斯坦嘗試以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語言理論為基礎,向聽眾建構起他對於「音樂要往何處去?」的思考邏輯。 在前3場講座中,伯恩斯坦試圖從音韻學、句法及語義學來分析音樂在聲音、結構與意義上的組成與發展,並將焦點著重在古典時期的音樂。到了第4講〈歧異的樂趣與危險〉中,伯恩斯坦解釋了浪漫時期音樂中關於和聲的不確定性與結構自由等特色,並仔細分析了華格納在《崔斯坦與伊索德》裡大膽卻又充滿創見的和聲手法。第5講〈二十世紀的危機〉則介紹無調性音樂的衍生過程及此一潮流所可能引發的重大危機,同時也在此揭示了艾伍士在《未解的問題》一曲中對於此一潮流的憂心與反諷。最後一講〈大地之詩〉則將重點放在斯特拉溫斯基的創作觀,伯恩斯坦認為斯特拉溫斯基已為這個「未解的問題」找到了答案。 而本書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將近一百則譜例,洋洋灑灑地分布在書上各處猶如一本專業的音樂分析教材。事實上當年伯恩斯坦在演講時時常信手彈奏他所要示範或舉例的音樂段落,有時也
-
 國際 澳門
國際 澳門第34屆澳門藝術節 經典與當代的「奇.遇」
「第34屆澳門藝術節」於5月3日至6月7日舉行,今年藝術節共上演19檔演出,並策劃了23項延伸活動,活動總預算約澳門幣 2,490萬元,比起去年增加了290萬,與2019年的第30屆相近,增幅主要來自邀請外國團隊。今年有來自中國內地、澳、台、港及歐亞等13個不同地區的表演團隊,當中澳門藝團製作的節目達五成,共有13個澳門團隊及學生戲劇組參加,而「排灣貝拉Paiwan-pella」則為自2018年後首個參與澳門藝術節的台灣團隊。過去4年由於疫情關係,外國團隊難以來澳,藝術節中幾乎都是本地及中國內地作品,本屆外國團隊的數量又回升到跟2018及2019年相近。
-
 評論 回想與回響 Echo
評論 回想與回響 Echo走進跨時空的《青.白一念》
朱安麗是跟我合作過的戲曲演員,從她在現代劇場的表現,可以看出她在傳統.戲劇的技藝是很具實力的,幫助在現代劇場呈現了一份有品質的表演功夫,這是我在參加過各種外國表演工作坊的演員身上,所看不到的一種成熟的風格。這次她在中山堂光復廰與長笛演奏家華姵,合作演出《青.白一念》,我看到DM令好奇心油然而出,於5月12日下午親赴現場觀賞。 她們的表演舞台是非常樸實的,只利用了光復廳原本二樓的迴廊,及左右對稱的斜梯作為穿梭的空間,及正前方搭起的一塊平台,觀眾既可以近距離看到朱安麗眼神細膩流盼的情感,從迴廊或斜梯上,亦可感受到演員形體在遠視之下造成一種立體的美感。簡單的燈光照明與下午室外光線從天窗投射進來,遂使觀賞空間充滿一種自然的現實感。 就在這樣一點都不如夢似幻,反而帶有真實既存的表演空間,上演了這齣不是原本戯曲的呈現,卻又混合了以長笛為主,配合西塔琴、古箏甚而打擊樂的複音效果,烘托出白蛇的旦角漫漶著繾綣悲絕的唱腔,在戲曲本已秉賦節奏錯落有致的雅音上,朱安麗的唱作表現可說是已達絲絲入扣的境地,與白蛇相依為命的青蛇雖由長笛演奏家華珮串演,相對於傳統曲藝的旦角唱功,無論是唱腔或道白,她皆以長笛細膩、濃密的音韻回應,並通過大提琴的協奏迤邐出極具現代意味的旋律。尤其華姵在長笛吹奏上滾滾盪出即興悠揚的氣韻,這是難得一種在聽覺上所感受到的聲音饗宴,當場聆聽無論朱安麗的唱腔或華姵的長笛,不只令人有耳目一新的驚豔感,更讓聽覺完全沉醉在這樣優美的音樂之中。 我在觀賞這場《青.白一念》的演出現場,深深感受到兩位女性表演藝術家運用了她們獨特的陰性情感,在與許仙、法海所代表無情無理的男性權力對抗時,表達了女性之間相互倚靠的孤獨卻共生的情感。曾看過無數白蛇傳不同的故事版本,不管電影或戲劇都有過不同手法的演繹,但這一次看到的《青.白一念》卻令我對這段熟悉的故事有重新的體會,細究原因,不能說不是跟朱安麗及華姵雙旦的精采演出有關。
-
 專欄 思想不短路
專欄 思想不短路文字指令:藝術生成的彈指神功?
史丹.李只負責擬出一頁的故事大綱甚或區區幾句提要,即交給合作夥伴自由發揮想像力產出20頁一本包含圖畫及劇情發展細節的連環圖,最後再回到編輯室由史丹.李「看圖說故事」填入對話泡泡。創作成果如鋼鐵人、蜘蛛人、X戰警等日後舉世聞名的超級英雄的酷炫造型,其實均由漫畫家們實際負責設計與成型。史丹.李僅執掌命名及出些點子,但卻成為代表漫威的門面。仔細想想,史丹.李的做法不就形同如今讓AI生成圖文、影像或音樂之前所下的文字指令?

-
人物 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舞蹈創作者
王甯 身體作為我的自傳
王甯腦海中有個畫面,是4、5歲的自己在家裡拿了一張紅色的舞蹈社招生傳單,「下一秒我就出現在教室踢踢腿了。」小王甯開始學習芭蕾、現代舞、武功身韻等「基本功」,進入北安國中舞蹈班也承襲這同一套「生產鏈」。在升學主義邏輯中長期被灌輸「北藝大是最好的學校,考上才代表很會跳」,王甯卻接連在北藝大舞蹈系七年一貫先修班、大學落選,於是在臺藝大舞蹈系畢業後,她不死心地繼續往北藝大舞蹈研究所敲門,並刻意繞開表演創作選擇理論組,終於在2013年取得入學門票。 隔年,王甯經歷巨大的內外震盪。10年前的318運動捲起台灣社會史上最大的公民抗爭浪潮,立院與其周圍持續被民眾占領長達23天;於此同時,王甯在面對母親的逝去。社會氛圍的混亂與家庭核心的崩塌,雙面夾擊才20歲出頭的王甯,「那個時期我有點搞不太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甚至是那一陣子書毅的演出忙完後,我好像才去經歷和消化那種對於親人離世的心情。」 當時她是周書毅《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2014,下簡稱「《看》」)的舞者,之後還去了一趟英國,參加侯非胥.謝克特(Hofesh Shechter)舞團徵選,從此明白自己不會再參與任何舞團的考試,她不喜歡在一大群人裡張牙舞爪,表現出力爭上游的樣子,然後被挑選。 處在生命的混沌,同為《看》舞者的余彥芳,成為王甯人生裡的重要角色。「我也不知道彥芳看中了我哪一點,或是覺得我一個人實在太可憐了,所以她就這樣子把我拎著。」王甯邊說邊將拇指與食指謹慎和緩地捏住再提起。盯著那兩指間的無形,我想像一個縮小到快要消失的女孩被一把拉起。
-
 評論 新銳藝評 Review
評論 新銳藝評 Review互文結構下的情感敘事
評一心戲劇團《相看儼然》《相看儼然》為一心戲劇團第三度改編張曼娟小說作品,過去《芙蓉歌》、《青絲劍》成功連結現代文學與歌仔戲,打造一心歌仔戲浪漫美學之高峰。此次增添「音樂劇」之元素,保有歌仔戲文學劇場之底蘊,呈現跨域藝術之創新。有別於過往改編依循原著搬演,編劇趙雪君讓《相看儼然》保有「本事根源」,僅萃取原著精神,解構原有敘事,重新建構話語,運用「戲中戲」與「互文敘事」之手法,打造文本情節牽涉之封閉邏輯,同時也與自身作品《狐仙故事》相互觀照來生輪迴與性別對話,讓文本敘事雙向並陳。 三線情節交錯互文敘事 雙生反串另闢性別輪迴 本齣戲以「宿命因緣」為主要敘事核心,「般度與殊離」之故事為基礎情感,從而敷演出「般度吳湄出家人」與「殊離郭子凌樊素」等三線角色輪迴,其中又虛寫一世「慧行與無塵子」之相戀。於此同時「般度與殊離」又是作為劇團演員樊素排練之戲齣,使整體架構建立在「戲夢/現實」之間,揉合「戲中戲」手法交錯敘事,三線情節交織相映,轉折之處全憑藉角色性別界線之跳脫。 一心戲劇團特色為雙生戲,此次演出中,雙生在前兩世中錯綜反串旦行,如此角色轉換快速,演員作表之創發如何「形神合一」成為一大考驗。 以孫詩詠扮飾殊離為例,演員聲腔較為沙啞,身段雖柔化卻因敘事時空在天人界,使得性別界線模糊,難以讓人感受其為旦行角色,即便粉紅色系服裝暗示,仍與孫詩珮扮飾之般度談情時,讓反串相愛似乎成為阻礙,實屬可惜。 到第二世轉換至孫詩珮反串扮演吳湄時,聲腔顯然與生行之般度作出區隔,行韻間稍牽尾韻,女扮男裝時,正好讓主攻行當與情節相吻合,使扮相轉為俊麗。尤其〈量身〉一折,該段為全齣戲勾起前世情緣關鍵,生旦聲腔之區隔,配合細膩身段與重疊投影之前世,以形體代替語言,讓反串成功另闢性別輪迴,使觀眾在龐大敘事結構中,能十分流暢地連結互文情節。 或因如此,編劇過度注重於輪迴之角色線,使得鄭紫雲飾演的香蘭一角流於功能性,與郭子凌之感情猶如林黛玉般,較關注於生存狀態之擔憂。雖然演員作表塑造立體,也成功烘托出諦問愛情之茫然,但在環環相扣之敘事結構中,反而削弱角色能量。
-
 演出 音樂 第三屆臺灣國際豎琴節
演出 音樂 第三屆臺灣國際豎琴節豎琴藝術的交流平台 展現多樣與可能
「臺灣國際豎琴節」(Taiwan International HarpFest)由台灣豎琴家解瑄創立,主要結合詩歌、舞蹈及攝影等多種藝術形式,以創新跨域的表演模式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今年第3屆的設計,以「豎光潮現」為主題,透過海洋世界、環保等議題來傳遞更多訊息,期待突破觀眾對豎琴既有的定見,展現它各種型制、樣貌與可能性,並集結國內外豎琴名家與新星的表演、大師班與講座,創造一個平台與世界豎琴藝術家相互交流。 由於豎琴學習的門檻高、樂器移動不易,樂團需求量又少,因此投入者不多。解瑄表示:「豎琴是相對弱勢的樂器,如果沒有年輕學子的加入,就不會有成長的空間。」作為台灣第一代的豎琴家,她挺身而出,盡力進行這項樂器的推廣。她說明:「古典曲目中,要到後期浪漫的樂曲才用得到豎琴,但當代豎琴有多種面向,例如在電子、爵士、流行都有發展,絕對是一個充滿想像空間的樂器!」 本屆音樂節共有5場音樂會,應邀而來的重量級音樂家眾多。法國知名超技豎琴家席爾凡.布拉索(Sylvain Blassel)不但是一位古豎琴收藏家,也熱中於以創新技巧拓展豎琴的獨奏曲目,如巴赫、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作曲家的名曲。此次他將以直立式音箱(Straight soundboard)豎琴演奏巴赫創作高峰之作《郭德堡變奏曲》,更加碼多首李斯特鋼琴版的舒伯特藝術歌曲,包含《紡車旁的葛蕾卿》、《磨坊少年與小河》等迷人作品。

Noriyuki SAWA沢則行:偶師、戲偶與觀眾,是不可或缺的三角關係

邱安忱:想賦予戲偶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劉毓真:有偶陪伴,善待彼此的人生

楊輝:四海為家,用掌中戲偶交朋友

陳敬皓:搭起一般人與劇場的連結,讓偶戲走進日常

你不可不知道的偶戲跨界創作

找尋自己的當代語彙:台灣現代偶戲的跨界表演

非「偶」不可?! 當代偶戲跨界裡的關鍵思考(下)
「愛國東小聚場 ——偶戲翻車記?」側記
非「偶」不可?! 當代偶戲跨界裡的關鍵思考(上)
「愛國東小聚場 ——偶戲翻車記?」側記-
 專欄 說戲
專欄 說戲藝術總監做什麼?
「每場演出妳都要來啊?」 國光演出時,觀眾這樣問我,還有許多好心的關注:「同一部戲演3場,妳不需要3天都到吧?」 很感謝觀眾體貼,但也很洩氣。 到國光擔任藝術總監22年,大大小小每一場戲都像自己孩子的人生大事,無論是幼稚園園遊會、中學段考、大學學測或博士口試,身為奶媽保母,怎捨得不緊張地全程盯著?甚至國光對外的每一段文字,我都覺得是自己的責任,當然也包括演出字幕的校對。雖然負責字幕的同仁非常認真,我仍忍不住雞婆再校3遍。 藝術總監的大節更在方向的掌握,22年前我提出「現代化、文學性」,這兩項都有針對性,甚至階段性。 傳統一定要扣緊時代脈搏,我不願以博物館櫥窗為定位,現代化勢在必行,更強調京劇是現在進行式甚至未來式。「文學性」是針對崑曲。我愛崑曲,我曾說京劇是娘胎元配,崑曲是中年外遇,我不想還君明珠雙淚垂,也不會恨不相逢未嫁時,只想左擁右抱。而我的兩個愛人有衝突,京劇還好,視崑曲為母體源頭,也是京劇大家族成員之一(註1),曾被京劇打敗的崑曲,重生之後卻難免有點吃味,總批評京劇沒文學性。 我對雅俗沒有高下之分,卻要再三強調文學不是詞采典故,生動就是文學。 第一部戲我選了《王熙鳳大鬧寧國府》,大家都以為要借《紅樓夢》昭告文學性,其實不是,我要以這劇本生動通俗的語言,讓觀眾體會未必「朝飛暮捲、雨絲風片」才叫文學。 王熙鳳處理丈夫外遇的經驗豐富,三下兩下就能搞定,而這回卻不一樣,這次的小三竟是賈家親戚,丈夫堂嫂的妹妹 :「新賤人 並不是 平常雜性」,新字妙到極點;又聽說新小三竟已懷孕,我王熙鳳的罩門不就在不能生兒子嗎?這叫「捏住我 鼻尖兒 不吃不成」!這樣的唱詞是俗,卻生動,這就是文學。 小說裡王熙鳳沒有文學素養,劇本讓她跑到小三面前示好:我不能生兒子,早就想為老公娶二房,誰知他手快先找到了妳,但「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把我瞞得個水泄不通」,觀眾看到「水泄不通」無不發笑,不是笑編劇錯用成語,而是讚嘆劇本厲害,讓鳳辣子口吻聲息活靈活現。 總監要「出戲,出人」,眼下放著魏海敏國寶,只演老戲怕只有同溫層能賞味,我想出王熙鳳讓魏老師極大化。海敏一聽,眼睛一亮:「這戲有料!」一開始遵循前輩童芷苓
-
 話題 話題追蹤 Follow-ups
話題 話題追蹤 Follow-ups傳統戲曲的現代挑戰 雙雙拿下年度大獎與表演藝術獎
第22屆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側記第22屆台新藝術獎於今年6月1日下午舉行頒獎典禮,年度大獎由窮劇場與江之翠劇場合製的《感謝公主》獲得;表演藝術獎和視覺藝術獎則分別由臺北海鷗劇場以鄭成功為靈感創作的當代歌仔戲《國姓之鬼》,和關注台灣移工處境的你哥影視社《宿舍K Tc X》獲獎。3個獎項即有兩組為糅和戲曲的表演藝術作品,且不約而同地對傳統形式與技藝的現代意義有所討論與探索,得獎別具意義。 本屆決選團由戲劇學者林鶴宜擔任主席,帶領藝評人張晴文、電影導演黃亞歷、製作人孫平、旅法藝術家鄭淑麗(CHEANG Shu Lea)、澳洲阿德雷德南澳美術館館長蘿娜.迪芬波特(Rhana Devenport ONZM)與德國柏林Radialsystem藝術中心總監馬提亞斯.摩爾(Matthias Mohr)進行3天高濃度的討論。評審團給予《感謝公主》高度肯定,認為其文本結構細膩,深刻展現傳統梨園戲與現代劇場的藝術特質和技法,窮劇場與江之翠劇場在各自專長之處找尋對話與交融的空間,為當代劇場與傳統戲曲開拓新的共作可能,同時亦於藝術辯證中,體現生命難能承受之重。(註1)《國姓之鬼》則無論在敘事結構、演員表現與題材處理上,展現出積極的實驗性,演員本身的深厚表演功力,將形式消化並展演出傳統戲曲當代的新路徑。(註2)
-
 演出 戲曲
演出 戲曲一人分飾多角 《凱撒大帝》重現穿梭古今的政治寓言
當代傳奇劇場自1986年創團以來,從京劇藝術出發,轉譯多部西方經典,如莎劇、希臘悲劇、契訶夫小說等,成為享譽國際的跨文化劇場代表。尤以莎劇改編最為當代傳奇劇場的特色,包含改編自《馬克白》的創團作《慾望城國》,並陸續詮釋《哈姆雷》、《李爾王》、《暴風雨》、《仲夏夜之夢》等,而將在台北演出的《凱撒大帝》則再次改編莎劇,並以「歌劇」形式,持續展現當代傳奇劇場在藝術創作上的多元與實驗意義。 對主創者吳興國而言,自《李爾在此》以來,就希望能將「自己」作為概念拋擲到角色裡,這也深深影響到後續作品的思考。《凱撒大帝》背後的政治性,就是吳興國所在意、卻又不知如何下手的關鍵,因為這可以很個人,也可以非常群體,甚至是影響整個世界。










